今天是1月23日世界自由日。
這一天的由來,雖然與歷史上的戰爭有關,但節日的意義,也許更著重在提醒人們反思日常生活中習以為然的秩序、或是重新記憶那些可能隨著時間推進而淡忘的傷痕與教訓。就像不是基督教的人也同樣歡天鼓舞地慶祝聖誕節、二二八紀念日領導人也都一定要率領群眾默哀致意一樣,既然今天是世界自由日,那麼我們也就重新被提醒了思考:「自由」的意義。
生長在台灣這個號稱自由民主的國家,我們對於「自由」的敏感度極高,無論是人身自由、言論自由等日常行為表達一旦被干涉或侵犯,都會讓人們馬上意識到不適感;照理說,在這種普遍認知的意識訓練之下,我們應該相對於受到囚困、拘禁、禁錮的生命體,都有高度的同理心才對——但事實上似乎不然,在台灣的動物園、大型水族館(海洋公園、海洋世界)裡依舊圈養著許多種類的動物,即便日前有阿河眼淚事件,犧牲了牠的生命希望可以喚醒人們的同理心,但卻依然無法與人們獵奇的觀賞心理抗衡。
當我們高舉雙手伸張自由的時候,卻只有極少人會轉身看看那些牢籠中的動物,去思考關於牠們的自由;當我們開始思考「自由是有底限的嗎?」這個關於生命的哲學問題時,殊不知對於被人們圈養奴役的動物而言,自由還真是有個對應的底限的。最早提出動物自由建議的英國政府農場動物福利委員會(FAWC),在1992年為回應Ruth Harrison於1965年所著《動物機器(Animal Machine)》一書,確立了「動物福利五大自由」(Five Freedom)的基本概念 。而「世界動物衛生組織」(OIE)進一步於2005年開始逐步訂定各項動物福利綱要,推動各會員國制訂相關法律與政策。
於是,當時以「讓動物有滿足這些需求的自由」為訴求所制定的「五大自由」,就成了現在許多動保人士或圈養機構,用來拿檢視或自圓其說的依據——但值得思考的是,當自由有了底限,還是真正的自由嗎? 有時,我們必須謹慎地看待這些條件所自困的圈套,當一套評估標準被制定,事件本身已脫離了生命該有的狀態,充其量,也不過是在為這些受困受苦的動物,爭取進一步的生存空間而已。有條件的自由,也許是一把比例尺,讓我們看見”自由”對於這些被圈養的動物而言,是多麼地遙遠。
免於饑渴的自由(Freedom from thirst, hunger and malnutrition)
—可享用足夠飲水與食物。—
生命三大要素:陽光、空氣和水。對於被圈養的海豚而言,究竟如何算得上「足夠的飲水與食物」呢?
根據曾在圈養海豚機構工作的訓練人員所說,海豚每天的食物是定量餵養的,餵牠們吃多少,則是由體重的比例來決定。動物們無權決定自己要吃多少,取決於人類認為牠們該吃多少。而眾所皆知的事實是:圈養動物的訓練就是靠飲食控制作為誘導,訓練人員透過動物對於食物的慣性與慾望,以「正加強」(獎勵)或「負加強」(懲罰)的方式,透過食物來訓練動物做出(不論是為了醫療或表演)各種人類期望的動作。
換句話說,動物是在有條件的情況下,被允許或禁止「享用」牠們的食物;基於動物健康的考量,圈養機構的工作人員會辯稱,最終仍會給動物吃到固定的量,不會刻意去讓動物挨餓。然而,不論是多麼正向的說法,都不抵動物若沒有對食物的缺乏為誘因,根本不會聽從人類指令的事實。
免於不合適的自由(Freedom from discomfort)
—保證提供合適環境、防風避雨、保暖禦寒的棲息處。—
野外動物的棲地,是經歷過地球環境演化數千年來,透過自由移動、適應、選擇而來的。這些所謂的棲息之處,有時甚至是隨季節大規模流動的。被圈養的動物,從本來經過族群自主選擇的原棲地,被人類捕捉到粗糙濫造模仿而成的人工環境裡,空間的設計完全是以人類便於管理、隨時可以觀看為考量去做規劃,而以棲息於海洋環境的海洋哺乳類動物而言,試問人類要如何模擬變化莫測的海流、海底地形、海洋生物,來符合這些動物所適合的水溫及海水濃度,提供所謂「合適的環境」呢? 以台灣現有的大型水族館來看,每一個都是以光禿禿的池壁、最深僅有七米的水池來圈養海豚,在圈養的環境中產生的各種音頻噪音、颱風過後時有異物的水池,都時時威脅著些動物的生存品質。
免於痛苦、傷病的自由(Freedom from pain, injury and disease)
—保證提供疾病預防、疾病及受傷可迅速治療。—
有些人會誤以為,比起在自然環境下面對天敵,圈養的動物相對不會受到痛苦跟傷害,還有人類隨時為牠們作疾病預防跟治療。但以目前國內圈養海豚不透明的死亡資訊而言,大多數的人恐怕是被海豚的微笑假面所誤導了。首先,人類對於海豚的認識和了解,即便經過多年的努力,都還不夠成熟。無論是病菌的感染源、動物致死的原因,突發疾病的治療,大多數都還是到動物死亡之後解剖才得知的。如果不是這樣,海生館就不會一連死了7隻白鯨、而海洋公園在2002年第一批自日本太地購買進來的11隻瓶鼻海豚亦只有4隻仍存活,而海洋公園內繁殖的小海豚則迄今未有成功活下來的案例。
表現其自行為的自由(Freedom to express most normal behavior)
— 保證提供適當空間、設備與同物種交往的機會。—
被圈養的動物,都是從原棲地被捕捉而來,早已脫離了牠們原有的社群、同伴。人們無法想像的是,大自然的動物社群和人類一樣自有秩序,在人類看來他者似乎差異不大,然而在自然界中卻差之千里。換句話說,並不是同品種的海豚就可以歸類為 「牠們適合住在一起」,而把牠們圈養在同個水池中。
事實上,即便是在同個海域出現的鯨豚,都有可能來自不一樣的家庭階級、文化背景,被單獨捕捉的海豚在遠離族群和同伴的狀況之下被關在一起,是不可能達到所謂「在適當空間與同物種交往的機會」的。相反的,動物毫無選擇的可能,被人類隨意嘗試配對拘禁,直到彼此間產生了爭鬥權力地位的打鬥之後,才被分開。
免於恐懼、緊迫的自由(Freedom from fear and distress)
— 保證避免引起心理痛苦的條件。—
顯然,這是更遙遠的自由。
當動物被捕捉,首先牠會經歷被傷害的恐懼,接著牠的族群可能被屠殺、被強制與母體或家庭分離、還要被挑選、接著經歷長長的黑暗運輸過程,被押運至完全陌生的地方,吃牠一點也沒有再更多選擇了的食物。然後牠無法選擇跟誰共處一室、無法選擇不表演或不交配,更無法不想念大海家園。這種種的痛苦,沒有答案也沒有出口,往往造成動物在身體、心理上的各種創傷,如果曾經長時間坐動物行為觀察的話,就會發現圈養動物都會出現一些固定模式的刻板行為,甚至可能自殘以及傷害他人。
動物福利的五大自由,被用以檢視原來生活在大海裡的海豚所處現況,簡直就是遙不可及的願望。人類在商業行為的利益驅使之下,去野外捕捉這些自由自在的生命,再以五大自由來包裝牠們其實沒有過得那麼糟,甚至去強調自己用了多少人力物力資源來達到照顧動物的生存品質,根本就是本末倒置的說法。在此,我們並不將擱淺救援的鯨豚列入討論的範圍之內;因為目前國內表演機構所蓄養的海豚,從來都不是來自擱淺救援的照護,而是勾結在全球捕捉—展演產業鏈底下蓄意操弄從中獲利的商業行為,多少生命的尊嚴在金錢的交易中被犧牲,多少不忍心的照顧者被說服與收買。
說到底,人類世界的利益本就不該用動物/他者的生命作為交易和威脅,當我們在這一天討論人類的自由時,是否也應該花個幾分鐘,為不可能討論自由的動物們默哀呢?
當然,更積極的是,從這一天起拒絕成為扼殺動物自由的幫兇,不支持動物表演產業,讓野生動物待在原棲地,用牠們生命的秩序,世代繁衍下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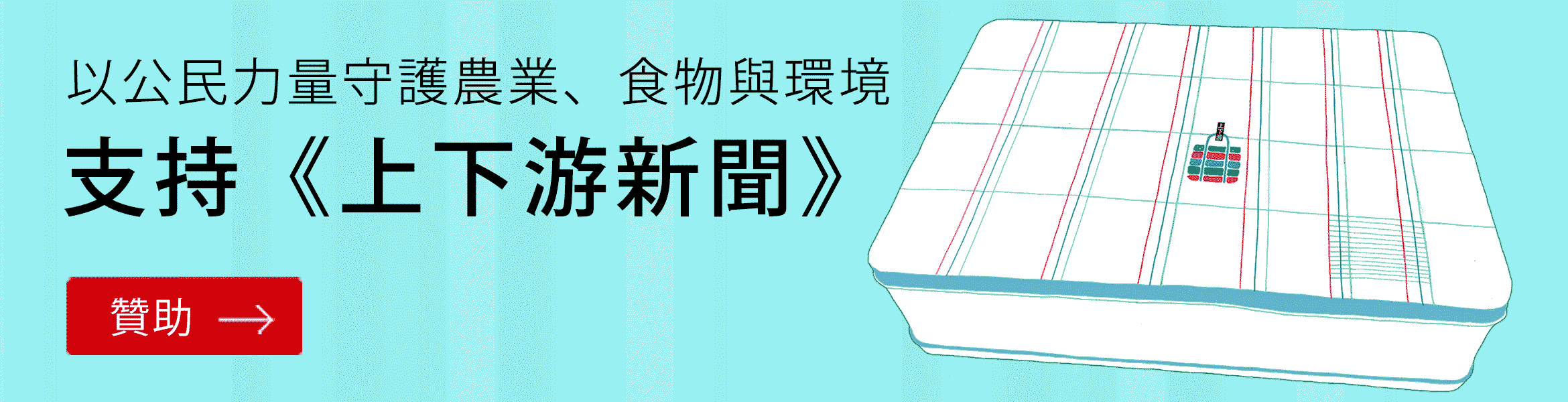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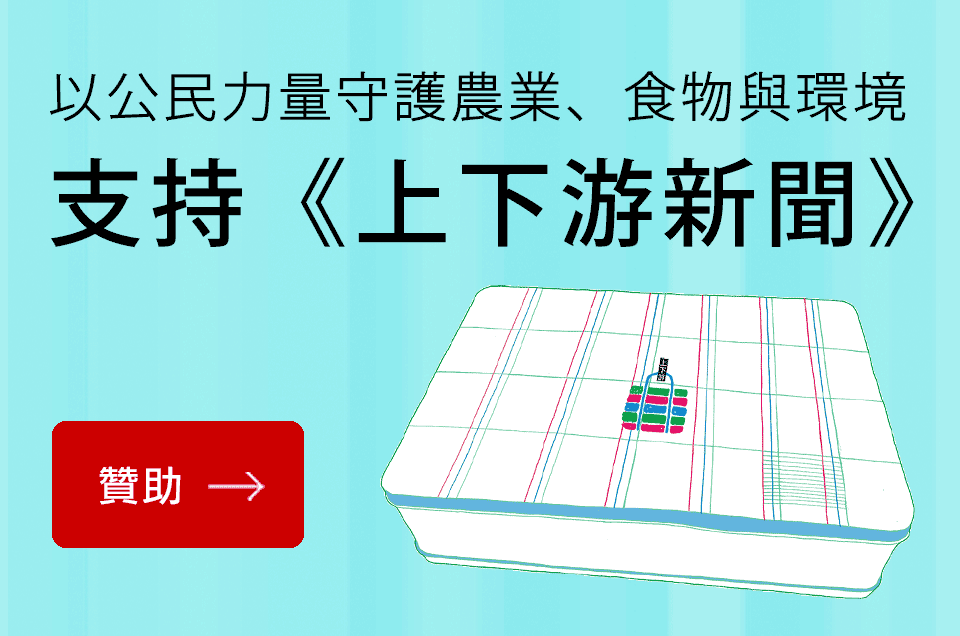














感謝本文作者不斷為海豚發聲,十分感謝
希望這樣的聲音能持續不間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