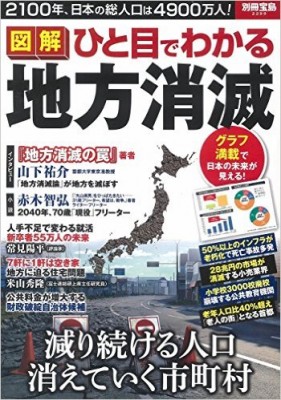
日本前總務相、東京大學客座教授增田寬也2014年出版《地方消滅》一書,描述根據國立社會保障人口問題研究所的最新官方數字顯示,由於日本人口流往東京在內的三大都市圈,適育年齡「20~39歲」女性人口數減少,以及高齡化與少子化的影響,到2040年全日本有896個市區町村(相當於日本地方自治體總數的49.8%)將面臨滅絕。
其中,北海道中部和東部等日本最重要的農業區,挑戰尤其嚴峻。到2040年,數十個村子的20歲至40歲女性人口至少將比2010年減少50%,有的高達87%。大約40%的人口將在65歲或65歲以上,引發誰將耕種日本最富饒的農業區的問題。
在台灣,類似日本的情形早就上演著,農村產業凋零所引發的人口外流、少子化與高齡化,正一步一步往《地方消滅》的方向邁進,然而比日本更嚴重的是,因為地方政府財政困難而進行小學裁併,引爆偏鄉教師出走潮,無疑是讓農鄉提早被「消滅」的加速器。
每逢驪歌初唱 偏鄉小校教師就爆出走潮
7月盛夏,正當畢業生展翅飛入下個教育階段,學校著手規畫下學期課程之際,偏鄉小校擔心的卻是「教師出走潮」。小校師資結構不穩雖是老問題,但近年國家財政困窘,中央和地方接連推動財政健全方案,教育經費刪減、小校整併計畫也在之列,不由得令人更加擔心小校的生存。
一個小校殞落不單是節省經濟資源,其背後與社區文化、在地農業的連結勢必削弱甚至斷根。
9年前接手雲林縣古坑鄉華南國小,力挽狂瀾拯救落入縣府第一波裁併名單的校長陳清圳,日前便於臉書寫道:
「每年驪歌初唱,除了送走一屆屆畢業生外,心中隱含另一波壓力,那就是偏鄉學校教師的出走潮。而這出走有的是調校,有的是辭去行政職。」
為何小校教師要出走?以華南國小6個班級、共有10個教師為例,陳清圳指出,除1位校長、2位專任主任外,剩餘負責班級經營的7位教師,還必須有2位身兼教務組和訓導組的行政業務,「但大校要肩負的行政業務換到小校並沒有減少,反而變成『三、四人業務歸一人扛』的窘境。」
以教務組來說,行政內容含括教學、註冊和設備3領域;訓導組則要處理生教、訓育、體育和衛生等業務,曾待過千人大校再到百人偏鄉小校的陳清圳表示,這些業務在大校是分成組別由專人負責,小校卻全交由一人負責,「老師怎麼可能不離開?」

「小校若關掉,社區就會『冰』起來」
而與都會型大校不同的是,偏鄉小校不只肩負教育功能,同時需身兼文化保存、少數民族語言傳承等,越偏鄉的學校和社區越密不可分。
像華南國小,陳清圳接任時便帶著團隊開發特色校本課程、四季高峰課程,鼓勵學生認識社區,甚至是思考社區產業的發展性。這背後付出的努力是,他需兼任校長和華南社區總幹事的職務,國小的總務主任也一起「撩下去」,配合推動社區營造、社區綠美化、農村再生、社會福利、社區醫療等事務。
都市因人力多,學校不需身兼這類功能,但偏鄉社區因老年化、人力外流,像華南社區常住人口約有300人,「社區和國小基本上是一體的,」華南社區發展協會理事長劉清極舉例,社區要大掃除學校老師會在八個部落分配好人力,請學生幫忙,學校還會主動辦活動讓學生了解咖啡產業,同時學生家長也會連帶參與,帶動社區裡有機蔬菜、橘子、柳丁、香蕉和愛玉等農產的銷路,「小校若關掉,社區就會『冰』起來。」

政府債台高築 加速小校裁併
但更大的隱憂是國家財政窘迫,中央、地方紛喊開源節流,繼苗栗縣政府,雲林縣長李進勇也在21日推出三年財改計畫,決定刪除五成縣長特別費、樽節公教人員加班費、業務費等,教育部分縣府除樽節獎補助費、檢討無意義的活動辦理外,長程規劃(105至107年節流計畫)更希望加速推動小校整併,雲林縣教育處國民教育科科長張淑芬坦言,內部將會提高獎勵機制,加速小校自行提出整併規劃。
截至2014年統計,全台百人小學共有1024所,雲林縣內154所就有83所不到百人,比例高達54%。加速裁併勢在必行,但陳清圳強調,政府在整體評估時應多看該地域文化獨特性、社區和學校的依賴性等,而不是單考量學生人數的多寡。
延緩「被消滅」 應整體增加偏鄉教師員額
在陳清圳於臉書寫下偏鄉小校師資來源不穩定的情形多年來未獲改善的感慨後,縣府教育處也在第一時間聯絡陳清圳,討論解決方案。
教育處社會教育科科長陳秀卿表示,雲林縣面對偏鄉小校問題第一時間不是裁併,而是朝師資優質化努力,這十年走下來,雖然教師能力的提升對偏鄉帶來許多幫助,但師資結構的問題還是得面對,所以縣內近期會著手規畫代理老師的專業課程精進、候用校長的學校領導,讓師資培力能機制化。
但代課老師能完全取代正式教師的功能依然有限,陳清圳和陳秀卿坦言,增加偏鄉師資才是根本解決之道。
陳清圳說,在都會區大校和偏鄉型小校身兼不同責任、卻肩負相同行政業務的狀態下,教育部不能再用班級數來計算教師員額;陳秀卿則表示,少子化是這個世代會遇到的問題,各縣市財政若持續惡化,小校裁併的可能就會增加,同時就會加劇M型化社會的發展,站在縣政府的角度,僅能從師資能力優質化著手,員額上的增加還是得仰賴中央整體政策的改變。













支撐一所6班的小校要一年要2000萬,弔詭的是這六班的小校有可能170人,也有可能50人以下;也就是說,原本一年要花2000萬支撐的學校(170人),要花到6000萬(50+60+60),當然教育效果有可能更差,或更好?當然這不考慮交通因素與孩子群體的互動;而更常見的狀況是老師流動率高、流失較關心教育的家長(通常移動能力也較好,學區外就讀去了)。當堅持社區一定要留住孩子與跳動的心臟(學校)時,誰在付擔這些支出?一個沒有產業的社區如何留住一間學校?靠補助?靠捐獻?靠舉債?這是大家要多去思辨的議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