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題前言:過去農民習於在田裡單獨奮鬥,較少合作組織經驗,近年來台灣出現許多精彩的產銷班或合作社,互相扶持尋求出路。上下游特別製作「團結力量大─農民合作的故事」,陸續報導各地農民合作案例,提供大家參考。完整專題文章,請點選這裡閱讀。
──────────────────────────────────────────────────
選美、選歌手、選模特兒,台灣選秀節目一籮筐,但你知道連胡蘿蔔都能選秀嗎?雲林縣東勢果菜生產合作社引進胡蘿蔔一貫化清洗廠,將每根胡蘿蔔分門別類,經過重重關卡後選出來的A級貨個個又甜又脆還沒有惱人腥味,不僅成功征服小孩子的嘴巴,打進國內各大百貨公司和超商,連在日本都能看到東勢出產的胡蘿蔔,年年創造破億產值。
東勢果菜生產合作社的胡蘿蔔佔台灣五分之一,為這個農業小鎮帶來不一樣的命運

機械化生產,帶領老農走出不一樣的路
「拔蘿蔔、拔蘿蔔、嘿喲嘿喲拔蘿蔔~」這句琅琅上口的歌詞是許多人共同的童年回憶,但是在雲林縣東勢鄉的蘿蔔田卻看不到一群人奮力拔蘿蔔的情況,取而代之的是兩公尺高的採收機。巨輪行駛過的田間,胡蘿蔔整齊地躺成一列,紅橘蘿蔔和綠色葉子與土壤交織出冬天最甜美的豐收,有了機器的輔助後,農人不必再「大粒汗細粒汗」和土地拔河,只要「撿」蘿蔔就好了,如此情景在日本已是常態,但台灣卻只有少部分地區有自動化採收機,雲林東勢就是其中之一。
每年12月到4月,走一趟西南沿海就可以看到一片片在風中搖曳的蘿蔔葉,土壤之下蓄積的「紅菜頭」是農民期盼了五個月的心血結晶,但不論是大豐收或歉收,他們都得看市場臉色才知道這一季能不能過個好年。出生東勢的合作社主席王文星從小看到家鄉的哀愁,1994年接手父親近二十年的胡蘿蔔栽培事業後,他決心導入日本經驗,以機械化、分級制度、生產履歷為核心,2009年建立生產合作社,讓農民走出不一樣的路。
王文星深知農村人口老化的問題嚴重,特別向日本添購播種機、採收機,本來需要80人的田間作業,在機器輔助下縮減到30人,時間更大幅減少一半以上,農民只要負責疏苗、灌溉排水、巡視田區,施肥噴藥都有專業的團隊代勞,合作社甚至添購自動化的噴藥機,牽設專門管線,成功種出品質齊一、產量穩定的胡蘿蔔,年年都通過國家檢驗,保證吃得安心。
在合作社的保障下,120戶農民平均每分地可以進帳一到三萬元,總計150公頃的土地每年生產九千到一萬噸胡蘿蔔,供應全台灣五分之一市場, 創造超過一億產值。合作社還在三年前成立「VDS活力東勢」品牌,成功打進百貨公司及便利超商通路,日本每年還預付訂金計劃生產,去年一共出口2000多噸,農民終於可以擺脫菜土菜金的宿命。


萬中選一的蘿蔔生死鬥,成功征服日本人嘴巴
雖然接手十多年,但真正帶領東勢胡蘿蔔脫胎換骨的契機是2006年的日本之旅。
王文星對日本農業管理印象深刻,他發現地狹人稠、農村人口比台灣還要老化的日本,從播種、採收到分級,全部都引進機械化設備,當台灣在採收期苦於找不到工人時,日本只要一台採收機、三個負責操作的人力,上百公頃的胡蘿蔔田一個禮拜就清潔溜溜。
走到日本的超市,王文星更大開眼界,架上每根胡蘿蔔簡直像雙胞胎一樣,大小外型顏色整齊又乾淨,反觀國內全部「摻摻作一伙」,消費者得要在籃子裡挑三揀四,過程中不知道造成多少擦傷碰撞,再怎麼好的胡蘿蔔品質也下降。
「如果不改變,5到10年內一定會收。」王文星認為,國內胡蘿蔔市場一直採取低價競爭,當然就無法顧及品質,但農村人口老化,人力成本節節上升,如果不改變模式,合作社絕對沒辦法生存下去。加上2008年中國毒水餃事件爆發,讓他看到台灣外銷市場的機會,更讓他下定決心投資近億元,引入胡蘿蔔一貫化清洗廠,還買了兩台胡蘿蔔採收機、播種機,成為台灣第一個採用機械化栽種胡蘿蔔的先鋒。
古時有皇帝選妃,彼時也有超級胡蘿蔔生死鬥,合作社將胡蘿蔔的「選秀」分成ABC三級,工人在田間會先初步篩選掉 C級,通過第一關的胡蘿蔔經過剪柄以及三次清洗後,容光煥發來到評審眼前,臉上有疤痕、皮膚色澤不佳、體態不夠均勻的只能無情被列入B級品,最後剩下約三成A級品,按照環肥燕瘦分為S、M、L、2L、3L、4L(及以上)等尺寸。歷經重重關卡,最後只有約兩成胡蘿蔔能雀屏中選揚名海外。


其中日本人偏愛小巧玲瓏的M(150~200公克)和L(200~250公克),香港多拿來雕花料理,喜歡偏大的3L(350~450公克)尺寸,不管要大要小、要便宜或昂貴、要包裝或帶土,合作社都有辦法滿足每個市場的需求。
經過嚴格篩選的A級胡蘿蔔咬起來清脆鮮甜,完全沒有一般胡蘿蔔印象中的腥味,顏色晶瑩透亮,還有人開玩笑說合作社的胡蘿蔔是不是打了脈衝光。如此細緻的分級,就是要讓客人不管上門幾次都能買到一樣的品質,王文星驕傲地說,台灣種出來的胡蘿蔔連日本人都說好。
產銷、教育、政策,合作社責無旁貸
從菜土菜金到開拓國際市場,這不僅是一場產銷革命,也是農民的學習之旅。
王文星接手合作社後便決心要生產出讓生產者和消費者都能安心的農產品,一開始為了管制方便,由合作社統一提供農民農政單位的推薦用藥,但許多農民卻偷偷摻其他的藥進去,理由是「之前剩下的,不用很浪費」,讓王文星好氣又好笑。而推薦用藥的藥效不如農藥行的「秘方」來的有效率,許多農民根本不願意使用。最後,王文星提出每季只要一千元就幫農民代噴到好的服務,農民覺得划算才紛紛改由合作社統一噴藥。
他也用胡蘿蔔汁「籠絡」農民,當農民喝到自己種出來的胡蘿蔔做成的果汁,而且還是外銷到日本,每個都驕傲的不得了,久而久之大家都漸漸能認同合作社的理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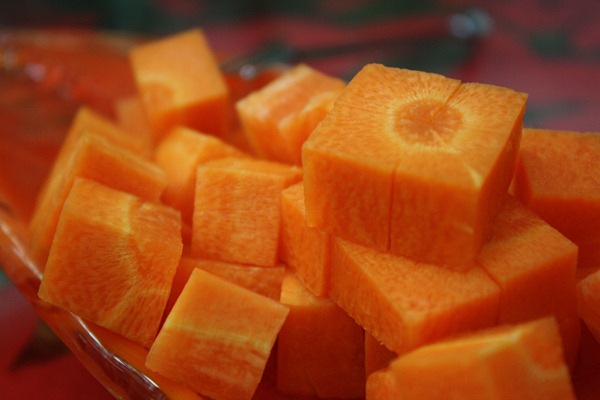
作為生產者和消費者的橋樑,合作社深知外界的想像與現實狀況的巨大落差,此時他們就成了最好的潤滑劑。「合作社不只要把東西賣出去,還要扮演教育農民的角色,這個過程是漸進式的。」王文星說,許多事情並非一蹴可幾,農民對於資訊的掌握度不高,需要慢慢教育,而這就是合作社的責任。
除了產銷、教育,合作社也是政策推動的輔助者,早在農委會推廣小地主大佃農之前,合作社就已經鼓勵農民集中土地種胡蘿蔔,只要鄰近農地加起來超過兩公頃,每分地就可以領兩千元獎勵。
掌握政策、市場風向,也能踏進土中和農民面對面溝通,合作社確實有很好的條件能發揮影響力。王文星說,未來除了繼續教育農民,種出更多安心、優質的農產品,也要推廣胡蘿蔔汁,讓更多人品嘗到胡蘿蔔的美味,繼續當市場的領頭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