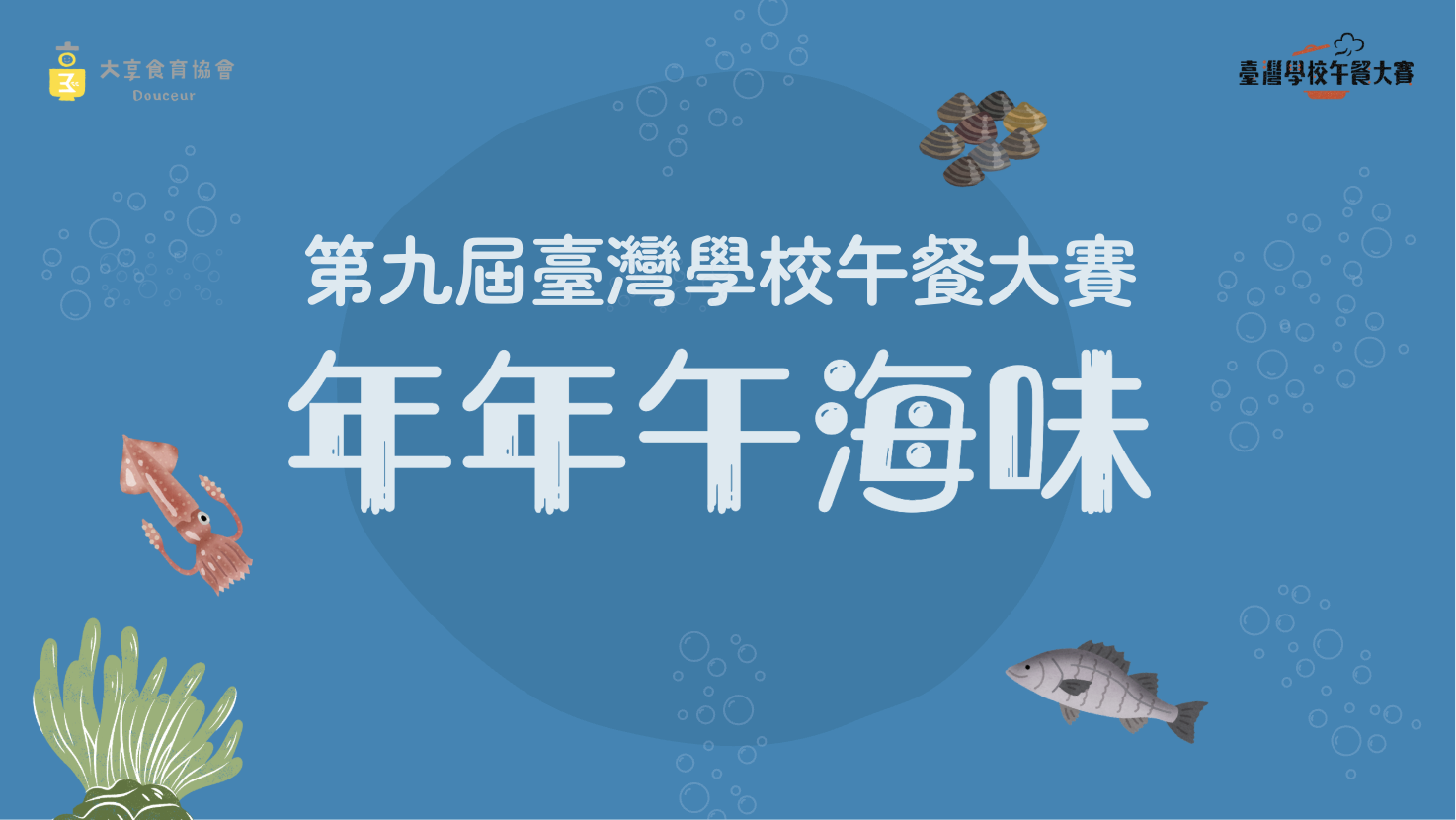我踏入職場後,做的多是農業相關工作,因此有人以為我是農校畢業的。每當我回答大學時代唸歷史系,許多人都是一臉吃驚,接著若有所悟:因為學歷史不實用又難找工作,就來種田囉!
我踏入職場後,做的多是農業相關工作,因此有人以為我是農校畢業的。每當我回答大學時代唸歷史系,許多人都是一臉吃驚,接著若有所悟:因為學歷史不實用又難找工作,就來種田囉!
對於「歷史」被視為「不實用」的學科,並和餵飽我們的「實用」農業毫無關係,我覺得很可惜。或許歷史不能教我們如何種田種得又快又好,卻能探究農業發展的軌跡,為農業議題提供更多元的見解。
比方說,如何面對糧食危機,「馬鈴薯的歷史」竟能提供靈感!
現今環境破壞、氣候變遷加劇,加上耕地日益減少,人口卻持續暴增,該如何應對未來可能出現的糧食危機?推廣馬鈴薯或許是解方之一。在歷史上,馬鈴薯可是拯救歐洲脫離飢荒,於近代成為先進國家的大功臣!
長久以來作為歐洲人主食的小麥、燕麥,容易因氣候嚴寒、土壤貧瘠而歉收,或在戰亂時被兵馬踩死,人們時時刻刻面對飢餓的恐懼。然而,自從歐洲人發現美洲,從當地引進馬鈴薯後,情況改變了。
馬鈴薯比麥類更耐寒、更耐貧瘠,即使在嚴寒的挪威北端與庫頁島也能生長;它也比麥類更有熱量,以相同面積的農地種植馬鈴薯與麥類,收成後馬鈴薯所能提供的熱量是麥類的4倍以上。即使遇到戰亂,由於馬鈴薯長在地底,遭兵馬踐踏後所受的損害也比長在地面上的麥子少很多。
基於上述種種優點,18世紀起,歐洲國家開始政策性的推廣馬鈴薯。例如普魯士(現今德國的前身)國王腓特烈二世,強制農民種植馬鈴薯,糧食產量增加,人口穩定成長。1740年腓特烈二世剛即位時,普魯士軍力只有8萬人;但僅僅過了13年,1753年的普魯士兵力已達13萬5000人。
馬鈴薯的主食化,讓歐洲國家脫離飢荒,人口增長,並有餘力發展科技,於近200年成為先進強國。這段歷史啟發我們,主食的改革能為國家發展帶來多麼大的影響。
以古鑑今,現今台灣似乎只把馬鈴薯當「配菜」,缺乏「馬鈴薯主食化」的討論。反觀中國為了應對人口增加帶來的糧食需求,於2015年喊出「土豆(馬鈴薯)元年」口號,把馬鈴薯列為繼稻米、小麥、玉米之後的第四大主糧,全力推廣馬鈴薯的種植與食用。
馬鈴薯雖為溫帶作物,卻適合冬天種在台灣中南部,雲林、嘉義、台中皆為主要產地。2020年,台灣的馬鈴薯種植面積達2600公頃,產量突破5萬噸,可見台灣並非不適合種馬鈴薯,或許也可討論「馬鈴薯主食化」的可行性。
以馬鈴薯拯救歐洲的歷史,啟發馬鈴薯主食化的討論,就是歷史切入農業議題的例子。其他例子更不勝枚舉:蔗糖的歷史,可敦促我們關心中南美洲蔗田的血汗農工(相關文章:〈為什麼聖經裡沒提到糖?〉https://www.newsmarket.com.tw/blog/120901/);甚至讀《封神演義》武王伐紂的故事,也可聯想糧食議題(相關文章:〈武王信仰背後的糧食議題:武王伐紂是搶糧戰爭?〉https://tian-di-ren-tao.blogspot.com/2023/07/5.html)
可惜台灣的歷史教育,以「政治史」為主,缺乏「農業史」的探討。即使我大學時代讀歷史系,打開琳瑯滿目的課程列表,就是沒有「農業史」。翻開國、高中的歷史課本,某朝代的某皇帝做了啥事,誰推翻了誰,xxxx年發生了什麼戰爭或叛亂,許多年輕學子的感想是:與我何干?
當然,傳統歷史教育講的朝代更迭、歷史事件與文化變遷,確實有意義與價值。只是歷史的探討若停留於政治、文化層面,沒有貼近我們的產業與生活,不談我們的農業、飲食如何變成今日模樣,人們對歷史的刻板印象永遠只是不實用的有趣故事而已。
期許台灣的歷史教育能多一些農業、糧食的探討,不但使我們更了解餐桌上的食物怎麼來的,更能為農業議題提供更廣闊的視野、更多元的靈感。
延伸閱讀:本文提到的馬鈴薯歷史,參考自:酒井伸雄著,游韻馨譯,《扭轉近代文明的六種植物》,台北:馬可孛羅文化,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