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種植我們的食物?「如何」種?「在哪」種?「誰」吃得到優質、乾淨、公平的食物?美國食物正義運動發起人羅伯.高特里布(Robert Gottlieb)及推動者阿努帕瑪.喬旭(Anupama Joshi) 所著《食物正義》一書,追溯食物走過的路徑,從餐桌、市場、大賣場,一路回到世界農場。不妨自這些他山之石,反省、改革台灣的食物系統,「公平對待每個環節,我們才能獲得好食物」。
(以下內容摘自《食物正義:小農、菜市、餐廳與餐桌的未來樣貌》一書,文字經早安財經文化授權。文中小標由《上下游》另行編輯,與原書無涉,更多精彩內容請詳見該書。)
.jpg)
不正義的食物鏈:食品業巨獸的興起
美國家禽農場的工業化,早已廣為人知。1980 年代初,當麥當勞開始計畫推出麥香雞時,就決定與泰森食品公司合作。泰森原本只是一家純粹生產雞肉的業者,後來成了食品業的巨獸,甚至開發出一種新式產品——重組肉,並開啟了農場、製造商、工廠工人及速食業之間關係的重大改變。
看泰森的發展,可以讓我們理解這個不正義的食物鏈如何演化。這家阿肯色州公司發跡於大蕭條時期,當時公司的創辦人約翰.泰森 (John Tyson) 向其他農場主收購雞隻,然後賣到芝加哥賺取利潤。1957 年建造了第一座加工廠,並靠收購較小的公司和採用工業生產方法繼續擴張。這些方法包括使用家禽類 CAFOs(concentrated animal feeding operations, 集中型動物飼養經營),把好幾千隻的雞塞進小小的空間飼養,通常是無窗的棚舍、箱式鐵籠、母雞狹欄或其他設計,總之都是禁閉式空間。雞隻通常無法移動或轉身,要靠抗生素才能活下去。
隨著泰森事業版圖擴大,逐漸透過與雞農簽約的方式,掌控下游運作。這些下游雞農本來就收入微薄,如今更被高度剝削。至於泰森自己的加工廠,因為工資低廉、工作環境危險,加上苛刻虐待員工,流動率高達 75%。

大型肉品業者壓榨雞農,也對環境造成破壞
1970 年代,泰森開始多樣化產品線,生產高達數十種產品──從雞肉火腿、雞肉熱狗、裹麵粉的雞肉餅到 Chick’n Quick 牌炸雞塊,還要加上跟麥當勞簽約後無處不在的麥克雞塊,以及眾多加熱即食的熟食類品項。到了 1990 年代,泰森更是全球化,在墨西哥、中國和南亞成立合資企業和工廠,最後擴展到九十多個國家。今天的泰森,是全世界最大的雞肉生產商,2001 年購併 IBP 公司後,也晉身為全世界最大的紅肉製造商。
另外還有一家 IBP,原名愛荷華牛肉加工公司,與泰森一樣,也是肉品業的巨獸。該公司起初賣薄利的批發肉塊,後來賣「分類包裝牛肉」或「現成切好」的牛肉部位給連鎖速食店和超市。這些產品深受沃爾瑪青睞,因此這家零售業龍頭也成了 IBP 的大主顧。對沃爾瑪來說,切好密封包裝的肉品完全符合它所想要的低成本策略,把切肉師傅換成搬貨小弟,工資就少了三分之二。
這些業者的大幅擴張,也讓他們成了「食物不正義」的主要推手。與泰森簽下合約的雞農被壓榨,淪為無權無勢的約聘工人,供應泰森龐大的需求。根據一項估計,這些約聘農民中高達71% 賺取的工資低於貧窮線。整個泰森企業雇用的工人在 10 萬名以上,其中許多人面對的是嚴重的健康影響及危險的工作環境。CAFOs 對環境的破壞也變得顯而易見,包括對水和空氣品質的廣泛負面影響,而幾乎所有這些運作都落在最貧窮地區。

加工食品大肆廣告,其實都是糖油鹽
與此同時,現代食品業者的強力行銷,也大幅改變了零售市場所販賣的食品樣貌。各種高度加工食品的普及化,使得美國人的日常飲食中,糖、脂肪和鹽分的攝取量快速上升。
1920 年代後期,一般商店平均賣 870 款產品,1950 年代初增加為 4 千多款,到了 2000 年暴增至 3 萬至 4 萬多款。光是 2005 那一年,就有 18,722 項新食品和飲料上市。其中許多「新」產品,都只是既有產品的小改款(例如同樣是奧利歐夾心餅乾,只是換了糖霜顏色),而且高達三分之二的新產品會在一、兩年後從市場消失。
「多國本土化、全球在地化」之名,毀小農生計
直到二十世紀初,美國商品如小麥、麵粉、棉花和菸草的出口,是美國經濟發展的重要驅動力,借用美國農業部分析師約翰.康諾 (John M. Connor) 與威廉.薛克 (William Schieck) 的話來說:「對國家資本的形成,貢獻良多」。但自 1920 年代起到 1960 年代初,雖然美國像聯合果品一類的食品公司生意擴及全球,但美國本身卻一直是食品進口超過出口的國家。後來透過積極推動出口,才順利將生產過剩的農產品外銷到其他國家,並打造出一個新的「全球食物系統」。
這個全新的全球食物系統時代,是一個出口導向的時代,不管是農業生產者、農藥製造商、食品零售商、連鎖速食餐廳和食品製造商,全都在多元性的全球市場攻城掠地。他們改變口味,創造新的食物偏好,把食物變成全球性商品。在此同時,食物生產和運銷成了多面向的全球事業,從供應鏈、農產品到食品零售,都在先進國家與開發中國家之間雙向流動──美國人的晚餐裡有中國蒜頭,中國消費者吃到美國食品公司用中國栽種的馬鈴薯製造的洋芋片。
後來,隨著這個食物系統不斷演化,全球化的食品業者不再把同樣的食品賣到不同的市場;相反的,他們逐漸學會標榜在地特質來討好市場,例如採購一些在地原料或聘用在地人為分公司負責人。這種策略叫做「多國本土化」(multidomestic) 或「全球在地化」(glocalization),例如麥當勞法國分公司的總裁就自稱他管理的是一家「多國本土化」公司,而不是「跨國企業」。
來自世界各地的食品(如樂事洋芋片),則取代了當地的傳統食品(如玉米餅)。「在地農業與在地料理之間淵遠流長的連結,已經被遠在其他國家的消費需求所取代,」哈麗葉.佛里德曼說:「一個地方盛產什麼農作物,不再等於當地人愛吃,而是代表著那些農作物的生產對跨國企業的營運最有利。」

CSA模式:你來當股東,我種菜給你吃
有一種值得一提的新農耕方式,叫做社區支持型農業(community-supported argiculture,簡稱 CSA)模式。
CSA 起源於日本和歐洲,是專為保護小農而設計的一套計劃。CSA 農場的會員(也可以叫股東)要預付一筆農場運作的預估成本和農民薪資,而農民在每一次採收後,都必須將收成分給這些會員,通常是一籃當週採收的食物。如果天候不佳造成歉收,會員與小農要共同承擔損失。這套做法為小農們克服了一個雖不大、但很重要的難題:價格波動。慢食運動的發起人卡羅.佩屈尼(Carlo Petrino)稱 CSA 的會員為「共同生產者」,而「吃下」食物的那一刻,算是「生產流程的最後一個階段」。今天,CSA 模式在美國只有 25 年歷史,但已展現重大成效。史蒂夫.麥克費登 (Steve McFadden) 寫過大量文章談 CSA,認為「CSA 已開枝散葉到社會各個階層」。
CSA 的初衷,與農夫市集相似,就是提供好食物給弱勢族群。最有效達成這個目標的 CSA,是由非營利組織經營的,他們一方面提供就業機會給年輕人、培訓失業者,另一方面提供新鮮農產品給食物銀行,並讓在地農場有場地可以銷售農產品。此外,CSA 還協助農地保育工作,讓好食物補給線不致突然斷裂。

別讓在地、有機成了大財團的「漂綠」工具
近年來,在地飲食也成了很多跨國大企業愛用的「漂綠」工具,例如前面提到的百事公司、沃爾瑪及麥當勞。
「在地飲食」之所以會成為這些企業的行銷噱頭,部分原因是在地食物日益受到歡迎。食品行銷協會調查發現,將近四分之三的受訪者說自己會定期購買在地種植的產品是因為產品新鮮,而75%的受訪者則是因為覺得這樣做可以支持在地經濟。
餐飲業協會於 2009 年進行餐廳顧客意見調查發現,高達 70% 的受訪者「比較可能去供應本地食物的餐廳。」今天,有越來越多的學校與餐廳直接將在地種植的水果和蔬菜印在菜單上,2009 年學校營養協會調查指出:「37% 學區供應在地水果和蔬菜,另有 21% 學區正在考慮跟進。」
食物正義關注的在地飲食,不只是食物從哪裡取得或如何種植,而是涵蓋什麼人在什麼狀況下用什麼方法種植、收成、加工、運輸及出售,也就是所謂的正義取向價值鏈 (justice-oriented value chain)。 另外,食物正義也努力建立所謂的「國內公平交易」(Domestic Fair Trade) 的認證程序,將在地、有機及永續食物納入公平交易的範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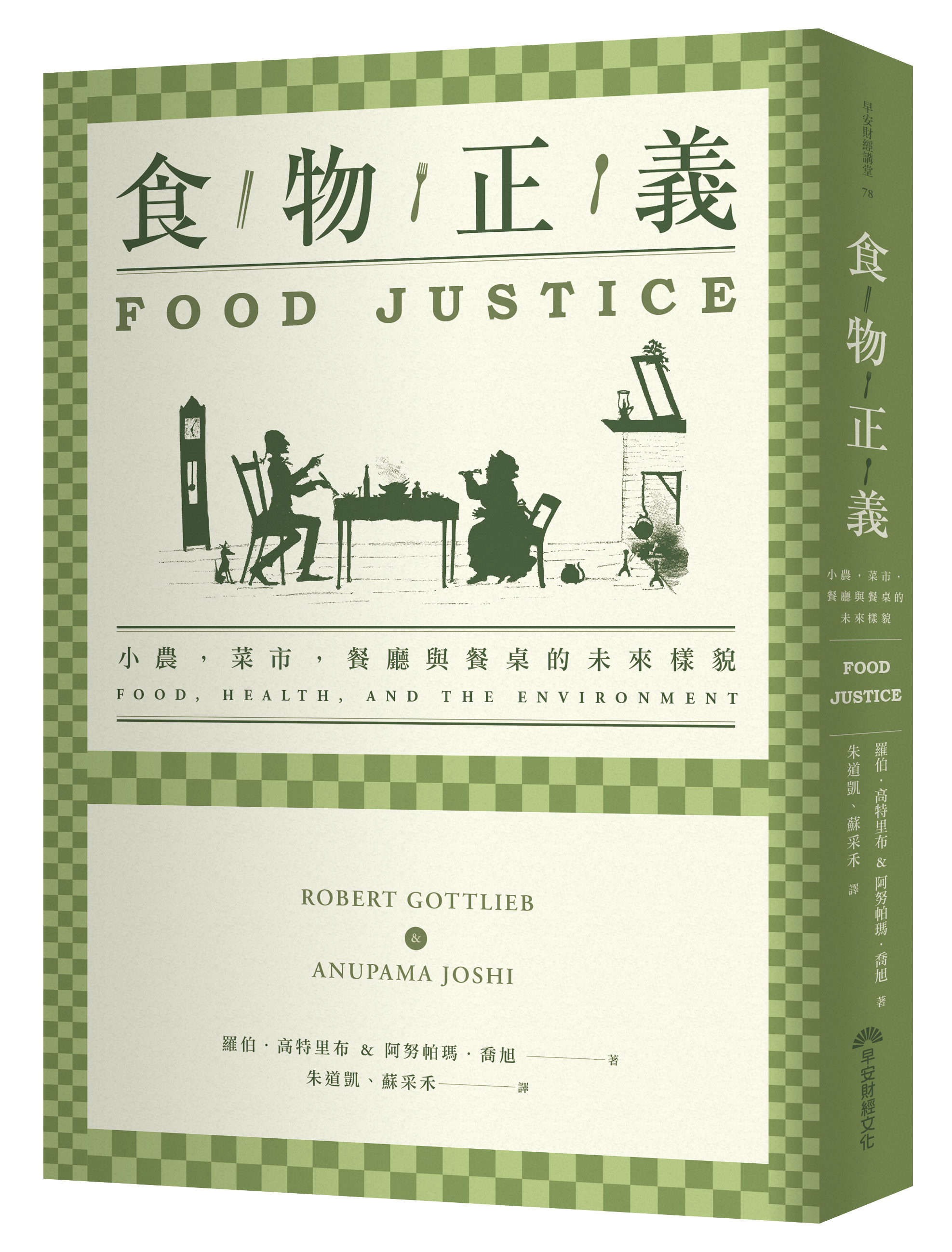
延伸閱讀












可能要先把那些無法在地完成生命循環週期的,都扣掉! 包含,原本每年只能生長一輪的! 其實不可能四季都是生鮮! 以及,其實根本就是與相關經濟生物一起抵達異鄉的人類! 就真的不要假裝在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