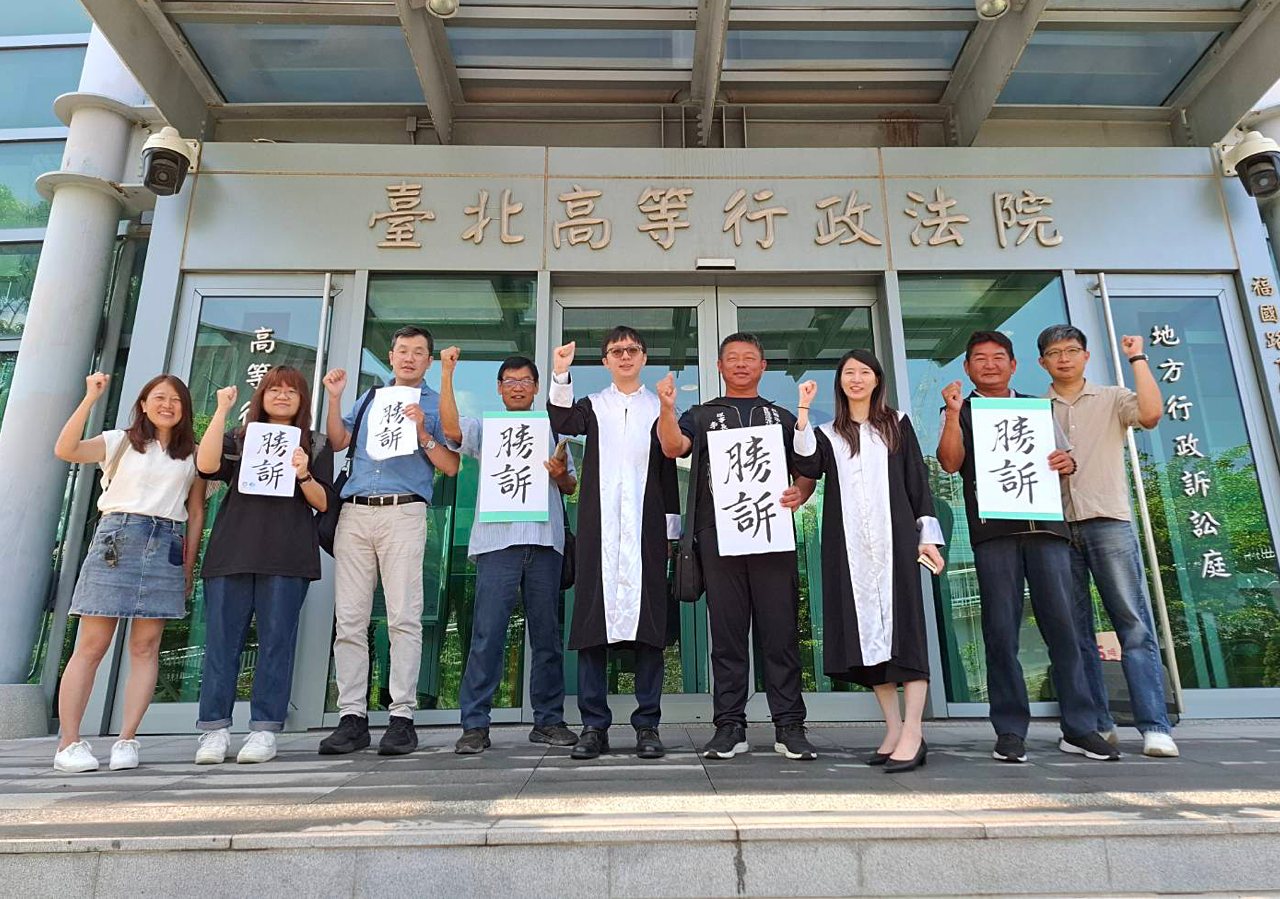紐西蘭液態乳即將叩關,零關稅牛乳將如何衝擊台灣消費市場,還在未定之天。不過外患未至、內憂已生,疫情後國產鮮乳銷量大減,但產量卻是歷年最高。值此存亡時機,自有牧場的四方鮮乳酪二代蔡佐鴻大方分享他們的因應之道。
教人遺憾的是,這個因為創辦人太過「天真」而成立的牧場,過去 30 年雖然「關關難過關關過」,但近三年營收掉了近三成,面對寒冬卻缺少爐火,前景不容樂觀。
「冬季剩奶」是乳品廠最頭痛的問題
與蔡佐鴻相約「四方鮮乳故事館」── 牧場為開闢觀光路線而設置的場館── 他負責的乳品加工廠就在故事館旁,弟弟蔡銘晃則主理六公里外的四方牧場。一個管奶,一個管牛,家業就在兩個人的肩膀,愈來愈沉重。
在外人眼中,四方既有乳牛、又有鮮乳品牌,還透過直銷掌握消費者,一條龍式的營業有無限風光。不過蔡佐鴻坦言,為了處理「冬季剩奶」,四方費盡心思,甚至必須「割肉」求生,所謂風光都是表面,肚子裡實是苦不堪言。

原來鮮奶用量在冬季與夏季有很大的落差,但乳牛是全年都在泌乳,「冬季剩奶」是所有乳品廠最頭痛的問題。蔡佐鴻並透露,牧場規模愈大,冬奶的壓力就愈大,紐西蘭與澳洲之所以是全球最大的奶粉出產地,正因為他們的冬奶量全球最多,「只好噴霧乾燥變成奶粉」。
四方牧場剛成立時,生乳交給苗栗農會的「將軍鮮乳」,因為是保價、保量收購,冬奶的壓力在乳品廠。不過後來四方成立自己的乳品廠,「我們從第一天開始,就設法把冬奶轉化成產品,而且也知道產品多元化才有辦法把冬奶去化掉」。
乳品廠成立第一年就靠鮮乳饅頭用掉冬奶,饅頭廣受好評,後來他們自己蓋食品廠,省掉代工費用。這幾年,四方又投入起司製作,蔡佐鴻說,高達起司需要半年熟成,他們冬天製作,夏天販售,目的也是為了消化冬奶。其他產品包括冰淇淋、鮮奶吐司,「我們整整花了十年的時間,才把冬季剩奶的問題解決掉」,回首來時路,蔡佐鴻表情凝重,壓力不言而喻。

台灣鮮乳的盛世與眼前的內憂外患
蔡佐鴻分析,台灣的鮮乳市場經過兩次大震盪,2008 年中國爆發三聚氰胺「毒奶粉」事件,台灣店家為求自清,紛紛宣稱「不用奶粉、只用鮮乳」,讓鮮乳用量一飛沖天,生乳量的高峰約在一年 35 萬噸。
2014 年味全的食安風暴讓產業大洗牌,全民拒喝味全鮮乳,義美趁虛而入,「加價購」爭取酪農,從原本的小廠一舉晉升為全國第三大。義美進廠攪亂一池春水,各大乳品廠為了「搶奶」,只得跟進「加價購」,讓酪農忽然間多了一大筆收入,於是不斷擴場、增產,生乳量的高峰衝到一年 45 萬噸,蔡佐鴻稱「那是台灣酪農的黃金盛世」。
紐西蘭液態乳即將零關稅進口,這會是台灣酪農業的另一場風暴嗎?蔡佐鴻直言,紐乳的影響力有多大,業界都還在觀望,「畢竟消費者的手要伸向架子上的哪一瓶鮮奶,現在誰也不知道。」
眼前的困境是外患未至、內憂已生,疫情後台灣經濟力大幅下滑,消費者愈來愈保守,許多「鮮奶族」改為「豆漿族」或「奶粉族」,國產鮮乳銷售量已經明顯下滑。若還是早年的一年 35 萬噸生乳,或許市場還可以胃納,但產量被撐大變成一年 45 萬噸,各乳品廠都叫苦連天。農業部試圖「勸退」某些酪農,也是基於「降低乳量」的考量。
從成衣業轉為酪農,衝太快導致賠本
聊到四方鮮乳的發展歷史,蔡佐鴻以「三個天真」來形容父親的決定。四方成衣是台灣的老品牌,創辦人蔡南經營成衣代工、外銷,生意做得呱呱叫!1980 年代,因為美國 301 條款,台幣大幅升值,加上中國市場開放,當地廉價的勞力讓轉移到中國的台商更有競爭力。蔡南不願離開台灣,但事業需要轉型的急迫感愈來愈強烈。
1989 年,四方牧場成立。從操作縫紉機到養牛擠奶,事業大轉彎,全因為蔡南的「天真」,他從朋友處得知,乳品廠保價收購生乳、價格又是農委會訂定的,雖然畜試所因為養牛太辛苦一再勸退,但「完全不必開拓市場、也不必擔心價格崩跌」,這麼容易做的生意,讓他一意往前衝。
當時全台灣約有 1200 個酪農戶,每戶平均飼養 40 至 50 頭牛,蔡南認為,擴大規模才能降低成本、更有競爭力,因此四方牧場一開始就以 300 頭牛的規格進場。但他不知道,多數酪農選擇養 40 至 50 頭牛是因為兩夫妻的家庭來照顧剛剛好。300 頭牛需要聘僱七名員工,人事成本比家戶型酪農高了好幾倍;同時,因為酪農間彼此不具競爭關係,大家會互通有無,所以飼養成本都差不多,並不會因為規模大而獲得優勢。

牧場賠不夠,乳品廠來賠湊一對
300 頭牛的生乳交給苗栗農會的「將軍鮮乳」,雖然是保價收購,但四方因為飼養的成本過高,賠本五、六年。蔡佐鴻說,父親的第二椿「天真」是繼續砸錢設立乳品廠,希望靠自己的品牌來回本。
蔡南認為,他用單一乳源,只要牛隻吃得好,自然會有好奶,「好奶就會有識貨人」,當時台灣經濟正在起飛,鮮奶消費市場也在成長,幾千萬元的投資絕對值得。
生乳變成鮮奶需要殺菌,國際間通用的方法有兩種:130-135°C 殺菌 5 秒鐘的 UHT 法,以及90°C 殺菌 14 秒的 HTST。蔡佐鴻分析,高溫殺菌會讓生乳產生梅納反應,略帶焦糖味的濃醇香印象就是這樣來的,台灣大廠也都採用 UHT 法。
但是因為當時達官政要最愛喝的「初鹿鮮乳」採用 HTST 法,它殺菌溫度較低,代表生乳中的生菌數也要夠低,鮮奶才安全,四方蔡南對自己的生乳有信心。只是 HTST 鮮奶比較接近生乳的味道,與多數國人習慣的濃醇香不同,一開始就被消費者投訴是「摻了水」,「天真」的蔡南才知道「有錢人跟普通人要的不一樣」!
蔡佐鴻回顧,當時四方牧場一天出產 3000 瓶鮮奶,但他們一個月都賣不了 3000 瓶,想要回頭找「將軍」收購,他們當然不願意。還好兩個月後是夏季鮮奶用量高峰,四方的生乳被大廠接手,才渡過危機。

長期配送制 + 有機通路,慢慢站穩腳步
四方一邊交奶給大廠,一邊慢慢找出品牌的利基,蔡佐鴻憶道,與大品牌競爭 B to B 的紅海市場太辛苦,他們跟嘉南羊乳學習業務模式,挨家挨戶去掃街,客戶再介紹客戶,透過「長期配送」,反倒經營出一條小眾市場。客戶喝慣了四方的鮮奶,也會順道買饅頭、起司,因為配送到家的服務把客戶寵慣了,因此產品售價雖然略高,但看在方便又能支持本土的前提下,直購的市場還算穩定。
此外,主婦聯盟成立後曾經觀察四方鮮乳長達一年,決定讓四方鮮乳上架。雖然當時主婦的站點不夠多,但其他通路有樣學樣,也開始販售四方鮮乳,讓四方鮮奶成為有機通路中的第一品牌。儘管如此,四方的乳量仍不及全台灣的 1%。
蔡佐鴻這樣說明差距:四方有 20 輛冷鏈配送車,但某大廠有六個配送站,每個站都是200 輛貨車。規模小歸小,四方的每一步都十足十做到位。例如他們想做起司,就是整個工廠含環境參數都從歐洲買回來。他提到許多酪農或許想要踏足起司,但技術不到位、設備又有落差,簡單來說就是不願先投資,自然容易失敗。

與其想破腦袋開源,節流更重要
冬天是鮮奶低消費期,但生乳生產量反而多;乳牛在夏天泌乳量少,台灣夏天鮮奶自給量確實不足,蔡佐鴻直言,現在四方的奶要配合大廠的銷售狀況,「大廠雖然願意收生乳,但要求『冬夏比』」,夏季交夠多的奶,才能決定收多少冬乳。
雖然夏天台灣的鮮乳自給率不足,國產鮮乳有多少就可以賣多少,但四方必須拉高夏奶交給大廠的量,以求得大廠多幫忙處理一些冬奶,「等於是割肉求生存」。更何況今年連夏奶都有剩奶,未來乳品廠收奶量可能會再緊縮,四方及其他酪農都非常緊張。
面對不景氣的市況及未來紐乳的變數,蔡佐鴻建議,與其投資各種產品開發,酪農更應該著力在降低成本。四方利用「小地主大佃農」制度取得苗栗後龍 80 公頃的土地種植盤固拉草,再透過青貯的技術保存草料,每個月可以省下 80 萬元的進口牧草費用。

費盡心思與努力,業績仍舊掉三成
遺憾的是,儘管做了所有的努力,四方近三年的銷售額還是掉了近三成。蔡佐鴻語帶唏噓提到,四方的每個轉型雖然都踢到鐵板,但天公疼憨人,他們一個難關一個難關踏實地突破,好不容易在台灣酪農業的盛世中站穩腳步,沒想到盛世結束得不僅倉促,而且很可能緊接著就是寒冬。
蔡佐鴻提到,四方現在的廠長、課長等幹部都是一開始就跟著父親打天下,俗諺說的「頭已經洗下去」就是指他們這種情況,「現在只求存活,讓老員工有所依靠」。天公會繼續疼憨人嗎?蔡佐鴻也想知道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