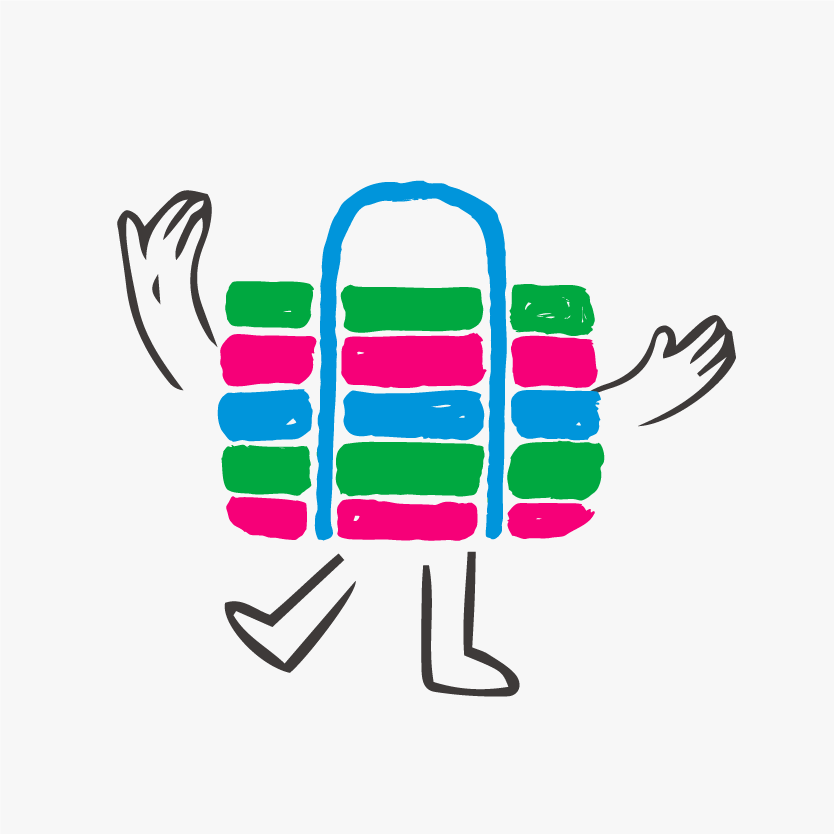候鳥如何飛行遷徙千萬里?這是科學家們一直想解開的謎題。有些候鳥從加拿大直飛委內瑞拉──相當於連續跑 126 場不吃不喝不休息的馬拉松;有些鳥類在九天的不間斷飛行中穿越太平洋,牠們幾乎沒有時間睡覺,於是一次讓一半的大腦睡個幾秒,交替進行;還有些候鳥遷徙前會囤積大量脂肪,體重在幾週內增加到兩倍以上,此時的血液化學神似糖尿病和冠狀動脈心臟病患者,不過牠們卻健康無虞,真教人讚歎大自然的不可思議。
然而,這些神奇的小傢伙們具備的「超能力」,卻沒有辦法減緩牠們消失在地球的速度。請跟著普立茲獎決選作家史考特.韋登 (Scott Weidensaul) 親見鳥類遷徙之美,一起來思索如何讓這樣的美維持下去。
(以下內容摘自《候鳥長征:一場飛越世界的奧德賽之旅》一書,由商周出版授權,文中小標由《上下游》另行編輯,與原書無涉,且為閱讀需要調整部分擷取內容,更多精彩文字請詳見該書。)
候鳥如何長途飛行?微型化科技幫助科學家研究
將近一世紀以來,科學家要是想釐清鳥類飛到何處,只能仰賴替鳥繫上有數字的輕便腳環,然後期待有人再度遇見這隻鳥。繫放仍然是研究候鳥的重要方法,比方說過去一百年來共繫放了七百萬隻綠頭鴨,其中有一百二十萬隻被再度記錄(大多由獵人發現),提供的資料對水禽族群的管理大有助益。
既有的繫放與觀察資料顯示,灰頰夜鶇遷徙的距離特別長。即使體重只有三十克,牠們仍然有本事從阿拉斯加北部和加拿大亞寒帶的針葉林與樹叢地飛到南美洲,每年往返。有些灰頰夜鶇會連續飛行六百英里穿越墨西哥灣,另一些沿著佛羅里達長長的手指狀陸地往南,再飛越加勒比海。到了冬季,牠們會隱身於南美洲北部的雨林裡,然而牠們究竟飛往那塊廣闊大陸的什麼地方?我們只有非常粗略的概念。
就在大家設法透過繫放填補知識空缺的時候,新的微型化科技也為候鳥研究開啟了令人振奮的視野。我們所用的地理定位器,只是那些能徹底改變候鳥研究的追蹤設備當中,比較平價小巧的一種。衛星發報器每件動輒四、五千美元,對小型鳴禽而言也太重了;相較之下我們用的地理定位器不到一克,一個也只要幾百美元。我們的團隊由國家公園管理局的生態學家卡蘿.麥金泰爾(Carol McIntyle)帶領,正著手進行一項多年計畫,想追蹤德納利和公園內候鳥所飛往的天涯海角之間的關聯。地理定位器提供了史無前例的良機,讓我們得以追蹤這些鶇實際上的飛行路線與目的地。

左右腦輪流睡、肥胖也不會生病,候鳥遷徙本事大
科學家發現候鳥啟程之前,不必勤加鍛鍊就能增加肌肉,真希望人類也有這種能力!
鳥類的肌肉組織和人類幾乎相同,因此必定是透過某些生化反應促進增生,而其中機制仍然是一個讓人心癢難耐的謎團。候鳥遷徙前也會囤積大量脂肪(許多鳥的體重甚至能在幾週內增加到兩倍以上),無論從什麼角度看來都極度肥胖,此時的血液化學也神似糖尿病和冠狀動脈心臟病患者,不過牠們卻健康無虞。
此外,候鳥還能持續飛行好幾天,不受睡眠剝奪所苦,牠們飛越夜空的時候,可以讓半邊大腦(以及連動的那隻眼睛)關機一、兩秒,左右腦輪流休息,白天則進行幾千次為時數秒的短暫睡眠。研究人員發現了幾十種像這樣的奇特方式,讓候鳥得以應對長途飛行衍生的壓力。
科學家愈是理解鳥類的遷徙能力,我們也愈是清楚候鳥面臨的生死難關(而且日益險峻)。牠們可是每年都會完成兩趟不可思議的遷徙壯舉。這二十年來,大家才發現人類遠遠低估了鳥類純粹的生理能力。
北極燕鷗遷徙能耐仍舊是個謎
北極燕鷗(Arctic tern)一直是長久以來公認的長途遷徙冠軍,這種淺灰色的海鳥體型和鴿子相近,會在北半球最高緯度的區域繁殖,卻到非洲、南美洲和南極洲之間的南冰洋過冬。只要在地圖上畫出牠們的航線,即使是隨手在餐巾紙上計算,也不難得出世世代代鳥類學家的結論:北極燕鷗每年遷徙的距離是兩萬兩千到兩萬五千英里。數據純屬推論,因為以前的追蹤設備不夠小,像燕鷗這樣纖細的鳥類無法攜帶。然而當發報器和記錄器愈做愈小,足以應用在其他體型大一點的海鳥身上時,北極燕鷗「推論出的」遷徙紀錄很快就被打破了。
北極燕鷗有兩條截然不同的南遷路徑,但無關牠們來自哪個族群。有些北極燕鷗先向東飛往非洲西北突出的陸地,接著繞回大西洋最窄的地方,抵達巴西沿岸,再沿著南極半島飛往威德爾海(Weddell Sea)。到了春天牠們會遷徙到南非外海,再度橫越大西洋飛往南美洲北部,最後才飛往北大西洋,整趟旅程是一個八字形,由振翅不息的羽翼銘刻在地球上。
基於某些原因,同一個繁殖族群裡有些北極燕鷗反而幾乎都沿著非洲海岸飛行,到了好望角附近才飛越南冰洋抵達南極海岸,或在高緯度的狂風巨浪中往東飛行幾千英里,抵達印度洋南部。
總而言之,伊恩的團隊發現,即使是最缺乏雄心壯志的北極燕鷗,每年也飛了至少三萬七千英里,有些個體每年則飛了將近五萬一千英里,再次打破了最長遷徙距離的紀錄,而且是科學家以往推論的兩倍以上。更厲害的是,三年後在荷蘭標記北極燕鷗的研究團隊發現,有些個體一年飛行的距離甚至高達五萬七千英里,牠們會飛往澳洲外海,並在印度洋集結(後來發現在緬因州標記的北極燕鷗也會聚集於此)。任何海鳥學家,尤其是一兩杯啤酒下肚之後,都會坦承沒有人真的知道北極燕鷗遷徙的極限究竟在哪裡。
中繼站的品質攸關候鳥的生存
牠們的確分秒必爭。大部分的鳥兒已經飛了數千英里,從澳洲西北部的八十英里海灘(Eighty Mile Beach)或紐西蘭的泰晤士峽灣(Firth of Thames)等南方國度遠道而來。牠們在一兩週內,又要前往俄羅斯遠東的堪察加、阿拉斯加西部的育空三角洲,或西伯利亞極圈內的安茹群島(Ostrova Anzhu)。
每年大約有八百萬隻遷徙性水鳥經過黃海,利用像在東凌(Dongling)的這種泥灘沼澤休息補給。我眼中空空如也的泥灘,地表下其實就是多毛類、雙殼貝、螺類、小型甲殼類和其他各種海洋無脊椎動物的大雜燴,對飢餓的鳥類而言堪比自助餐。
研究候鳥的科學家把這些關鍵驛站稱為中繼站,又餓又累的鳥兒在此歇腳,養精蓄銳。生態保育學家近幾十年來才完全確定保留中繼站是最根本的要事,雖然任何人,只要曾經規劃過橫越全國的公路旅行,設法搞清楚該在何時何地停下來加油、食宿,一定都能理解這個道理。
中繼站的大小和品質各異,鳥類學家打趣地把它們歸類成「緊急逃生梯」、「便利商店」和「五星級飯店」,即使它們對候鳥存亡的重要性可不是開玩笑的。就像車潮能反映高速公路休息站的優劣,上好的中繼站只要擠滿候鳥,便代表此地食物不但豐富,盛產的季節也恰逢所需,環境安全無虞,又有充裕的活動空間;而這些候鳥也演化成必須仰賴通常相距甚遠的中繼站。
中繼站大多位於考驗候鳥生理極限、難以克服的地理屏障前後,例如撒哈拉沙漠南端是向北飛的鳴禽短暫歇息的最後機會,牠們接下來得先通過廣大的沙漠,再飛越地中海才能抵達歐洲;或者新英格蘭的灌叢與沿岸沼澤:鳴禽和水鳥接下來要飛一千英里橫越大西洋西部,再借助東北信風飛一千英里,才能在委內瑞拉或蘇利南的海邊降落。每條航線、每個遷徙路徑都有這種瓶頸要塞,但如果綜觀全球,黃海無庸置疑是最關鍵的中繼站,攸關更大量、更多鳥種的存亡。

候鳥的未來掌握在人類手中
黑夜似乎還逗留在松樹幽暗的陰影裡,我瞥見地面附近有個拘謹的身影,於是拿起雙筒望遠鏡──灰頰夜鶇水彩渲染似的胸口羽毛和棕色的身軀映入眼簾。牠在幾碼外狐疑地打量我,輕輕發出警示叫聲。然而鳥為食亡,牠顯然又認定我沒那麼邪惡,轉身繼續踢動松針,搜尋筋疲力盡飛行十二小時後的第一餐。

這隻灰頰夜鶇的翅膀覆羽末稍是淺色的,代表牠還是幼鳥,這是牠第一次遷徙。牠很可能出生於紐芬蘭或拉布拉多北部的雲杉林,和我們在阿拉斯加標記的灰頰夜鶇隔了整個大陸的距離。但我仍然萌生同樣強烈的渴望,很想像我們研究德納利的鶇類那樣深度認識牠。這隻灰頰夜鶇不但是熱鬧的早晨中熙來攘往的眾多候鳥之一,還是獨立的個體,擁有超凡獨特的一生。
牠是一隻非常普通,卻又不平凡的鳥,就像每隻躍入未知的候鳥那樣,牠受本能指引,承襲百萬代先祖的含辛茹苦,任憑無情的天擇所形塑;牠飛越蒼穹,歷經我們難以理解的險阻,憑藉幸運的機緣和強大的耐力度過千鈞一髮,仰賴自身肌肉和羽翼的力量飛過千山萬水。無數個紀元以來,往往如此就足以讓牠們成功遷徙。然而好景不常,候鳥的未來是福是禍,都掌握在我們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