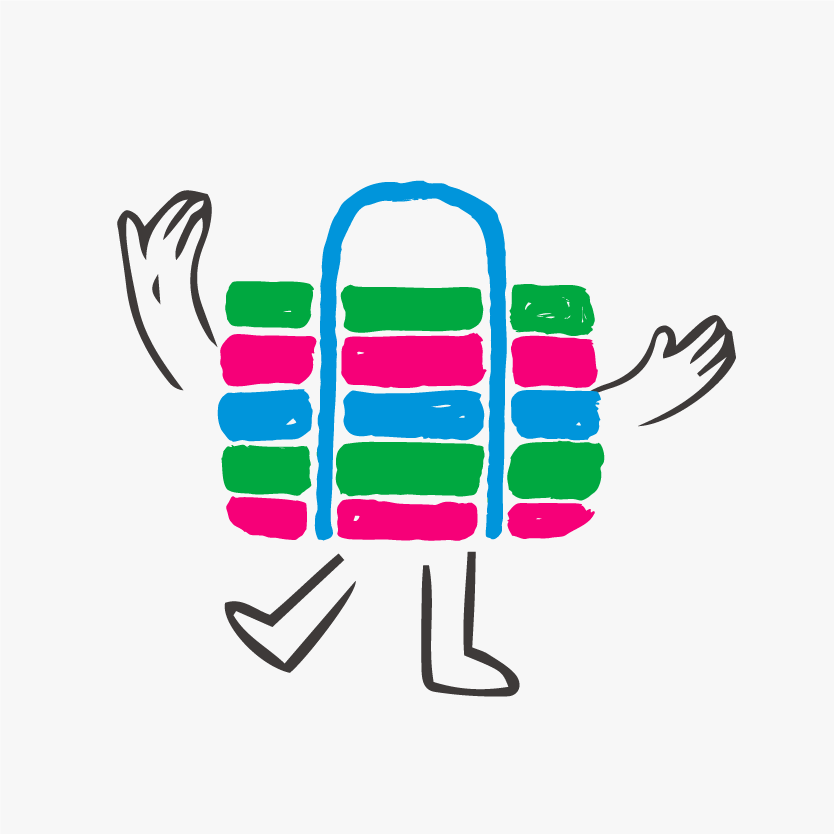三月下旬,我到美國丹佛參加應用人類學第73屆年會,本次的主題是「21世紀自然資源的分配與發展」,而「糧食」是其中一個重要子題,網羅了大量研究成果,範圍涵蓋糧食安全、健康、營養、認同、教育及反資本主義體系的食物生產等,而「在地食材」(local food)概念貫穿於各研究間,成為思考21世紀糧食議題的關鍵字。會後,我行旅美國西南地區克羅拉多州及新墨西哥州,時正值初春新耕之際,親眼見到美國式的工業化農業,因而對當今飲食全球化及地食材運動的意義有了更深的體悟。
美國式工業化農業
春天,山上的積雪未融,但農業及畜牧業興盛的科羅拉多平原已開始甦醒,大型的灌溉機械手臂在一望無際的乾燥土地上,滋養出一片又一片圓形的綠色農田,有如工廠般的巨型穀倉矗立於平原間,這是美國工業化農業的一景。
1960年代,諾曼.布勞格研發出新的高產量和抗病蟲害小麥品種,帶動了第一次綠色革命。此後,雜交配種的技術不斷研發,使作物更適合集約式密集耕種,而擁有廣袤國土的美國,搭配高度機械化的耕作技術,一躍成為農業輸出大國。美國超市可說是美式食品帝國的展示場,一望無際的食品陳列架,彷彿訴說著這個國家食物豐沛,然而仔細觀察卻可發現,大部份的食物出自少數幾家托拉斯企業,生鮮或加工品皆然。
超市裡看不到「在地食材」,食品經過長途跋涉,從產區到達各大城鎮,冷藏及保鮮劑技術,讓陳列架上的蔬果「看起來很新鮮」;詭異的是,以食品添加劑製作的飲料和加工食品比生鮮更便宜。在超市中也看到有機農畜產品,不過旅居美國的友人說他從不購買,因為看來為數不少的有機品牌,其實總歸都屬那幾家食品大企業的子品牌,而他們也同時生產慣行農作物。「有機只不過是一種商業操作」朋友說。
研討會中,Mark Swanson博士發表他在肯德基州推動在地食材教育的成果,會中我請教美國是否如日本般為食育立法,與會學者一致搖頭,更有人大膽地說:「雖然歐巴馬非常重視食育,也推動鼓勵性質的政策或小型計畫,但這樣的法案絕不可能在美國通過,因為食品工業巨頭會率先出來反對」。深入美國日常生活才發現其飲食問題深刻,而對抗飲食工業巨獸的社區支持型農業、在地食材運動等,有如小蝦米對大鯨魚。

在地食材運動
2005年世界環保日,San Francisco 提出在地食材(locavore)的概念,倡議將環保的概念融入飲食。所謂的在地食材指的是由家庭菜園或在地生產單位生產的食材,它強調地產地消,降低運輸對石油的消耗與空氣污染(減少碳足跡);也倡議串連在地的「生產-製造-消費」供應鏈合作,促使消費端及製造端將所投入的每一分錢留在當地,協助生產端改善生產技術、進而提升農產品品質,有利於當地經濟發展。
倫敦新經濟基金會研究指出,每消費一元的在地食品,可為當地經濟創造倍數的收入,在地食材的採購,可創造在地就業機會。
在地食材概念提出後在飲食界掀起了一股「產地論」風潮,2007年牛津字典即把locavore列為年度風雲字。此一風潮也影響台灣,2012年取得碳足跡標示的台鐵便當,強調各站便當採在地食材,新鮮直送;南僑與嘉義縣合作,將柿子、山葵、黑木耳及虱目魚等嘉義在地食材,應用在餐飲、烘焙及冰品等產品的研發及製作;符節合令的無菜單料理興起;以及天下雜誌推出2013年新良食運動等。
近年來花東興起的「新野菜運動」,就是一種在地食材運動的展現,透過花蓮的「新野菜運動」,我們看到了「在地食材」在本土發展出的多元詮釋。
在地食材的環境意義
在地食材最容易被看見的是它的環境意義,關鍵字是「縮短食物哩程」與「低碳飲食」,野菜走進大眾消費市場,標榜的就是健康、無毒。「野菜就是要在自然的環境中成長,可是台灣這樣的環境太少了,過度酸化、鹽化,長出來都不健康,所以不要說只有野地生長的才是野菜,因為野地都是殺草劑,應該是經過人工照料的土壤,長出來的才是健康的野菜。」青陽農場復元生態系統,以模擬自然的方式培育野菜,不求產量,賣野菜不是真正的目的,環境教育才是其目的。
在地食材的文化認同意義
但是在地的阿美族不會只強調環保,因為文化與生態是不可分割的整體。原住民種野菜強調原生種的「作物種源」、父母傳授技術的「血緣傳承」和生態環境的「在地物質條件」三者之間的連結關係。正如同花田喜事農場的徐妍花小姐所言:「是媽媽要我一直堅持永續的,其實野菜還是要用我們原住民的種植,用自然農法,原生種的種植是媽媽要我一直堅持的」。原住民認為野菜作物的推廣不僅有益於生態環境的永續,透過食物也傳承了在地文化與族群認同。

在地食材的「新美食主義」
阿美族是台灣原住民族中最擅長食用野菜的族群,他們能辨識食用的野菜超過200種。2006年阿美族的吳雪月老師出版了《台灣新野菜主義》一書,介紹阿美族野菜的古老智慧與新吃法,開啟了社會大眾對野菜的認識,野菜跨越族群界線,成為觀光客造訪花蓮必嚐佳餚,野菜餐廳、野菜火鍋店逐一成立,原漢搶攻野菜市場。
拜訪青陽農場的時候,主人傅元陽正與一位前來尋訪在地食材的法式餐廳主廚談話,了解我的來意後他說:「她(餐廳主廚)來我這邊找在地食材,因為很多找不到的都在我這找到。你看那野菜拼盤,好的食材加上懂得食物美學就會做出好菜,其實就跟國王的新衣一樣……譬如說水田芥(西洋水菜)在台灣只能做火鍋,但在法國卻是高級食材。」
阿美族人蘇秀蓮成立的馬太鞍邦查農場也努力開發野菜市場,他們與原住民學院促進會合作推出野菜組合包,附上食譜讓都市消費者了解野菜的食用方法。花田喜事農場則採「產地直送」,到農夫市集與消費者面對面傳授「新美食主義」所必要有的新鮮、自然、健康與原汁原味要素。
在地食材的經濟意義
野菜餐廳及農夫市集點亮野菜的經濟價值,在地小農透過與餐廳契作或在農夫市集直接販售等友善的產銷關係建立,保障其收益。
花蓮農改場也注意到野菜的經濟價值,自2009年起投入野菜的品種改良,研發出抗病、適合大面積種植的野菜品種,以及具醫藥技轉價值的山苦瓜。農改場為國家設置,初始目的為協助農民進行經濟作物的大規模工業化生產,農改場與農民的互動,往往帶有公益服務性質,經常無償提供種苗或技術建議給農民。但隨著農業政策朝向農改場法人化,研究機構得自籌部份經費,甚至研發的衍生物也納入評鑑,這使得研發單位容易傾向以技轉產值為優先考量。
花蓮的小農擔憂將來一般農民拿不到改良品種,而出現大農場與藥廠壟斷新技術及市場的情形。另一方面,品種改良提升野菜的生產效率,大面積野菜農田的出現,讓小農擔憂量產帶來市場價格下跌的問題;外來種的野菜引進,讓原住民擔憂原生種棲地被侵佔問題。
在地食材的社會照顧意義
小型農場或許不能帶來規模經濟利益,但它的經濟利益體現在弱勢照顧上。馬太鞍邦查農場、花田喜事農場、吉拉卡樣有機共同農場等都以雇用在地單親、弱勢或失業家庭為經營理念。花田喜事農場徐妍花小姐用阿美族的文化意義mapulong ko orip(直譯:聚集/把/生命;意譯:把生命連結在一起)的概念,來解釋原住民有機共同農場的社會照顧意義。她說:
我們阿美族採野菜,不會一次只採一種,我們採很多種,每種只採一點點,然後全部放到鍋子裡一起煮,這個「一起」就是mapulong。然後我們吃的時候,大家一起吃,這也是mapulong,所以我們的農場就是把大家mapulong在一起,一起工作、一起享用食物、一起生活。
或許基於一種「後進」的學習心態,美國的糧食生產技術、飲食文化及各種革新被毫不反思地引進台灣,數十年來,台灣人在小小的島嶼上複製國土比我們大將近300倍的美國社會發展思維與進程。人與自然競爭、人與土地競爭、人與人競爭,污染、土石流、剝削弱勢,帶來了這塊土地的災難。
在原住民有機農場裡,阿美族的哲學直接洞燭現代化發展理論的矛盾。在台灣這艘船上的我們,都是mapulong,都是生命共同體。部落裡不談「有機認證」,也不懂「社區支持型農業」這些外來辭彙,因為媽媽教種植技術以及mapulong的共享智慧,比那些翻譯的、拗口的美國文化與技術更本土,更貼近族群的情感與心靈。
馬太鞍邦查農場照顧數個弱勢家庭
馬太鞍邦查農場蘇秀蓮正在做農事體驗教育
(本文曾刊載於農訓雜誌第27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