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裡,雨淅瀝瀝嘩啦啦落著,窗台邊時而亮起清脆的小雨聲,或是響起咚咚的大鼓雨聲,老天在鐵皮上譜了一曲。手機刺眼的螢光幕顯示著凌晨三點鐘,甚麼時候,我竟會被這樣的雨聲打醒,微微睜開迷濛的雙眼盯著沉沉的天花板,抓不太清楚我跟它之間的距離,進而將思緒飛向五公里外的鳳梨園。
基本上,我是個相當好睡又能睡的人,可說是天賦異稟。不論是九二一大地震,或是朋友在房間打著麻將,甚至坐著上下左右彈跳的吉普車駛在顛簸的林道,只要想睡,我就能睡。這老天給的好本領直到前陣子都還管用,殊不知,竟破功在這夜裡的一場雨。
可能,是心中有所牽掛了吧。
學生時期,對於雨天有點歡喜,悶熱的夏日午後常突如其來一場雷雨點綴著炙熱炎夏。首先,雲層開始堆疊,白天的明度頓時下降好幾階,空氣逐漸窒息,行人不安躁動著,然後,猛然起了一陣風帶來一陣傾盆,嘩的一聲,淋的眾人措手不及,像是老天不小心打翻了好大一桶水,來的快,去的更快,當世人正要困擾大雨時,上頭就停止了宣洩,當路人正要甩去雨傘上的水滴時,陽光早就調皮的露出光芒,半截彩虹偶爾掛在天邊。暫歇的城市又重心回到軌道,方才的雨宛如不曾發生的過去。我愛台南的雨天。
上到台北,雨天多了些憂鬱氣息,連日的陰雨不若台南的乾脆,不知天氣是否也會影響一個城市的個性。我擠在人行道,擠在捷運,擠在濕答答的公車裡,然後回家收下衣架上前一晚的溼溽,抱去樓下的投幣烘衣機,我猜,這是許多外地遊子的共同記憶。台北的雨天讓我無勁,將我軟禁在三、四坪大的公寓監獄,想要逃離卻又懶散哪都不想去。這是我的台北雨天記憶。
而待了將近一年的西澳,藍天自私到容不下一朵白雲,別談什麼下雨了。
那麼,農人的雨天呢?
印象中,不管晴天或是雨天,剛從田邊回來的阿公永遠都是剛下過一場雨,頂著斗笠與白色汗衫,這是阿公一貫的造型。艷陽天,他一身溼著回家,白色汗衫下透出黝黑的膚色,內褲溼到外褲,身體散發著汗臭酸味,我攆鼻躲著他並在心中想著他剛才淋過一陣酸雨;陰雨天,古早蓑衣進化成達新牌雨衣,卻依舊溼了整件內衣,有點年紀的達新牌早該退役,外頭下著大雨,裡頭滲著小水滴,不透氣的塑膠也逼出一點汗水,回家的體味依舊微酸,PH 5.7。
而我的雨天則是多了些矛盾的情緒。不用去田裡曬太陽,被蚊子叮,被鳳梨刺,內心實屬開心,就像小學生放假般愉悅,畢竟農人沒有所謂的假期,但雨後的雜草一見到陽光,就像瘋狂粉絲碰到超級偶像,宛如洪水般前仆後繼蜂湧而至,怎樣也擋不住,光想到這,我的腰就不自覺痠了起來。
儘管臉書上充斥著朋友們不用上班的好心情,颱風天我依舊到了田裡,平日的涓涓細流成了滾滾黃河,鳳梨田的水位漸漸從腳踝爬上了小腿肚,肩上的鋤頭早已無能為力,撐著傘望著雨水和鳳梨,我沒有太多的心情,只是一股腦的發愣,或許在這時,擔心已經是太多於的情緒,觀察著田水如何切過土地帶走沙泥,思索著下次該如何提前準備將水引導出去,如果阿公還在的話,不知道他會怎樣解決這困境,或者,在這片土地上,這已是個無解的問題,順應自然,順其自然,回歸自然,自然自然會解決自然的問題。
想著想著,一腳陷進了爛泥,搭配著傘面的雨滴,驚覺,這是我成為農人的真實記憶,如此甜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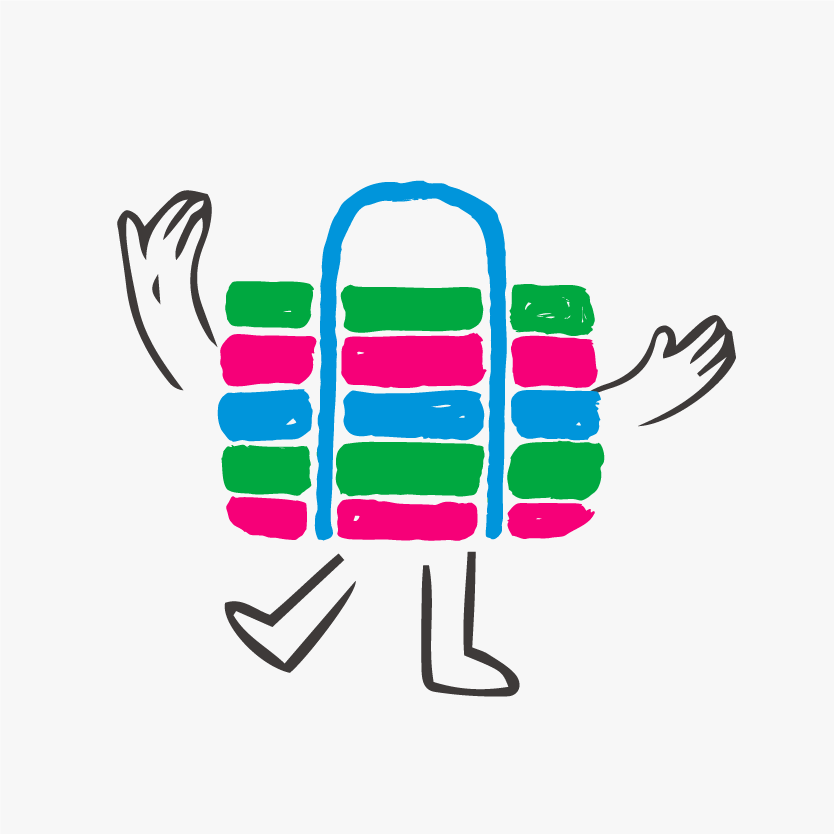
原來,我已經成為你的讀者。
原來,妳年紀比我小。哈哈哈
能做又能寫,讚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