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圖王章逸
「我是誰?我來自何方?我為什麼在這裡?」進入田野地調查前,二林的合作夥伴崇銘這樣問大家。
以歷史為經緯 以田調為度量
八月盛暑,農陣跟 蔗青文化工作室(以下簡稱蔗青)合作,帶領學員在二林溝頭社區進行田野調查。蔗青專長田野調查與文化書寫,經營數年後已有豐碩的在地紀錄及行動。除此之外,他們也跟當地學校、組織合作,規劃在地學程與帶領田調工作坊。深知蔗青在地方的實踐與深耕,敲定夏耘第二階段與蔗青的合作後,農陣辦公室就已經開始期待二林田調的到來。
不負我們的期待,在蔗青的規劃下此次田調並非只是一個禮拜的鄉村體驗,而是紮實的訓練實作。進入社區前,崇銘先帶領學員討論張素玢老師撰寫的《濁水溪三百年》。這本書描述濁水溪三百年的歷史,從河水不定時氾濫、整治後河灘地大興甘蔗種植、到現在集集攔河堰興建改變濁水溪的生態景況。雖然濁水溪逐漸平順,沿岸居民的生活卻沒有因此安穩。甘蔗的種植成為日本人榨取農人的手段,集集攔河堰則限制農地灌溉用水,並且改變沿岸生態甚巨。

除了歷史,崇銘也用一個早上講述「田野調查的基礎概念與方法」。蔗青擁有豐富的田野調查教學經驗,除了長期跟二林地區的國高中合作,夏耘訪調開始前剛結束四天「溪州水文化調查工作坊」的帶領。崇銘將他的經驗濃縮萃取,搭配親身經歷的田調故事,讓課程成為田調初學者能快速入場的大補帖。
他將田調分為三個步驟:文獻分析、田野調查、提案實作。除了分享文獻與田調的技巧與注意事項外,崇銘更重視田調的後續「對我來說,田野調查並非只是單純的認識及調查。重點是在認識一個地方後,可以提出什麼切合在地需求的計畫與行動」。大多數人都知道田野調查是認識地方的重要方法,然而後續的關懷卻時常被遺忘。這樣的提醒對於剛接觸鄉村與田調的學員而言,無疑重要且深具啟發性。

誠如崇銘在田調課的結語說到「從田野出發、向在地學習」,一直以來,貼合地方都是蔗青最重要的精神。協辦這次夏耘的田野調查,也希望將「以地方為師」的理念傳遞給學員。學員在《濁水溪三百年》的歷史洗禮,以及田野調查課程的補充後,終於進入田調的地點溝頭社區。
二林蔗農事件百年之後——蔗農的勞動記憶與溝頭新生
二林是台灣第一個農民運動的發生地。日人整治濁水溪後控制洪患的發生,也讓過去淹沒的大量河灘地得以種作。在日本政府的推動下,這些新生河灘地紛紛種下甘蔗,彰南地區包括二林成為甘蔗重要的產地之一。1924年年初,農民透過地方菁英反應林糖(林本源製糖株式會社)收購甘蔗的不公,1925年更成立「二林蔗農組合」,組織會員與林糖交涉。同年十月,林糖在日本警方的協助下強行收割甘蔗,於是引發蔗農與官方的暴力衝突。

二林蔗農事件之所以特殊,除了他是台灣第一個農民運動,同時也反映了日治時期對農業控制與榨取。百年之後,蔗農事件漸漸不為人知,遍佈的甘蔗田已被越光米取代,蔗農當時的勞動及處境也讓歷史洪流沖散。我們常可以聽到一句俗話:「第一憨,種甘蔗戶會社磅」,到底彼時的蔗農有多辛苦?懷著這個疑問,二林組的訪調以蔗農勞動經驗為主軸,進入溝頭探訪。

百年之後,經歷蔗農事件那代人大多已經仙逝,很幸運地溝頭社區仍有幾位長者健在。幾位八、九十歲的長輩提供學員珍貴的田野資料,從他們充滿甘蔗的童年記憶(收成時總要從五分車上偷抽幾根甘蔗嚐嚐甜頭),聊到受僱於農場,擔任粗重且日薪低廉的會社工(彼時所有的勞動都依靠人力,整地、插甘蔗、採收無所不做。甘蔗的甜來自辛勤的汗),再聊到農場關閉後,甘蔗漸漸消失在二林(現時農場已在平地造林政策下成為無法親近的森林)。長輩的分享如同畫筆,讓過去種植甘蔗的圖像逐漸清晰,也見證了糖業的百年興衰。

駐足溝頭社區的這幾天,也讓我們看見當代鄉村的老化與新生。都市化造成的老齡鄉村是台灣普遍的現象,溝頭社區同樣如此。無人居住的傳統閩式建築破敗,庄內唯一的檳榔攤在數年前關閉,徒留紅磚上的檳榔字樣噴漆。
人口老化不再是教科書上的定義,在溝頭社區是懾人的現實景況。老化是不爭的事實,但我們同時看見社區的動能。恩斌在四年前從台北回到溝頭,拜舅舅為師開始他在農村的事業;停擺多年的社區發展協會也在現任理事長的帶動下重新運作,並且積極成立長照C級據點。「為什麼要做這些事?」恩斌在為我們介紹社區時說到「這不僅是幫助社區的長輩,這也是為了我自己、我的孩子所做的努力,這是我們的家」。
百年之後,蔗田已不復存在,但一代一代溝頭人撐起的家,新的故事仍在繼續。

田野之歌:知道我是誰
在二林的最後一站,我們抵達由返鄉青年開的Loca café,交流田調後的心得觀察。
首先崇銘詢問大家在田野現場覺得困惑難解的狀況「很多時候,我都是一個人進行田野調查,碰到疑惑時只能自己思考與解決。因此這個機會非常珍貴,大家可以將這幾天碰到的問題提出來,大家一起討論」。學員提出各自碰到的問題,諸如受訪者無法精確回答問題、村民請喝酒不知道該如何拒絕,以及如何看待自己進入田野現場「目的性」的前提。

下一輪的分享則聚焦在這幾天的心得。二林的田調不僅是討論蔗農的勞動經驗,學員也從自己的生命經驗反思在田野現場的所見所聞:
有人說:「做為台北人的這件事,好像少了點什麼,總是會被說以台北的觀點看待台灣。經過這次的田調,讓我好像更完整了。」
有人說:「田調後,你真的可以發現歷史仍存在現實生活中,歷史就在那邊。如果我們沒去問這些東西、記錄下來,就只會停留在他們兒女那一輩,孫子是不會知道的。這次二林的觀察後,我回去會想問我阿嬤花壇磚窯場的故事。過去我會覺得這僅僅是我們家的故事,但不是,這是整個花壇的故事。」
有人說:「我們常在新聞上看到社會有很多問題,例如地方派系、工業污染農村等等。會覺得,好像是一個很自然的事情,這些東西是在新聞中被報導出來。但是經過田調、經過實際去看,才會發現說他不是自然而然產生。在我的同溫層中,儘管有注意到,但大概都是鴕鳥心態,經過這次的田調,我認為是要一步一步慢慢解決,要一次可以解決是不可能的。」
有人說:「我是台南學甲農村的小孩,但我對於農村零概念。因為都一直讀書,直到上大學之後,才知道這個地方(農村)為什麼會變成這樣。對我而言參加夏耘是在找一條回家的路。在做訪調的過程中慢慢把小時候的回憶找回來,例如小時候阿公阿嬤曾經種過甘蔗,我也有在裡面玩過,這個記憶已經消失在我腦海裡十多年了。透過接觸農村讓我想起很多事,讓我慢慢找回自己的根在哪裡。」
田野調查是一首唱不完的歌。誠如進入田野前,崇銘問大家的問題:「我是誰?我來自何方?我為什麼在這裡?」當我們進入田野,除了與地方、與居民對話,每個人也都在對話中更認識自己。我們必須思考田調與自身的關係,必須釐清這些對話對自己帶來的質變。

田調是一首唱不完的歌。儘管在二林田調的甘苦之歌已經結束,但對學員而言,田調的結束並非完結,而是不斷更認識自己旅程。
後續,學員將會把田野資料整理成文,再與大家分享成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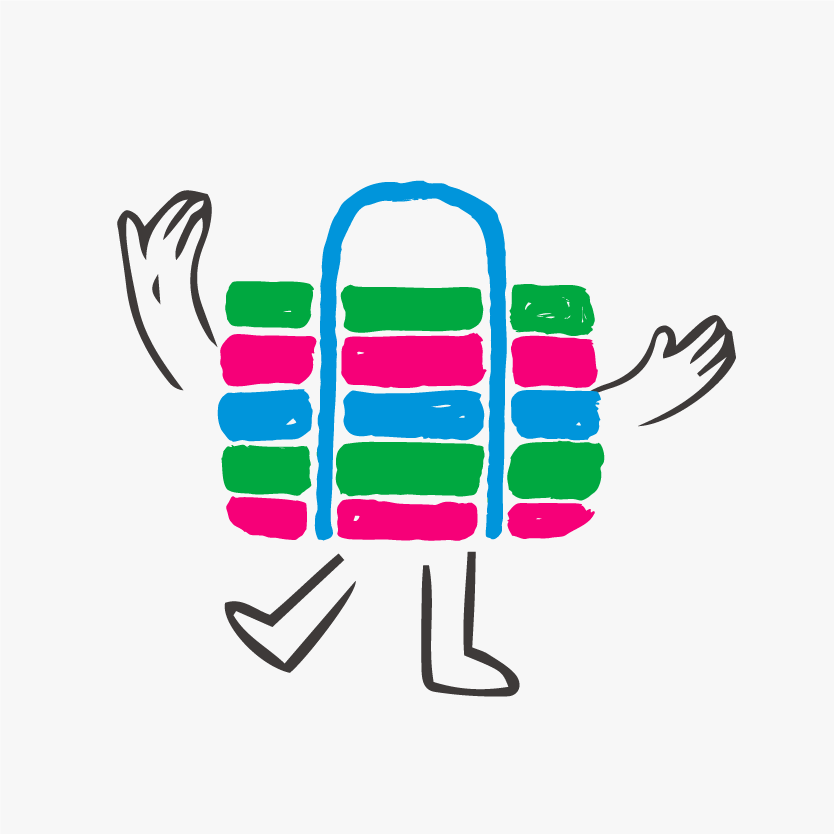
現代農業發展的越來越先進,聽說歐美的農民種地,基本上全部都是機械化,一人可以管理上百公頃的田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