節氣即將入冬,烏魚季就要來臨,三百多年來,野生烏魚群年年南下,有如遵守著和漁民的約定,讓從古至今的台灣漁民熱血沸騰,更構築出台灣海洋文化和沿近海歷史最關鍵的一章。但是最近航港局卻新劃設彰化風場航道,位置就在最重要的烏魚漁場,禁止下網捕魚,消息一出引發全台沿海漁民群情激憤,大規模串聯抗議。
烏魚對台灣漁業為什麼這麼重要?牠在漁民心目中的地位為何如此獨特?透過漁民生動口述捕烏魚時驚心動魄的實況,一起來了解這尾在歷史上和產業面都是重量級的「烏金」。
.jpeg)
烏魚季是台灣沿近海漁業文化的核心
相傳漢人就是因為追逐烏魚,勇敢跨越湍急的黑水溝來到台灣,在沙洲上搭建草寮而與岸上平埔族交易結市,形成最初的聚落。從荷蘭領治時代,中國東南沿海漢人來台灣捕烏,必須向荷蘭官府繳納烏魚稅、領烏魚旗。即使到了養殖烏魚取烏魚子相當普遍的現代,烏魚文化仍然持續影響著台灣西南沿海發展。
如果鮭魚是北美代表性的海洋文化物種,對經濟、文化、精神有重要的啟發,那麼烏魚堪稱是台灣的海洋文化最重要的代表物種。全年度最精采的烏魚季,形塑台灣漁民的討海拚搏文化,不僅有著厚重的歷史脈絡,更是台灣沿近海漁業數百年文化的精髓。
.jpg)
乘風破浪,不眠不休集體作戰
每年十月以後烏魚群南下,冬至前後兩周在台灣西海岸達到最高峰,吸引全台灣漁船齊聚西海岸追捕烏魚。此時的台灣漁民,不僅要對抗東北季風嚴峻的風浪,在大海中航行搜尋烏魚群,也必須有老道的經驗加上熟練的技術,團結作戰才能圍捕成功。
雖然漁民平時各自獨立作業,海上難免暗自較勁,但是烏魚季是短期群體洄游,為了擴大捕撈效率,漁民會進行集體作戰,數十條漁船不眠不休會在海上巡查。
烏魚具有珍貴的烏魚子、烏魚膘、烏魚腱等市場價值,而被稱為「烏金」,是漁民一年到頭等待的最大宗收入。對年輕的漁民來說,烏魚季更是一場考練技術與心性的成年禮。
.jpg)
熱血的烏魚季,是年輕船長的成年禮
「烏魚大家又稱牠叫做信魚,意思是跟漁民約定好的,每年都會如約而來。對漁民而言,也像一場約定好一年一度的勝負對決。」剛滿30歲、擁有碩士學位的青年漁民許秦源,回憶在網路還未發達的時代,接近烏魚季時,雲林沿海漁民會在屋頂上用竹竿將無線電收訊天線撐到最高,最遠可以監聽到苗栗、台中海上無線電話機對話內容,確認烏魚魚汛。
「老人家說,烏魚有靈性會拜燈塔,先去富貴角、再來王功,最後到鵝鑾鼻。」自幼跟隨祖父出海捕魚,長輩口傳烏魚南遷傳說,人性化形象至今仍讓他朗朗上口。而烏魚對漁民的誘惑,他形容,「漁民一年到頭抓魚是養家活口,烏魚季就是去尋寶、挖寶藏。」
「烏魚季出海時如果碰到東北季風,那感覺就像坐雲霄飛車,船身被浪抬起來一瞬間,空氣凝結時間停止,前甲板箱子漁網什麼的都飛起來,心臟也差點停止,等到船落下去,時間才開始恢復運轉。」他回憶小學三年級第一次和爺爺、父親出海捕烏,「暈船連膽汁都吐出來,但是那年烏魚豐收,光分紅就拿了80萬。」烏魚季收入驚人,刺激驚險程度也難以為外人所想像。
.jpeg)
許秦源從小立志存錢造大船,就讀海洋大學期間趁冬季出海捕烏,幸運捕到兩萬多斤烏魚,「滿到幾乎沉船!」他將拉不上來的漁網割斷交給鄰船對分漁獲,最後勉強將漁船開到最近的漁港,那次他豐收數百萬,不過也錯過期末考,至今仍成為海洋大學一樁趣談。
「東部人要能夠鏢到旗魚,才算是漁民。抓烏魚對西部漁民而言,也好像是一個成年禮。」對許秦源這樣剛過而立之年的青年漁船長,捕烏是漁民從生手邁向獨立作業的證明,是漁民養成的進階,能夠克服嚴峻海象、迅速做出明確判斷,才能證明自己的經驗、心智與膽識都處於成熟的階段。
捕烏是重要傳承時機,年輕漁民磨練膽識學經驗
討海資歷第七年的鹿港漁民林仕軒回憶第一次烏魚季出海,「還沒找到魚的時候,只有看到浪,那時當然很害怕。但是看到魚之後,眼裡再也沒看到浪。即使是小艇,只要海象可以,我們都是會出去拚。」
等待稍有經驗之後,駕駛小艇的他,也會跟著大船出海在彰化、雲林海域巡弋搜索,等候烏魚群,「天氣真的很好時,我們會到現在航道的海域下網,大家在海上排成一排,地毯式搜查,看烏魚群大小,決定要從哪裡合圍。」目前他的紀錄最多是抓到兩百多尾。
剛滿 21 歲的林冠羽,是雲林台子港最年輕的漁船長,他想起高中剛畢業,第一次跟著資深前輩出海捕烏的心情,「很恐怖,歹天的時陣,一、兩層樓高的浪打過來,心臟幾乎停止。但是船長操槳必須很穩,船頭必須正面對決大浪,不然會翻船,尤其是在起網的時候,絕對不能閃避,否則漁網如果絞到引擎失去動力更危險,只能加緊速度起網。」
.jpeg)
「浪通常一次都來三個,人站都站不穩,只能不斷的拉網子,站起來又跌倒,手還是不敢放開網子,只能趕快爬起來繼續拉,一直拉到船開出危險海域。」想起剛入行就出海捕烏的經驗,讓他餘悸猶存。
年輕船長從每次捕烏過程中不斷吸取經驗,「烏魚季跟一般時候都不一樣,全船都要保持最高警戒,掌舵的船長要負擔全船安危下判斷,絕對不能怕,觀察海浪水流,告訴前面的海腳仔(船員),該從哪裡下網?要打陀螺(圍圈)還是要用追的,哪裡可以安全起網?哪裡該快?哪裡可以慢?這些都要一邊看一邊學。」
在年輕漁民心目中,烏魚季是一個重要的門檻。漁民在捕烏魚過程,為了挑戰惡劣的海象,將用上畢生所累積的經驗跟判斷力,透過合作捕魚,長輩也將經驗傳承給年輕人。
.jpeg)
大海賜予漁民的年終獎金
正值壯年的雲林箔子寮港漁船長黃正鎮回憶小時候,沿海沙灘在農曆十月初,待祭拜水仙尊王後,就會搭起數座竹寮等候烏魚,稱為「烏倉寮」,作為捕烏、處理存放的基地。越是逼近冬至,所有村內壯丁都在烏倉寮度過,縫補加強漁網或整備船隻,猶如進行集體生活,各家婦女們輪流準備三餐,整個漁村彷彿大戰在即。小孩們被大人緊張、亢奮的心情渲染,也不時往返於村莊跟烏倉寮巡邏,深怕錯過了最新消息。
進入無線電時代,捕烏魚同樣驚心動魄,在東北季風嚴峻的海面上,漁民倚賴團隊作戰來追捕烏魚, 數十條漁船在海上不分晝夜擴大搜索,所有人徹夜未眠滿眼通紅。率先巡到烏魚群的船通過無線電廣播,數十條漁船瞬間將馬力開到最大,有如萬箭齊發直奔目標。
「話機傳來發現烏魚群,當然很緊張很興奮,油門催到緊繃,眼裡只有烏魚,哪裏還看得到浪!」黃正鎮描述捕烏時血脈賁張的爆發力,是台灣沿海漁民共有的集體經驗。
.jpeg)
「靠近烏魚群時,你會感覺好像海面在震動,一大群萬頭鑽動好像看不到盡頭,水面上全部是黑色閃耀著魚鱗,黑金黑金的整大片。」熟練的船長必須馬上判斷魚群走向,海流方向,決定要從南向北下網,還是由北向南框住烏魚群,「整個作業把魚群圍繞起來,打一圈之後,船隻要開進去漁網包圍中心,魚群受到驚嚇衝向周圍網子,才算中網。」
「烏魚群衝擊力大,網子若不夠堅固甚至會被衝破,加上自身重量會沉到海底,根本沒時間多想,當下全部都是憑藉著經驗跟直覺判斷,捕烏幾乎是在跟時間賽跑。」黃正鎮說起這畫面,眼睛發亮。
「烏魚季絕對不會空手而回,伴隨著白鯧、竹午,隨便下網也有幾萬塊。」烏魚彷彿是大海給漁民的年終獎金,對平時運氣不濟的人來說,烏魚季也是年底翻身的最後一搏的手氣。只要技術夠好加上運氣,一天就捕獲數千尾,一、二百萬入袋的事情在漁村並不罕見。
.jpeg)
烏魚是漁民心中的神聖之魚
為了備戰烏魚季,漁民從入冬前會特製「烏魚綾」漁網,預防突遭大量烏魚同時中網時,巨大衝力扯破網子。過去通常是自行加工,現在交給專業工廠,不過為避免大量中網造成漁網沉底,漁民仍然會在長達2、3公里的漁網上,加掛好幾座浮球。
由於烏魚群行蹤不定,且加上東北季風強勁、海面波濤洶湧,漁民的不安與祈佑,只能對神明訴說。信仰在此時更加重要,也衍伸出不少文化與習俗。「出門捕烏魚前都要請示王爺,這段時間不能行房,按日焚香祝禱。」甚至吃飯的時候講話也有禁忌,因忌諱漁網沉底,盛飯時不能說「底飯」、要稱為「添飯」。
.jpeg)
「對漁民來說,烏魚季就是一件很神聖的事情。」漁民不約而同認真說,「雲嘉彰地區沿海漁船,幾乎冬天烏魚季都要出海,討海人一生都在期待著拚這一堵,至少要抓過烏魚才算是討海人。」
如今烏魚季前,政府公告劃設航道,面對漁場被蠶食鯨吞,再度讓漁民感到悲涼。「西部外海漁場先是受到六輕影響,現在又被風機佔去,未來彰化外海再畫航道,我們還能去哪裡捕烏魚?」漁民黃正鎮看著大海,茫茫然的說。
.jpe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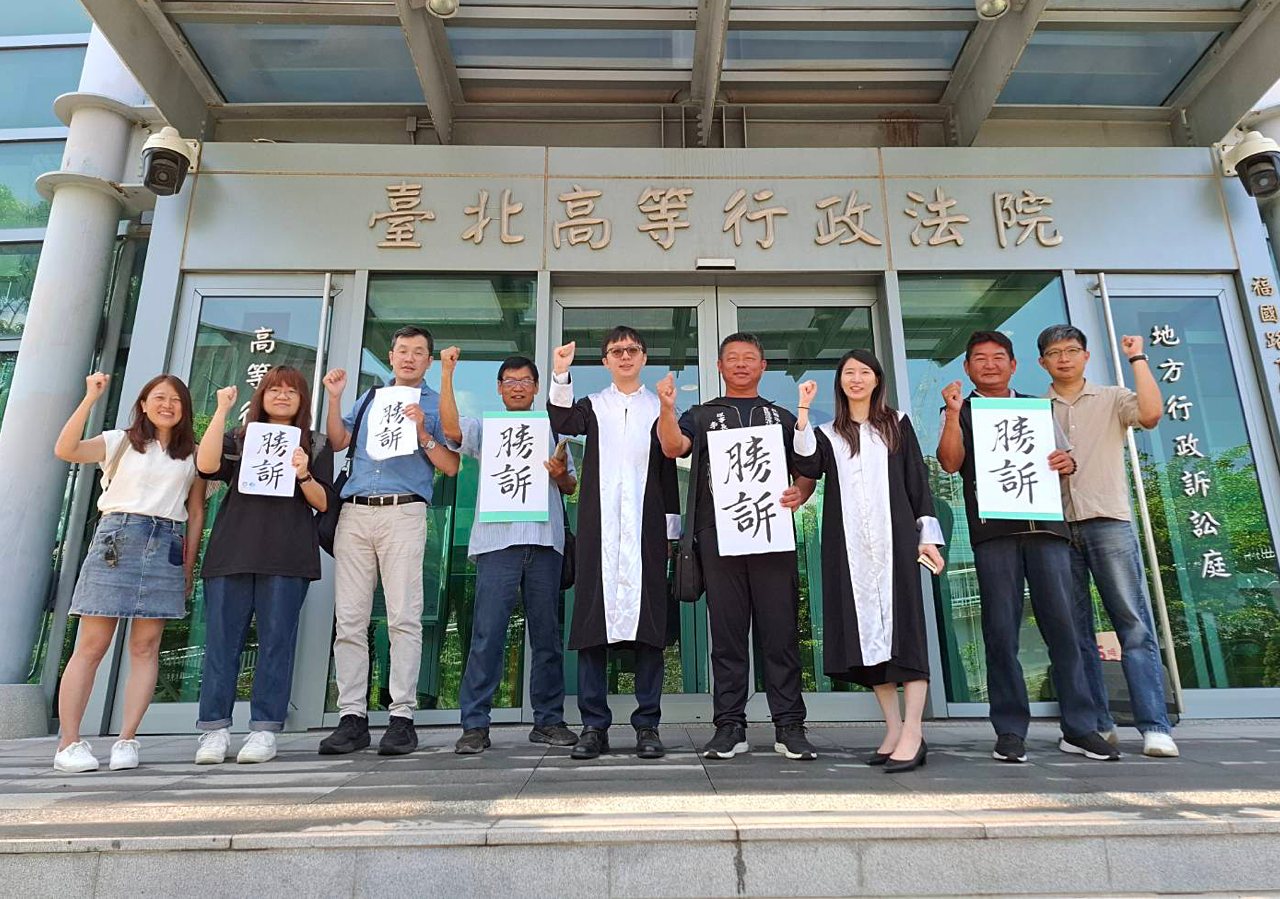



自從突然發現,原來泉漳潮汕沿海,其實至今還有畲族等民族行政單位,比如說畬族村或街道之後,就突然覺得,在那個雲山百越路、市井十州人,還有朝貢貿易的年代,其實,該不會更早就有其他民族是追尋候鳥跟魚群季節移動? 類似遊牧民族,只是跟著海洋生物或候鳥? 因為好像通常被報導的都是陸地的遊牧游耕遊獵? 海洋相關的傳說似乎更多是固定的,而不是也隨季節物候移動?
dmfw mca gov cn/online/map.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