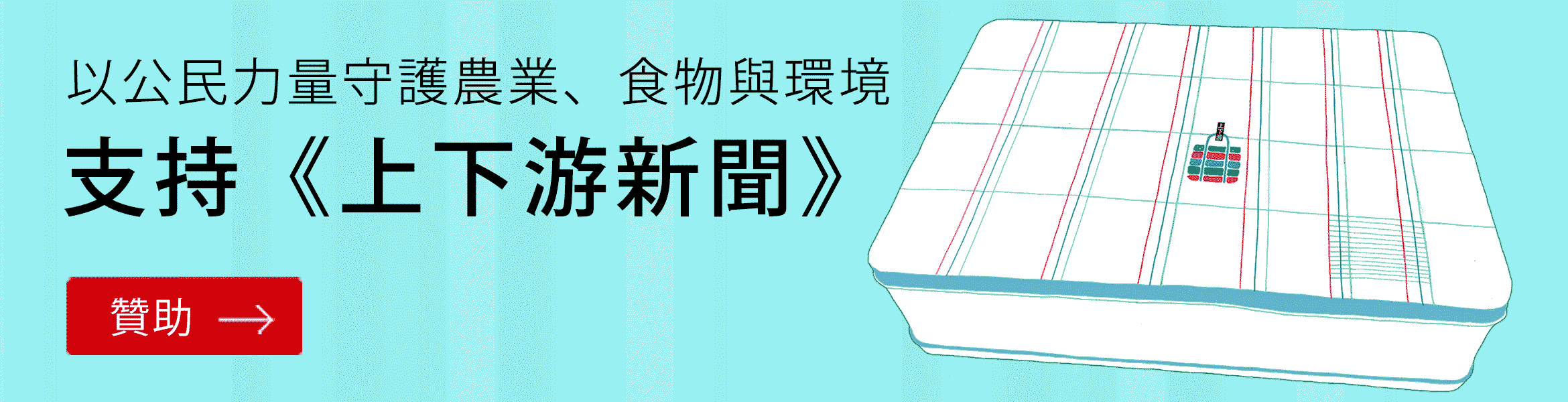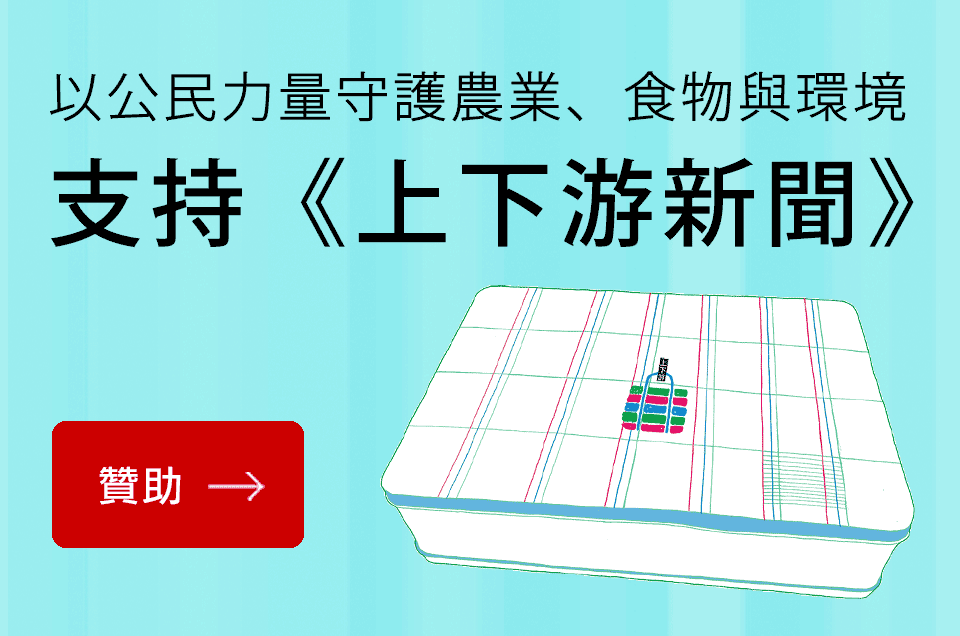到底水稻要怎麼種最棒呢?小工現在覺得這個問題可能要去廟裡擲筊才能解決。某個教授等級的專業農民看到我那有點纖細的水稻,不禁建議我可能要用二氧化氯消毒整塊田土(但好菌壞菌都會一起昇天);但另一位種稻一甲子的老江湖阿伯,卻誇獎我的水稻色澤漂亮,而一般比較「暗淡」的慣行水稻,其實都是因為吃肥過多、密不通風而遭受病菌侵襲,所以事後灌注再多藥物都無法全身而退。再舉個例子,有農民覺得常常下田拔草是好事,可以擠壓泥濘的田土增加空氣含量,有的農民卻認為這樣容易踩傷水稻的根系。
在農業的領域裡常常會聽到這樣的道理:有一好,沒兩好,沒什麼是最好。任何做法都有利有弊,也不見得適合每一個人或每種時空環境。所以…照理說農業和那些千篇一律、自吹自擂的直銷事業應該是誓不兩立的敵人才對啊,怎麼近幾年來倒是珠聯璧合、休戚與共了起來呢?終究還是為了爭名逐利吧。日本自然農法宗師福岡正信在《一根稻草的革命》裡曾提到:「人們認為農業比商業、工業更接近原點、更接近神、在神的周圍。」(36) 但在台灣,農業這一行倒像是常常把神出賣給消費者。
秋天一到小工也種起了馬鈴薯,拿了許多甘蔗葉來覆蓋畦面,北風一吹就整個仙女散花、跌落溝底了,看起來頗凌亂,只好很阿Q的自我安慰:會不會其實連溝底也是需要覆蓋的呢?接著開始栽種工作,一開始拿著約莫30公分長的鞋撐量測種薯的株距,因為種太近怕日照通風不佳,種太遠又覺得浪費空間。投鼠忌器下只能緩慢的前進,直到發覺兩分地對一個人來說太龐大了,當機立斷把鞋撐甩開,單憑感覺拿捏距離。突然就有鬆了一口氣的感覺,就此開啟我的「玩心」。株距遠近、洞口深淺、覆蓋與否,不再只是冷浚嚴苛的數字或標準答案,而是賦予每粒種薯將來個性差異的生命起源。於是在這看似枯燥累人的栽種過程中,我同時在品味著自己的創作與馬鈴薯們的存在──不只我有生命,馬鈴薯們也在生活著啊!
所以當成功國小師生來視察我的水稻田時,只聽見我自然而然的脫口而出:「慣行農田的成就可能只來自最終收成的產量與市場價格,而友善栽培卻比較可以享受整個栽種的過程。」看到孩子們以奇異的眼光看待眼前事物,開心的聞著水稻田旁邊的香草植物,甚至興奮的截下一小段想拿回家種看看。我卻不知道該怎麼向小朋友們說明──你們的純真就是我這塊田最無價的成就。
或許明年的一期稻作,可以來計畫一下開放歪七扭八的手工插秧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