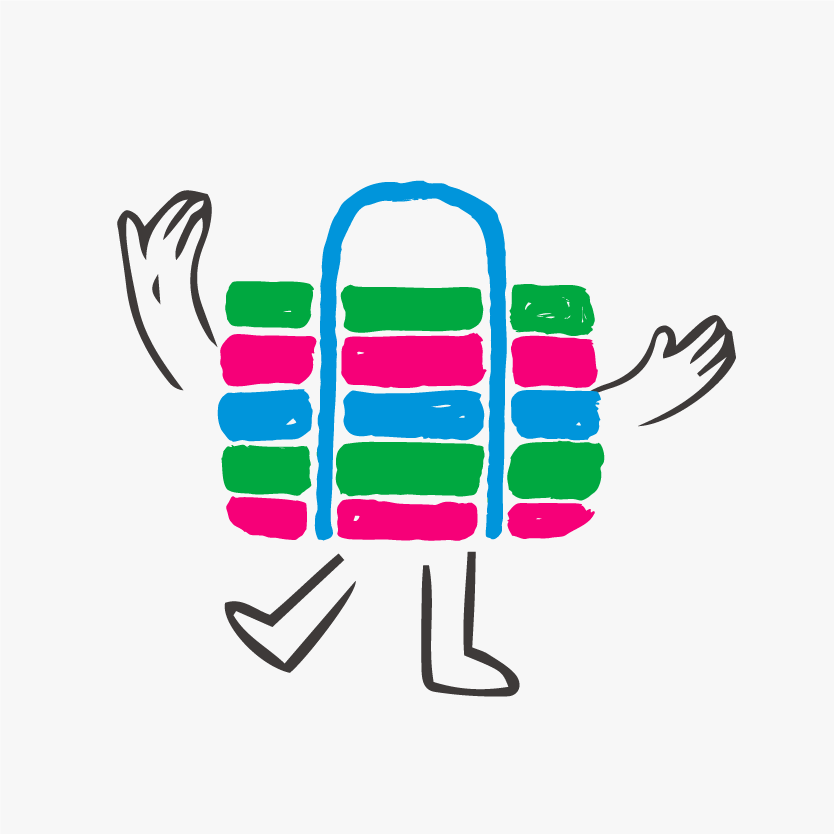一道身影劃開水面,遠遠地還來不及看清楚是什麼,忽然就在眼前,數隻銀亮苗條身材與陽光下異常薄弱卻閃耀的翅膀,「唰」地衝濺起浪花,接著竄入水裡瞬間消失無蹤。
「被驚到就飛起來啦。」船長看著瞠目結舌的我,決定說兩句安撫一下。「有時是鬼頭刀在追,剛剛是船經過嚇到。」我的腦子飛快運轉,試著把那不到五秒前發生在蔚藍海洋上的事件重播。
「鬼頭刀可以做魚丸;飛魚,只能晒乾著吃啦。」船長自言自語起來。
那是我第一次看見振翅的飛魚,也是唯一一次。此後我認識的所有飛魚不是奄奄一息擠在港邊魚攤塑膠籃裡,就是急速冷凍有著凸出魚眼僵硬身體;不過最常見的,還是掛在屋簷邊,或者已經被取下正在炭火上烘烤的飛魚乾。
每年到了這個季節,沿著十一號公路只要有聚落的地方都會有人掛起「烤飛魚」看板。這些廣告小看板一年出現一次,就像洄游性的飛魚,順著黑潮在二月回春時刻緩緩來到台灣週遭。四、五月開始產卵,牠們數量龐大、種類繁多,不只對外島蘭嶼而言是相當重要的傳統食物,在台灣東部與南端同時也是夏季亮點魚獲。


 (懸掛的飛魚。攝影/胡人元)
(懸掛的飛魚。攝影/胡人元)
還記得低頭走過懸掛在屋簷的飛魚乾,望著起皺魚鱗,感覺海風正帶走生命裡最後一絲豐腴。這些小小身體充滿野性,如果沒有經由曝曬風乾處理,一般人甚難享受其中滋味。我喜歡在炎熱夏季踏上十一號公路,並在征戰飢渴片段,隨意坐進路邊飛魚攤招呼的紅色塑膠椅上,等待一隻烤飛魚,灑上鹽巴搭配從冰桶中拿出已經滲入正午溫度的冷啤酒。
對我而言吃飛魚是一種儀式,關於夏天,關於東部,也關於能夠勇敢出行的自己。雖然不似達悟人如此複雜虔誠,卻也不是輕描淡寫垂手可得的日常生活。達悟人在 飛魚季初始,遵守傳統規範只在夜間划大船出海,以火光(如今是燈光)吸引離群分散的飛魚,直到魚季汛期才開始出現各家小舟浮沉在海上,進行豐收的捕撈。然 而這樣數百年來人與自然磨合出的永續系統,卻在短短數十年間因為外來機動漁船的侵擾海域,或是看中飛魚卵龐大商機的業者,用草蓆假造飛魚喜愛產卵的底棲海 草,一網打盡。
如今,蘭嶼島上的飛魚架只有在魚汛時期能稍稍見到往日成串懸掛的擁擠場面,但大多時候,屋簷總寂寞著。
過往,我對魚的味覺記憶來自飽滿柔嫩的肉質、豐沛誘人的鮮味,但遇到飛魚之後,我才了解品嚐樸素簡單的震撼,才了解原來懸掛在藍天或屋簷下的那樣等待不是流失了什麼,而是讓大洋不斷不斷用呼吸吹撫,魚身便褪下死亡腥澀、重新灌入海浪澎湃的記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