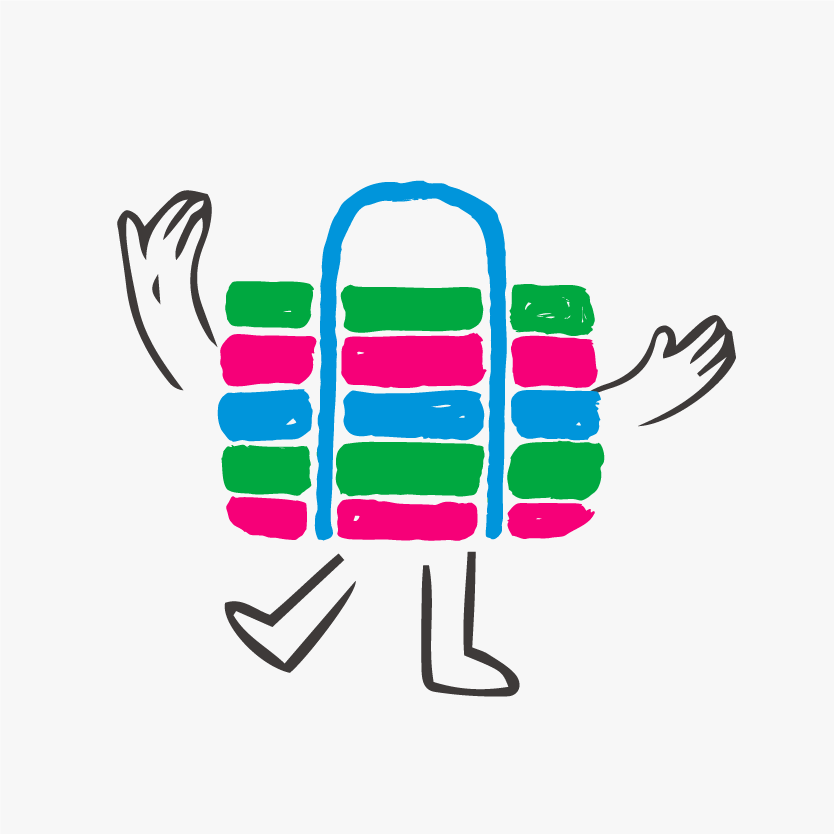編按:作者為清華大學中文系博士,現為成功大學台灣文學系助理教授,本文扼要的整理了台灣戰後以「農業、農村與農民」為主題的書寫模式,從文學擴大至音樂及實際行動,原文刊載於聯合文學,也同時提供上下游讀者一起分享。
──────────────────────────────────────────────
一、人與土地的多重奏:輓歌、戰歌與牧歌
承繼著日治時期知識份子對於三農(農業、農村與農民)議題的人道主義關懷,帶著中國經驗回到故鄉的鍾理和,在1950年代即以《笠山農場》和〈竹頭庄〉、〈山火〉等作品,見證了台灣土地的興衰,並以貼近弱者的視角與辯證性的思索,反省了不同殖民體制,帶給農村怎樣的掠奪與傷害,而棲居於土地之上的人們,又該如何縫補人與自然的裂痕?留給後繼的創作者視野開闊的書寫景觀。
完整成長於台灣從農業到工業發展這個歷史進程的作家們,在戰後鄉土文學的系譜中,陸續地以不同文體展開對三農議題的關懷。擁有血脈相連的土地經驗的作者如黃春明、吳晟、阿盛、洪醒夫等,農村即孕育他們的世界,也是形塑他們世界觀的重要起點,因此,當政經體制與進步主義的發展,席捲了島嶼的每一個角落之時,他們就會在作品裡調動農村的價值與記憶,以往昔的美好對照出發展的無情,以農民的溫暖豐厚反映資本家的冷酷。
更具備控訴傾向的作者,如宋澤萊、林雙不等人,則在作品中揭露那一雙雙剝削農民與農村的黑手究竟所來何處。在1970年代末的鄉土文學論戰高峰之時,對抗性的、行動主義式的書寫策略,成為彼時作家們處理三農問題的主要敘事模式,也因為如此,農村的肌理、農業問題的複雜與農民人性的多樣,皆在這樣文學烽火的遍燃年代中,暫時被遮蔽了。
另一種型態的作者如陳冠學和粟耘,則以梭羅為師,以離群的姿態,牧歌的旋律,將農村與農民歌詠為避世的美好。很長一段時間,梭羅在台灣文藝界的接受視野中,是跟荒野、離群索居等字眼連接在一起的,出版界近二、三十年來,亦出版了多種《湖濱散記》的中文譯本,學院亦不斷以「隱者」的觀點堆疊梭羅的身影,進而,嚮往田園生活美好的作家們也僅吸收、咀嚼到這單一的滋味。


(右)黃春明(右)吳晟兩位先生作品,為台灣經典農村書寫作品。
二、回到南方
在全球化時代的跨國資本主義浪潮中,南北的分立而論,不僅僅是發展與落後之別、也不只是權力不均等的地理疆域之判,「南方」更是一種重要的精神召喚。經過了許多大大小小的爭議與抗議事件之後,我們這個社會終於開始意識到「土地倫理」、「環境正義」、「糧食安全」等這些價值的重要性。
台灣環境議題與農村覺醒的歷史上,美濃反水庫運動是個非常重要的里程碑,在鍾鐵民與返鄉青年鍾永豐、鍾秀梅的凝聚與行動中,這個被許多都會作家想像成最為寧靜美好的農村,從1990年代中期以來,正以不同的形式,翻動了三農議題與書寫的新頁。
「美濃愛鄉協會」、「旗美社區大學」在農村教育與社區意識重構的工作上,提供了許多具有想像力與反省力的實踐途徑。在台灣的農業不得不被捲入WTO的浪潮中,而被國家機器犧牲、成為其他工業與資本部門的交換籌碼之時,如何在生態、生產、生計和生活的眾多面向上,找到一條平衡前進之路,美濃的案例提供了台灣其他農村的重要啟示。
而將這樣的行動與實踐,以美學和藝術的形式書寫下來的文本,已不再是1970、80年代那樣的文體,在音樂、報導和行動藝術的多重媒材上,這樣的三農書寫正試著用協商取代對峙,用積極的生產與創造替代抗爭的能量耗損。最為顯著的成果,當是由林生祥與鍾永豐這對音樂創作組合,以一張一張質量俱佳的概念專輯,唱出了土地之歌,並逐步摸索出了一條在社會介入與藝術創造之間求得平衡的返鄉之路。
鍾永豐曾經在〈我的南部意識〉[1]一文中提到:「所謂臺灣經驗或臺灣奇蹟,它的核心是掠奪性的發展主義,從半個世紀前開始,它掃過西南平原,掃過高雄市,現在它前脚跨進大陸,後脚還在北臺灣,聰明的你可以努力拖住這支脚,或者與被它丟棄或正要丟棄的人們或地方,一起討公道。」正是這樣的政經認識與倫理承擔,讓他筆下的農民是活在一個具體可感的社會條件裡,也使他歌謠體的詩具備一種能量,可以讓我們體會到沈重之後的可能與拔昇。


鍾永豐與林生祥的音樂文學創作。
三、從新故鄉到新農業運動:重新集結的行動者與書寫者
當然,不僅僅是美濃的案例,十餘年來,一波波新的農業運動,正在台灣的許多角落上演。並留下許多可觀的作品,如賴青松的《青松e種田筆記》[2]和阿寶的《女農討山誌》[3]等,這些作者與作品不同於過往的三農書寫,而有底下幾個特色,作者本身並非專業文學作家,原先本有其他專業與工作,因為想在農村與農業中尋找安身立命的價值,故返回或抵達那已被政府逐漸棄守的土地之上,展開小農的生活。
如果我們將視野放大,會發現台灣的新農業運動,是在兩股內外潮流的匯聚之下,沖積而成的新沃原。首先,1990年代中期,由文建會啟動的「社區總體營造」計畫,雖然只是一種由上而下的放煙火活動,但經過幾年的喧騰,卻也埋下當前草根性社區運動的種芽,並逐步引進來外來的範式,如《故鄉魅力俱樂部:日本十七個社區營造故事》[4]、《從329瓶牛奶開始:新社會運動25年》[5]等書所提供的經驗那樣;
其次,跨國資本主義也將西方先進國家的農業帶往一個前所未有的方向,種子公司的專利壟斷、基改作物的強勢橫行,也讓日本和美國的眾多小農開始反省,如何以小搏大,以對土地更為友善的方式耕種,更用新的網絡與產銷方法,在生產與消費端拉起一條信任的軸線,塩見直紀的《半農半X的生活》[6]和Elizabeth Henderson的《種好菜,過好生活:社區協力農業完全指導手冊》[7]正是這樣的新思維。他們兩位也在近幾年受邀來台訪問,與此地小農與各行動組織建立起合作關係。


(左)阿寶的經典書籍「女農討山誌」(右)鼓舞許多青年從農的「青松種田筆記」
當然,此地的行動者不會只是一昧往西方取經,在地經驗的生產與書寫已在不斷的累積之中,吳音寧將馬訶士領導馬雅農民對抗墨西哥政府的精神帶回自己的故鄉,寫出了《江湖在哪裡?台灣農業觀察》[8]這樣具備歷史脈絡的報導文學,並和父親吳晟共同在彰化平原築起了一道動人的土地防線,近幾年的反國光石化和反中科搶水的抗爭行動,皆可以看到他們父女的身影。
吳晟的〈我不和你談論〉不僅是行動宣言,更是一種農民詩人美學觀的捍衛與展現,而吳音寧於上班清晨,隻身盤坐,擋下準備開挖農田的怪手之身影,更是撼動了許多安逸在冷氣房裡的台灣人民。最近幾次的抗議行動中,我們看到了過去甚少走上接頭的藝文工作者的挺身而出,這是非常值得觀察的訊息,或許,當維繫著島嶼命脈的基本元素,水、農田與糧食正被體制與資本家以各式各樣的理由,各種取巧、暴力的方法鯨吞蠶食之際,才是讓寫作者的目光重新凝視土地的開始。

(左)吳音寧(右)吳晟父女一起靜坐抗議中科搶水(攝影/新新聞)
另外一個值得觀察的面向,是新的傳播媒介,讓紀錄農村、反思農業、刻繪農民的書寫主體釋放到更為多元的身份之中。從「小地方」到「上下游」這兩個網路平台中,連結了台灣各地的寫手,他們或者是學生、家庭主婦、耆老、NGO工作者,當然有更多新世代的小農在這樣的平台裡分享他們的勞動經驗與生活。
我們經常可以在這些素人作者的文字中,翻讀出各種泥土的滋味,和各樣平實卻動人的農家大小事。一旦農村有事,資本家的手又準備侵入哪個家園之時,這些平台則扮演了立即的訊息交換中心,當我們的主流媒體對弱勢與環境議題是如此冷漠與怠惰時,更顯得公民新聞與報導平台的重要。
John Berger在《班托的素描簿》[9]裡,有意地在許多段落中迴旋、重複了這樣的句子:「我們畫畫的人,不僅想創作一些看得見的東西讓別人觀察,也希望能附帶一些看不見的東西,陪著它走向無法預料的終點。」將畫畫置換成書寫,同樣是成立的。因為新的農業運動,而正在不同地方紮根、搏鬥的生存故事,以不同於過往的三農書寫姿態,緩緩生成與累積,而這些文本究竟能不能成為下一個世代思索土地問題的重要參照,還有待時間驗證。
我們並不清楚,有多少文本能通過所謂文學性或藝術性的篩選,被未來的讀者讀出當下的農村記憶或傷痕。但有一件事是確定的,這些試圖捕捉鐵鍬擊打在大地之上的書寫,它們不僅留下了當代農民的身影,也不只攝錄了對抗不公義體制的聲音,還附帶了更多「看不見的東西」,陪著島嶼上的子民走向無法預料的終點。

許多素人用文字、影像紀錄生活所在的農村。攝影/阿輝。https://www.newsmarket.com.tw/blog/16304/
[1] 鍾永豐,〈我的南部意識〉,《讀書》(北京:三聯書店),2007年5月號。
[2]賴青松,《青松e種田筆記》(台北:心靈工坊,2007)。
[4]西村幸夫原著,王惠君譯,《故鄉魅力俱樂部:日本十七個社區營造故事》(台北:遠流,1997)。
[5]岩根邦雄著,生活者日語讀書會譯,《從329瓶牛奶開始:新社會運動25年》(台北:主婦聯盟,1997)。
[6]塩見直紀著,蘇楓雅譯,《半農半X的生活》(台北:天下,2006)。
[7] Elizabeth Henderson著,李宜澤等譯,《種好菜,過好生活:社區協力農業完全指導手冊》(台北:商周,2011)。
[8]吳音寧,《江湖在哪裡?台灣農業觀察》(台北:印刻,2007)。
[9] John Berger著,吳莉君譯,《班托的素描簿》(台北:麥田,2012)。
(本文原刊於《聯合文學》2012年8月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