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初,設想的分享內容只想盡情的漫談新竹六家那片美好景緻與純樸自然,暫時放下沉重徵收包袱,及那些我們總是不斷聽見的對抗與控訴。然而,夏耘二階訪調的幾天相處中,多數談話裡卻免不了持續滲出他們的心聲與無奈,我們聽著、看著、思索著……如果可以,我們試著傳達。

新竹高鐵周邊林立著一叢叢的「空心水泥柱」,那是新竹高鐵特定區都市計畫下的產物,幾乎全台灣的高鐵周邊都有類似的模樣,雜草四漫的小綠地與住宅高樓詭異的混雜著。那些空心的水泥柱除了是一般住宅的空間狀態外,著實,也是「中空」的──無人的。
雖然這批徵收案已過去,抵價地也發還了,但另一批,更多批的徵收案至今不曾中斷過。台灣經濟知識旗艦園區(前身為璞玉計畫)如同巨獸般匍匐在新竹竹北一帶十年之久(民國89年至今)。居民瞅著道路一遍遍的拓寬、房屋仲介一間間的進駐、徵收買賣的看板不斷「長出來」擋住眼前那片熟悉的綠、電線桿天天有人沿路綁上虛假喊價的廣告板、鄰居的地被買走而荒廢……久而久之,這樣扭曲的生態漸成為這兒習以為常的新風景。

一波波稻浪隨風起舞,熱烈的陽光打在璞玉(當地似乎已慣習的稱呼東海、隘口、十興、下山等地為他們的「璞玉」)這塊土地上,閃耀著熠熠光輝,如同被聚光燈攝住般令人目不轉睛。
當地嚮導田正祿夫婦帶領我們走訪大街小巷,從認識竹北六家一代的人文歷史到神祇信仰到體驗田間的幽默趣味;從到處都是的土地公,乃至一塊石頭都能夠成為他們內心依歸看出居民對自然的景仰與虔誠,尊重、疼惜是他們長久深耕在這裡的生活態度;從清澈的水圳中徒手摸起粒粒蜆仔,魚、蝦、水草滿佈腳邊,親身體會在現今社會難能可貴的非凡經驗,了解這裡環境資源之珍貴與豐腴。
印象裡,深深記得的是,六家人他們對自我家鄉肯定且不願屈服(惡勢力)的燦爛笑容,「看!我們這裡多好!為什麼要給他們徵收我們的地?!」


這兩三天當中,我們摸過蜆仔、吃過冠軍米、認識稻米產銷與生產線、接觸糧商及如巨獸般的大型機具(脫穀機、烘乾機、冰庫等)、踏進田埂中彎腰除草、在當地茶餘飯後的聚會所(伯公廟)享受茶餘飯後的豪邁暢快、訪談徵收戶,了解他們反對徵收的理由、以及在每日的回顧討論中更加認識一同踏察的夥伴們……族繁不及備載。
一連串緊密的行程,老實說非常不輕鬆,希望在短暫的時光裡獲得最大最多的了解,體驗最深最道地的生活,即使疲累,卻緊緊牽起所有人,居民與我們,我們與彼此,還有六家一片好山好水。

眾多碎片記憶穿插在腦海,有些也許倏忽即逝,但其中一個微小的畫面卻令我不時想起—農人的食指,彎曲的食指。
我們知道綠油油的稻田間,除稻米外,更穿插著不計其數的雜草,不施除草劑的稻農靠著白鷺鷥、鴨子等踩死或吃掉雜草籽,卻無法除盡大量隨風飛來韌性堅強的雜草們。因此,勤勞一點的農民,必須倚賴佝僂的軀體,彎著腰,親手將雜草一株株的連根拔起。我們第二天下午跟著農民田守喜,踏上濕涼的泥土,歪下腰學習識別雜草,如何利用最省力的方式斬草除根,約莫兩~三分的地,我們一行七人拔了兩個鐘頭。雖然我是農村長大的孩子,但長期缺乏農務勞動的狀況下,進行這樣機械式的動作兩小時,還是覺得吃不消。
就在田守喜吆喝我們看著他如何拔起雜草的同時,我的雙眼卻不自覺的被他的食指吸引,這個「刺點」(註1)把我給震懾了……那個好像天生為了拔草而設計的彎手指,其實,是因為長期拔草與農務「適應」下才變形的。
此景令我立刻想起我的阿公阿嬤,他們的手指,也是這樣。辛勤了一輩子、勞動了一輩子,那樣的手指如徽章般的鑲嵌在他們的身體裡、記憶裡。即便我沒有相同的身體記憶,卻也因此更深刻的明白,彎手指背後蘊藏的執著,那是一種一直依賴著土地,離不開土地的最深的牽絆。

農業本是台灣的生命線,年年生產豐饒優質的作物,卻在不當政策下,務農人口持續且大量流失。對農民來說,辛苦整年的回報竟不足以溫飽,叫他們如何是好?除了受到政策的打壓,產業型態轉型的擠壓,人力需求的排擠效應,更關鍵的是年輕人不願繼續耕種──農村,已難以留住年輕新血。蝴蝶效應般各個問題環環相扣,最終導致的是一個失落的農業環境,一個隨著人口老化逐漸凋零的農村生態。
我們這幾天居住在農民鍾光耀提供的貨櫃小屋裡,六個人擠一間兩坪大的空間,好險天氣涼爽,雖然簡單卻也蠻歡樂的。方才題外話,回來是想討論鍾光耀的問題,他們家是六家一帶主要的育苗場,也就是(稻)秧苗供應中心,他們供應了約三百公頃農田所需之種苗,幾乎可說是這裡握有大權的農戶。
和他幾次的懇談中,發現他雖然也站出來對抗不公的體制、政策強壓人民、及政府財團間邪惡的共謀。但像他這種在地方上較有能力的農民,卻也無奈於徵收的壓迫與農地、家業後繼無人接管的窘境。即使勇敢站出來保護家鄉土,卻難以掩蓋想要退休的心理疲勞,「種田,苦。」

除了訪問稻秧的生產與稻米耕種過程,產銷鏈的最後一環,最末端的步驟,也是左右稻農生計的最重大關鍵所在──銷售(通路)。
我們接觸了當地稻農,東海裡稻米產銷班班長,也身兼糧商的陳發生。年邁的陳發生對於政策的不公雖也深感不滿,但他利用產銷班的名義四處申請補助,購買巨大的機具,數層樓高的脫穀機,烘米機,還有冰庫,一整條稻米收割後的產線,包括銷售,都在他與兒子的管理下進行。他聲稱只要是產銷班員的穀都會「加碼」收購(一百斤加十元),然而,現實狀況則是兒子管帳,是否落實這樣的「理想」,不得而知。
他們掌握了末端的稻米產線,多數小農家中沒有這些機具,只能將濕穀全數繳交給他們去脫穀、烘乾、包裝、銷售,他們以八折的重量收購濕穀,折扣後的重量再除以百斤,大約是每一百斤一千一百五十元。一甲農地又能生產多少斤稻穀呢?粗估約一萬斤,算下來,一甲地可以賺的錢可能不及十萬元。一年二期的稻作,最終也不過二十萬的收入,但又有多少稻農能夠擁有一甲可耕地呢?而且,更甚者,他們掌握了最關鍵,也是小農們甚至消費者都難以直接接觸的「銷售通路(管道)」。
造成小農與消費者間躲著一隻看不見的操盤手,沒能力購買機具的小農無奈繳穀,沒對口找在地農民購物的消費者圖便利購買「被定價」穀。明明很便宜的米啊!為何一包五斤買起來消一兩百元呢?


我們看的越多,心裡的疑問也越繁雜,太多問題還牽扯著大人間的利益、認知、道義、無奈、堅持……一時間要釐清如此龐雜的問題不容易,更何況,問題常是沒有(標準)解答的。
此刻的我,試著將問題傳達出來,集合大家一起思考和討論。我們能做些什麼?不是「為了」(註2)幫助他們,而是為了永續的未來,「共同」尋求解決之道,如何付出自己一份心力留住感動我們的那片土壤、那塊田地、那爽朗遼闊的天空?
夏耘從美濃開始,走訪田野,認識環境,在土地中找到更多認同感;夏耘來到璞玉二階訪調,進入田野,置身在地,在土地裡找到它應有卻逐漸落寞的價值。這份價值,我們這世代需要努力把它「彰顯回來」,因為,它一直都在,從未消失。只是,被遺忘了。
一塊真正的璞玉,是歷久彌新的。
註1:「刺點」(Punctum)出自羅蘭巴特(Roland Barthes)「明室˙攝影札記」( La chambre claire)一書,指的是照片不起眼的微小事物,卻吸引我們特別注意,甚至讓人感到芒刺在背的小東西,可使人感動,卻難以用言語形容的事物。
註2:這裡的「為了」有種上對下的憐憫感,但筆者用意在於平等彼此的關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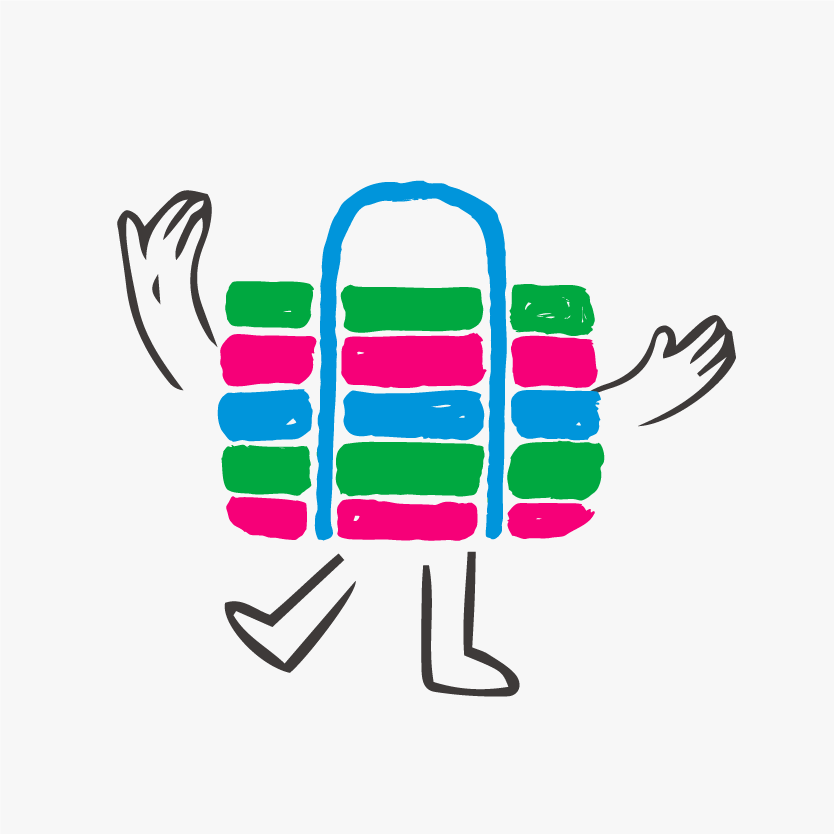
我有親戚就是六家人,過去都是種田為生。因為高鐵站開發後,他們全都成為了富翁,興高采烈的收著徵收後的大筆金錢還有重劃的土地,現在蓋了一棟樓房自用同時還將未開發的空地租給建商做廣告,每個月可以領三十多萬的租金,徹底擺脫了務農的辛苦…其實他們一開始是有反對的,不過反對的只是徵收的方式讓他們可以得到多少利益。這是很諷刺的現實,農地最大的價值似乎已經剩下徵收後大家可以得到多少利益,現在的人早就不想種田了,太辛苦了(就是沒有相等的利益可得)。其實還滿傷心的,因為現代化的發展,讓人類忽略了所追求的進步背後犧牲了多少重要的東西。所以,我們這個世代確實要非常非常努力的去"彰顯"這份價值,這些璞玉才不會隨著這份價值的遺忘而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