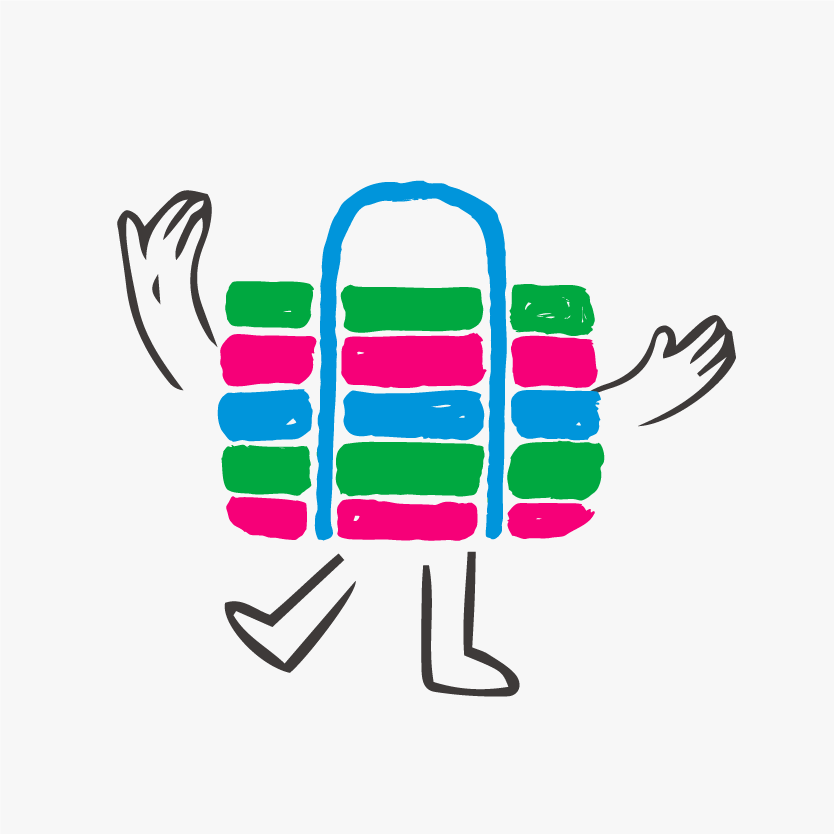作者/張茜
前言:陳婉寧介紹
陳婉寧來自臺灣,2009年加入大陸成立最早的環保組織“自然之友”,現今負責低碳家庭專案。大學時,她曾參與較多NGO的志願工作,只要不排斥的統統參與,包括為勞工爭取權益、婦女兒童保護等,通過這些活動尋找自身感興趣的領域。
大學主修政治系國際關係組,輔系農業推廣學系鄉村社會組,畢業後選擇了建築與城鄉研究所,此領域注重空間與環境的規劃,而陳婉寧的指導老師卻認為,城市規劃師不僅應從專業的角度出發,更應多瞭解社會不同方面的聲音與需求,這樣做出的空間規劃才是符合人情的。
進了研究所後,透過學校的課程與校外的實踐活動,陳婉寧漸漸開始喜歡上更具人情味的規劃模式,對參與式設計很感興趣,在參與臺灣荒野保護協會組織的一些活動之後,她將重心轉移到了自然環境保護領域。開始涉略參與反對蘇花高活動、新竹霄裏溪高科技產業污水排放調查,之後陸續在臺灣環境資訊協會、專業者都市改革組織等機構兼職服務。
陳婉寧還未畢業,便來到北京。她說:“學校注重實踐教育,鼓勵大家沒畢業即可離校做志願者,老師也支持。”在建築與空間規劃領域,陳婉寧表示不會放太多精力,即使以後從事這方面的工作,她也更熱衷於生態與可持續發展的空間設計與規劃。“做志願者的經歷,慢慢影響了我對建築與空間規劃的看法。我的志願不再是剛入學時所想的那樣,當一名特別出色的建築師,設計出一些很炫很漂亮的建築,現在,反而希望有機、自然的環境與城市規劃的結合是生態的、參與式的。”
以下是陳婉寧與有機會記者的訪問實錄:
“我們希望透過大家可以體驗並感知的方式,介紹節能減排和氣候變化的議題,讓他們從對環保的認知過度到真正去行動。”
張茜:你認為北京的城市規劃做得怎麼樣?
陳婉寧:這個城市讓人感覺不是很舒服,空氣不好、人很多、綠地空間不足、城市很擁擠,生活在這裏的人們很有壓力。在這裏,長期居住的生活成本、精神上的感受、人與人之間的互動都與臺灣不一樣。一方面是我發覺北京城市規劃的尺度過大,也就是沒有以人的尺度來規劃城市,城市空間更多是讓位給私家車和商業資本。今天我們說要有一個宜居環境是需要考量公民參與、文化多元性、物質生活的安全和社會氛圍等等。這些不是依靠政府一刀切的城市規劃,而是需要更多地與公民團體、科研團體,立基在開放又科學的基礎上來做。
張茜:請介紹一下臺灣在這方面的情況,兩個地方有什麼差別呢?
陳婉寧:最大的差別是公民社會的發展程度。許多朋友到臺灣學習或旅遊,可能覺得臺灣不是一個先進、富庶的地方,但他們卻感受到了臺灣的人情味,公民參與公共議題的活躍度、在社會底層表達意見的權利、大家主動性地參與社會事務的進程,這些方面與大陸不一樣。當然目前臺灣的公民社會和自由民主也有許多待改進之處,仔細去檢查還有許多制度上的問題尚未完善,如環評制度、都市更新制度等等。
張茜:你主要負責的專案是什麼?
陳婉寧:我現在主要負責的專案是低碳家庭,即協助城市居民減少自己家庭的碳排放。2009年,我還未來到自然之友的時候,這個專案已經有了。2009年至2010年,我加入自然之友,負責社區工作,在社區裏進行低碳環保的宣傳與家庭用水用電量的調研。第二階段,我開始負責自己比較擅長的領域——建築節能改造的工作。我們通過簡單的手法、應用相對節水節電的環保產品使生活中的能耗降低下去,以此改善家庭的碳排放量。
2011年,有23戶家庭完成了建築節能減排改造工程,我們也推出了與此相關的低碳家庭的展覽和書籍。今年,將有31戶居民參與我們的專案。整個專案週期為期一年,居民必須先上課、接受培訓,然後完成房屋改造,最後還要參與書籍的策劃、展覽和對外宣傳的活動。
日後,我們會把低碳家庭的概念推向社區與學校,規劃與設計整個低碳社區,讓更多人參與進來,提高學生們對於學校公共用水用電和能源教育的認知。當人們能夠體驗並感受到節能減排的好處時,他才會開始思考在我們身邊的能源議題是以怎樣的一種方式真實存在。我們認為,氣候變化可能是太遙遠的議題,對大部分的老百姓來講,他們可能不了解什麼是碳排放,如何節能減排,所以,我們希望透過大家可以體驗並感知的方式,介紹節能減排和氣候變化的議題,讓他們從對環保的認知過度到真正去行動。
張茜:這些參加改造專案的居民是如何被選出來的呢?他們的選擇是否具有代表性?
陳婉寧:他們是來自社會各界的普通市民,分佈在北京的各個不同地區,代表的經濟水準與教育程度也是不同的。選出來的居民屋有平房、樓房、新社區、別墅等。成果整理出來後會很有借鑒性。即使你是一個普通民眾,沒有參與我們的活動,也可以找到適合自己的方式、按照書上的指示操作。專案後續依託的是整理出來的資料,只要市民翻閱我們的成果資料,就可以自己在家動手操作。透過有效的傳播讓成果更廣泛地為大眾所知。
張茜:他們自己的屋子作為節能減排的改造對象,改造成功之後,會作為示範單位對外公開,是嗎?
陳婉寧:是的。因為是自己的房子,參與專案的家庭會長期住在裏面,真正體會到節能減排的好處,同時,他們很熱情,十分歡迎媒體記者或社會各界人士前往參觀。他們會通過各種宣傳管道分享改造之後的感受。政府目前在推節能建築,從醫院、大學、政府機關、新蓋大樓開始,像你我所住的房子,比如老社區、舊房子、平房等也需要改造,但卻沒有政府與我們對接。自然之友作為草根組織,更希望通過改善一家一戶的生活方式來達到認知與實踐環保的目的。
“如果你生活的環境過於單一,做事的思維就會局限於幾種模式,這會影響你看世界的方式與在這個世界成長的方式。”
張茜:你認為在北京的小孩子(12歲以下)需要什麼樣的教育?
陳婉寧:我觀察到這邊的孩子壓力挺大的,不是要上補習班,就是要培訓才藝。臺灣有許多環保組織致力於孩子的環境教育與自然教育,像自然之友也一直在做這樣的事情,希望傳導一個理念:小孩子必須要親近自然。現在的小孩很可憐,比如生活在北京城裏的孩子,他們以為世界就是被高樓大廈和地鐵包圍起來的,沒有機會感受和認知自然的美好。
我會覺得很可惜,正是由於他們沒有感受到自然的美好,才會覺得所做所為即使破壞了環境也無所謂。可是,一旦小孩子對自然有了認知,就會開始思考環境的議題,開始關注自己的一言一行、一舉一動是否傷害環境,甚至在長大後選擇職業與做事的方式也會更傾向於對環境的友善。
臺灣有蠻多的環保組織針對中小學開展環境教育工作,帶他們去山裏住上一兩個禮拜,或者是潛水、露營、爬山、漂流,通過各式各樣的活動讓你意識到自然是一個很重要的媒介,它能令你的心靈平復,令你感受到世界的美好。這邊的父母想著孩子如何在學業成績上突出,卻忽略了自然對於培養小孩思維模式與想像力的作用。前一陣子我看過一個報導,德國的學校規定,小學以前不能給孩子太多填充式的教育,比如計算、閱讀之類的,他們認為這一階段的小孩更應該在大自然的環境中成長,身體的感受是不同的。
父母沒有認識到自然對人的重要性,他們會認為分數、考試比孩子接近自然更重要,他們可能也沒有意識到孩子能夠從大自然中學到什麼。但是,國外的許多調查研究已經表明,自然對人類靈性的提升是有幫助的,它對於你平靜心靈、啟迪智慧都有幫助,對你的創意也有幫助。自然就像一個寶庫,你隨時都能看到新的東西,而且這些元素是無法複製的。如果你生活的環境過於單一,做事的思維就會局限於幾種模式,這會影響你看世界的方式與在這個世界成長的方式。
張茜:其實我們也有自然課,但不像臺灣那樣可以隨時去到自然的環境之中,更多的是老師在課上播放影像之類的。
陳婉寧:臺灣的環境教育傾向於帶孩子去野外生活一至兩周,支帳篷、露營,他們必須學會野外求生的基本方法,讓他們懂得思考:地球能源不是源源不絕的。如果今天你在一個沒有商店、沒有水電的地方,那麼,如何獲得生活的能源與支持,也是環境教育的一環。我們環境教育的同事一直致力於這樣的工作,在城市裏的家庭比較難以接觸綠地,我們會選擇城市有限的綠地公園設計相關的活動,希望能夠讓孩子和家長有所感受。
“如果想要一個城市與社會環境變好,民眾需要有將公共場所當做自己的家一樣珍惜與使用的認知。”
張茜:你能談談在北京生活、工作的感受嗎?
陳婉寧:整個社會給我的感覺是對公眾議題參與的熱情不大,或者態度上是與我無關,比如插隊;還有我第一次下飛機,就看到大家在吐痰,或者亂丟垃圾。雖然都是小事,但它體現出公民對除了“家”之外的公共空間是不在乎的。但我同時也感受到,正因為中國目前城市化腳步在加速進展,北京無疑已經是一個巨大的人工城市。而在城市化的進展下中國公民社會需要試著去跟上。我認為對政府、公民團體與市民大眾,都是一個很好的建構與學習的機會。
張茜:大家可能覺得我自己方便就好,我家乾淨就好,外面的空間都與我無關。
陳婉寧:如果想要一個城市與社會環境變好,民眾需要有將公共場所當做自己的家一樣珍惜與使用的認知。我們各個團隊,比如低碳家庭小組,以後會邁向諸如低碳社區、低碳校園更大的公共領域;固廢管理組,雖然在做家庭的廚餘堆肥與垃圾減量,但最終是要解決大環境的城市垃圾議題;環境教育小組也希望將公共領域放大,除了讓更多孩子在城市中享受自然環境之外,也需要政府相關部門的支持。如果我們這樣的草根機構與公共部門的主管——綠地規劃部門、國家公園銜接起來的話,影響會更廣一些。
公民與社會發展有強大的關係,這個關係又影響到環境與我們的感受。比如我們到了歐洲,會羡慕那裏河流乾淨、秩序良好、公共衛生好,可是,我們需要瞭解它們公民社會的行為是如何建構的。北京還處在一個成長的過程中,但這是一個必經的階段。
“有機不單純是一種交易,不是把價格賣得很昂貴,或者變成另一種超級市場,更多的是傳遞一種理念,當消費者與生產者認同這個理念後,大家才會關心身邊發生的與環境、公平貿易相關的事情。”
張茜:你對有機農業的概念如何理解?
陳婉寧:在臺灣的時候,有蠻多NGO組織在從事這方面的推廣工作,最有名的是臺灣的主婦聯盟。一群媽媽和婆婆,她們很關心食品安全,關心家人吃進肚子裏的食物健不健康,因此成為最早一批關注有機蔬菜的人。她們將資源整合在一起,推出有機菜的訂購,大家去指定的地點取菜,在這個過程中宣傳有機蔬菜、農藥殘留、 基因改造食品、種菜的農民與土地的故事。最初瞭解有機是從這方面開始的。
一開始,我只是認為有機菜比其他產品健康、無毒、環保,但後來認識到,有機不是建立在我們吃下去的食物是否健康與安全的機制之上,這樣就太狹隘了。有機應該建立在我們對地球、土地是不是足夠友善,是不是希望它持續不斷地產出美好的食物的基礎上。有機背後的土地和農民是很重要的一環,它不是把土地的價值與有機蔬菜的價格剝離開來,而是整合起來考量,是一個大的環境議題。
張茜:有機提倡“生態、健康、公平、關愛”,其實與自然之友和其他環保組織宣導的理念很相似。
陳婉寧:2009年我來北京的時候,還沒有有機市集,但現在有很多了。因為週末要辦活動,我還沒有機會逛北京的有機市集,但去過的同事回來分享說市集上的東西有些價格很高,甚至部分產品從臺灣運過來,賣得比臺灣貴很多,他認為有機在這邊被誇張和扭曲了。臺灣的有機市集可能所售的蔬菜比一般的貴一些,但更強調生產者與消費者的互動。有機不單純是一種交易,不是把價格賣得很昂貴,或者變成另一種超級市場,更多的是傳遞一種理念,當消費者與生產者認同這個理念後, 大家才會關心身邊發生的與環境、公平貿易相關的事情。
2012年我在以色列與巴勒斯坦,那時候住在集體農場裏面,就是沙漠裏的一個農場。 我們每天的生活屬於自給自足,除了自己無法生產的必須品需要從外面購買之外,農產品之類的都是自己生產。我們每天整理餐廳的廚餘,然後堆肥,再去採收我們三餐需要做的菜,這是一個有機循環農場,因為我看得見這些菜是如何生長出來,並且全部是自己施的肥。
在這個過程中,有機理念就是一個自然的過程。回溯到很早以前,世界各地的生產者都是用自然循環的方式對待我們的土地,只是後來有商業的機制與因素、量產和國際貿易的需要,才導致這樣的模式被扭曲或消滅。我看到北京有很多人在做,比如小毛驢市民農園,臺灣也有很多人在做這樣的事情,整體來說是一個相對好的趨勢。
“如果希望員工長期留下來為這個機構繼續貢獻的話,就需要給員工提供好的福利制度與成長空間。”
張茜:許多NGO的全職工作者的薪資很低,北京的生活壓力又如此之大,他們或許懷抱理想,但現實又不允許他們堅持下去,逼不得已只好放棄NGO的工作,你是如何看待這個問題,又是如何取得平衡的呢?
陳婉寧:非營利組織在世界各國的薪資都是偏低的,在臺灣也一樣。我問過其他國家的朋友,他們也是這樣的狀況。但是,在北京的話,不同規模的NGO組織,薪資水準與結構也不一樣,有國際組織規模、自然之友規模,或是更草根的規模。來NGO工作的朋友除了自身有相對應的專業和熱情之外,自然之友也在盡可能提高薪資保障,至少讓大家在北京不會有太大的生活壓力。
但對於新進的員工來說,比如剛畢業的年輕人,或者到了一定年齡必須要成家或生小孩的朋友,NGO的薪資就很難支撐他繼續從事這份工作,轉而變為兼職或找另一份工作支撐他的理想,但其實這不是正常的狀態。
換言之,NGO工作者的價值在哪里?難道在世界運作中不是扮演一個重要的角色嗎?NGO致力於建構與追求公平正義、修補國家政府與民間社會間的鴻溝、促發公民社會的啟蒙思想與第三部門的活躍。這些都是讓世界與社會更加進化的一環,而有其必然的意義。
理想的狀態是整個機構需要思考與規劃自己對員工和員工質素的需求,並在自己的能力之下幫助員工爭取更體面的薪資。員工在一個機構工作很多年後,對機構的運作、對此領域的專業度以及各方面的人脈都有一定的影響力。如果希望員工長期留下來為這個機構繼續貢獻的話,就需要給員工提供好的福利制度與成長空間。不然大家像一次性筷子一樣,做了幾個月或一兩年離開了,產生的空缺又讓新的一次性筷子補位,提供的薪資沒有改變,陷入惡性循環,這樣,個人不會成長,機構也不會成長,更沒辦法刺激機構做更多的改變。所以,在薪資福利或者長遠的規劃上,不管是員工還是機構本身,都應該時時刻刻進行討論和爭取。
張茜:謝謝你接收我們的採訪。
本文作者:張茜
更多信息請參看自然之友:http://www.fon.org.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