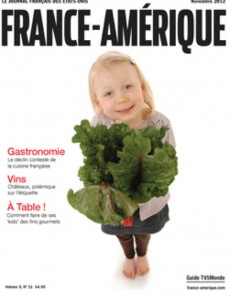編按:本文節錄自《法國爸媽這樣教,孩子健康不挑食》。作者凱倫因為嚮往老公家鄉的生活,興沖沖地拖著老公跟兩個女兒飛抵法國,正當以為全家即將展開夢幻美好的異國生活之際,怎料自己與兩個女兒的飲食習性,竟成了親朋好友、甚至陌生人群起圍勦的標的!一場高潮迭起、機鋒幽默的飲食文化洗禮就此展開……
—————————————————————————————————————–
法國日常生活最緩慢的時刻(也是我最難以應付的)是用餐時間。下廚煮飯的時間倒還好(法國人平均每天花四十八分鐘下廚,美國人則只花三十分鐘,是已開發國家當中最少的),令我難以應付的是花在吃飯上的時間(或者更準確地說,坐在餐桌旁的時間)。
在家鄉時我習慣在辦公桌前吃午餐,五分鐘或十分鐘內便吃完。忙著幫孩子準備上學之餘,如果有時間的話,我會狼吞虎嚥地吃完早餐。晚餐也一樣,孩子一起用餐時我也會急忙大口吞。我們也許花十五分鐘坐在餐桌旁,而且大半時候我經常起身張羅孩子需要的東西,擦拭飛濺物,或設法擺平姊妹之間的爭執。一整天下來(包括我寶貴的睡前宵夜時光),我平均花五十分鐘吃飯。我到底是個典型的北美人。我們每天花在吃飯上的時間不過一小時多。
反觀法國人,他們平均每天花兩個多小時在吃飯上:十五分鐘吃早餐,將近一小時吃中飯,吃晚飯則超過一小時。這還不包括買菜、煮飯和收拾碗筷的時間。用餐時間長度非常固定;法國人幾乎從不狼吞虎嚥,也不邊走邊吃。他們期待孩子也是如此,畢竟吃飯是一種社會性活動;更準確地來說,是一種社交聯誼,每天最重要的交談就在這當中發生(不管是在上班或在家中)。無怪乎法國人吃飯喜歡慢慢來。
如果說我孩子坐不住,那我也同樣坐不住。我們剛搬到法國時,我發現要在餐桌旁坐上一小時之久實在困難得可以。和家族親戚一同吃飯的話,時間又會拖得更久:他們也許十二點半開始吃,直到兩點半或三點才結束,如果有訪客的話,甚至會更晚(夫家紀錄是某年復活節午餐從十二點開始,最後一位客人搖搖晃晃離開時已將近晚上七點)。聖誕晚餐從八點或八點半開始,直到過了午夜才結束。
這每一餐感覺上好似跑馬拉松,我總坐立不安,又頻頻偷看時間。我自願到廚房跑腿的心意從沒人認可;我被期待要跟大夥兒一樣坐著不動。
無論如何,這些漫長的家庭聚餐開始對我一點一滴起作用。部分是因為看到我老公那麼樂在其中,我體會到「慢食」的藝術。外國人很難體會法國人有多麼享受餐桌旁的歡樂時光。即使年少即離開法國,我老公依然懷念(甚至是渴望)和好友慢慢吃一頓美味餐飯的這些真正放鬆的時刻。
他們無止境地說笑,無疑使得吃飯時間拉長變得足以忍受,而且一些最爆笑的笑話每每一說再說,譬如菲利浦的朋友頭一次上我們家吃飯,也是我初次設宴款待法國訪客的事。當時一切進行得很順利,直到上乳酪時,奧利維耶切了一瓣我端上的在地有機康門貝爾乳酪,驕傲地宣揚它的好處。在說著另一個百說不厭的笑話時,他不經心地把乳酪送到嘴邊,卻被他太太及時攔下,她無言地指著在他就要吃下的小瓣乳酪上蠕動的白色蛆蛆。事後我嚇壞了的婆婆問起時,我才知道乳酪要密封包裹才不會招惹蒼蠅(尤其是在夏天),避免大自然遂行其道。不過沒人被觸怒(奧利維耶肯定沒有),而這糗事當下變成日後聚餐時乳酪上桌之際會被一再提起的趣事。「凱倫,這是有機的嗎?」某人要吃下第一塊之前會笑著這麼問。
這些聚餐讓我懂得,「歡樂」是法國人聚在餐桌旁最重要的目標。我見到的法國小孩似乎本能地知道這一點,我找到的法國小孩飲食習慣調查也確認了我的觀察。在至今規模最大的一項調查裡,獲得孩童「認同」的最高分陳述如下:「最重要的是享受食物。」
一如研究者下的結論:「父母親和孩童均強調,愉悅是養分最關鍵的一面。」其中,孩童的態度呼應了他們爸媽的態度,就像世上各地的孩子一樣。根據國際性的調查,北美人對食物的聯想多半與健康有關,關乎愉悅的聯想少之又少。法國人則是另一個極端:他們多半聯想到愉悅,最不會聯想到健康。而對法國人來說,愉悅的飲食代表放慢步調吃食。急急忙忙地吃是不會有什麼樂趣的。這一點也相當重要,足以列為另一項法國飲食規則:
法國飲食準則第8條:
不管是下廚或用餐,一切慢慢來,慢食即樂食。
這規則看似簡單明白,然而意蘊深遠,因為它意謂著,如何吃、為何而吃對法國人來說,和北美人所認為的差別很大。營養不是吃食的主要目標。補充能量(感覺飽足)不是吃食的主要目標。個人健康不是目標,減重也不是。
享受才是吃食的目標。狼吞虎嚥地吃,或擔心體重,或計算卡路里,記錄微量元素的攝取,或是在趕往某處的車上匆匆忙忙地吃,是沒辦法享受吃這件事的。飲食多樣化是該取向快樂的副作用(因為新奇食物也多半有趣,因而使得法國人快活),不是主要目標。目標是從食物中(所有的食物)獲得樂趣。吃得好無須引發罪惡感,吃食也無須是焦慮的活動。
對法國人而言,放慢速度品嘗食物,體悟與他人同食共飲的深刻意義,飲食之樂自然樂無窮。比如說,正午的一餐,是白天之中半神聖的活動。不管他們從事什麼工作(無論壓力多大、多麼忙碌,多麼吃力),法國人會刻意暫停下來,品嘗好吃的食物,與家人、朋友或同事分享這一刻,好似全民集體大大地喘一口氣休息一下,然後再回頭跳進你爭我奪的現實生活裡。
因此我們搬回法國,難怪我老公如魚得水。每到吃飯時間,他便生龍活虎、笑語不斷。和朋友飽餐一頓後,他總活力旺盛。說來有點反諷,那用餐的步調似乎慢得讓我昏昏欲睡。這似乎也很矛盾,畢竟法國人在做其他很多事時快得像急驚風。
我問維吉妮,希望她為我解開謎底。「我們加快生活的腳步,是為了在用餐時放慢下來。」她告訴我。「放慢下來意謂著吃得比較少,但更加樂在其中。」她的說法我不怎麼採信,直到她提出一項科學研究,兩名研究者(一個法國人,一個美國人)量秤巴黎和費城的麥當勞同樣套餐的分量。結果差很大,費城麥當勞的中薯比巴黎麥當勞的要多上百分之七十二。研究者也計算人們的用餐時間,巴黎是二十二分鐘,費城是十四分鐘。
和菲利浦的家人共度無數的餐桌時光,我知道法國人在餐桌上做些什麼事:細嚼慢嚥,鑑賞食物,刻意「喊停」,時時聊天,笑話不斷(在麥當勞用餐的法國消費者很少獨自進食)。他們吃得很專心(這樣做的明顯好處是,在你掃光盤裡的一切之前,你的身體已經發出飽足的訊號)。
這是法式「慢食」取向的弔詭之處:法國人吃得很慢,所以吃得更少。維吉妮對我解釋說,其實用的優點在於幫助孩童(及大人)敏察飢餓感和飽足感。這是基於一種平衡感,換句話說,和適度原則有關:從自制而來的愉悅,基於對品質(而不是量的多寡)的鑑賞。我婆婆吃甜點的方式貼切地說明這一點:「我只要一點點就好,否則就沒辦法充分享受它。」即便是餐桌上的用語也耐人尋味。法國人不說「我飽了」,而是說「我不再餓了」。法國爸媽會鼓勵孩子「吃到你滿意」。他們不會問「你吃飽了嗎?」,而是「你滿意了嗎?」或「你吃夠了嗎?」。
最後,我明白為什麼我們的朋友維吉妮會覺得美國人飲食習慣很孩子氣。她真正要說的是,我們還沒學會大人吃食的方式。大人最重要的飲食能力是,聆聽你身體發出信號的能力,感知你的飢餓感何時消除,而且滿足於合理的分量。「媽咪!我跟妳說」的歌詞說得貼切(我唱了好幾年後才自問它到底是什麼意思):長大並採取合理、理性、負責的生活態度,意謂著放棄孩子氣的品味和行為。
說不定這就是為什麼「速食」就某個程度來說,無法在法國真的蓬勃發展的原因。我剛搬來時,我以為速食在法國是不存在的,因為我們村子裡沒有一家速食餐廳,也沒有外帶餐廳。後來珊卓恩告訴我,炸薯條的小攤子隱身在小艇船塢後頭,而且大一點的城鎮都有速食店,包括麥當勞。千真萬確,最近的大城鎮的公路旁就有家麥當勞,而且每次我們經過總看到停車場停滿了車。
我很好奇法國人吃多少速食,於是請薇若妮卡幫忙找一些統計資料。結果,美國人將近一半的伙食費花在外食上,在法國這類花費只有兩成,而且其中大部分花在孩子(和父母親)在學校(公司)食堂吃的高品質餐飲上。只要不是用恰當的傳統方式料理的食物,都被稱作「la mal bouff e」(壞食物、刻意帶有貶抑的詞)。

法國人對食物的區分涇渭分明:唯有「真正」食物才被稱作nourriture(或aliments〔滋養品〕),其餘的多少都可疑。法國人尤其不希望他們的食物速速揮就即成(他們的假設是,快速煮好的食物想必是草率煮出來的,品質不佳)。一家土生土長、頗受歡迎的法國版速食業,冷凍食品龍頭碧卡第(Picard),掌握到要「快」又要「好」的巧妙。(它在巴黎中央區的門市比地鐵站還多。巴黎人會在碧卡第門市買東西,但他們上那兒買的是蛙腿和碳烤鴕鳥肉。即便「速」食也可能是「慢」煮出來的。
我女兒們無疑從她們爺爺奶奶那裡聽到這個觀點。我們頭一次開車經過公路旁的麥當勞,都上了跨文化的一課。我們拜訪過菲利浦在海灣的另一頭經營一家藝廊的表姊克麗絲汀,正在回程路上。當時天色已晚,我們都又餓又累。
「那個好吃!」蘇菲說:「我要吃麥當勞!」
「那裡的食物很糟糕!」她奶奶說。
「不會花很多時間的!」蘇菲執意要去。
「這就是那裡的食物很糟糕的原因!」她爺爺說,用一種最終定奪的口氣說。
「我們做更好的薯條給妳吃,在家從頭做起。」她奶奶說,而且說到做到。
不用說,我們沒去麥當勞,我公婆想都沒想過要帶孫子去麥當勞。可是村裡的一些年輕人想的不一樣。我們的保母卡蜜拉就常去。
「你為什麼喜歡吃麥當勞?」有天下午我出於好奇問她。「妳有很多很棒的法國餐館可以去。」
「嗯,我爸媽不喜歡我去麥當勞,可是那裡便宜,我也喜歡那裡。」她答道。「那裡沒有規則,有點像美國,對吧?」
把上麥當勞說得像青少年的叛逆行徑令我莞爾。不過它有趣地捕捉到很多法國人說到美國時會聯想到的自由。自一九六○年代末期反社會成規的風潮興起以來,法國年輕人(我老公也是其一)一直很叛逆,吃速食是展現叛逆的方法之一。菲利浦仍記得他念大學時看過的一則電視廣告,當時麥當勞進駐布列塔尼遠端他的學校附近。那廣告有著童音旁白,歷數一長串的餐桌禮儀(「不可以把玩食物」、「不可以把手肘靠在桌子上」),與此同時螢幕上出現人們打破每條規範在麥當勞吃喝的景象。他記得那明亮的色彩、硬質塑膠擺設、陌生而親切的員工和即食的餐食很吸引人。「那感覺起來,」他回憶道:「像是小孩子設計的餐廳,有點像遊樂園,只是擺的是大人尺寸的家具。」
我們有些朋友憂心速食對法國年輕人的吸引力(雨果輕蔑地稱之為「麥當勞化」,維吉妮則說是「懶散的攝食」)。珊卓恩帶給我看的一部紀錄片「我們的孩子將控訴我們」(Nos enfants nous accuseront)總結了法國人的恐懼:農工業(agro-industry)、農業污染、垃圾食物、速食和全球化加總起來,危害了大眾健康、法國文化,甚而法國的風景地貌。看到電影尾聲,我倆都掉下眼淚。
電影裡有個名叫約瑟.博維(Jose Bove)的法國農人,曾因為搗毀南法家鄉米洛鎮的麥當勞遭到逮捕。我們搬到法國時,博維已經是法國民族英雄,而且被選為歐洲議員。不過他反麥當勞的抗爭行動,是法國人對他印象最深刻(最欽佩他)的地方。他聯合其他的抗議人士,持斧頭和工具,一磚一瓦地砸毀了麥當勞大半的建築物,並且在警方來得及阻止之前,把碎塊運到當地鎮公所前的草地上傾倒。法國綠色和平組織負責人布魯諾.拉貝爾(Bruno Rebelle),總結了從全國各地湧入的支持聲浪:「你瞧,在美國,食物是燃料;在這裡,則是個愛的故事。」
不過問題是,食物對我來說不是愛的故事(至少一開始不是)。我逐漸體悟到,真正的問題是,我如何把用來準備和享受好食物所需的時間擺優先(或者說,沒把它擺優先)。我不喜歡花時間下廚,卻樂得每星期花數小時載蘇菲上音樂課並敦促她練習(不管她多麼反抗)。我必須承認,在我內心深處,我把孩子的成功看得比教她們吃得好還重要。我頓悟到這一點,是某天從瑪莉家吃完漫長而美妙的一餐後散步回家的路上。那一餐有在地農場的烤雞、些許初春的野苣淋自製油醋醬,最後是我最愛的翻轉蘋果塔(我依然搞不懂是這玩意兒怎麼做出來的)。女兒們在花園裡玩了好幾個鐘頭後,開開心心地吃光盤裡的東西。瑪莉家充滿遊戲和笑聲,完全沒有我在家裡製造出來的壓力(算數!拼字!音樂課!)。
作者簡介
凱倫.勒比永(Karen Le Billon)
 英屬哥倫比亞大學教授,2010年曾獲選加拿大40位40歲以下傑出人士之一。身為羅德學者,擁有牛津大學博士學位,曾出版3部學術著作。過去10年,她和家人旅居於溫哥華和法國兩地。本書出版後,曾獲選傑米.奧利佛「食物革命」網站2012年8月駐站作家,發起「法國小孩學校午餐計畫」,文章內容引發各界好評迴響。
英屬哥倫比亞大學教授,2010年曾獲選加拿大40位40歲以下傑出人士之一。身為羅德學者,擁有牛津大學博士學位,曾出版3部學術著作。過去10年,她和家人旅居於溫哥華和法國兩地。本書出版後,曾獲選傑米.奧利佛「食物革命」網站2012年8月駐站作家,發起「法國小孩學校午餐計畫」,文章內容引發各界好評迴響。
個人網站:http://karenlebillon.com/
譯者簡介
廖婉如
輔仁大學應用心理學系畢業,紐約大學教育心理學碩士。曾任技術學院講師。現為自由譯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