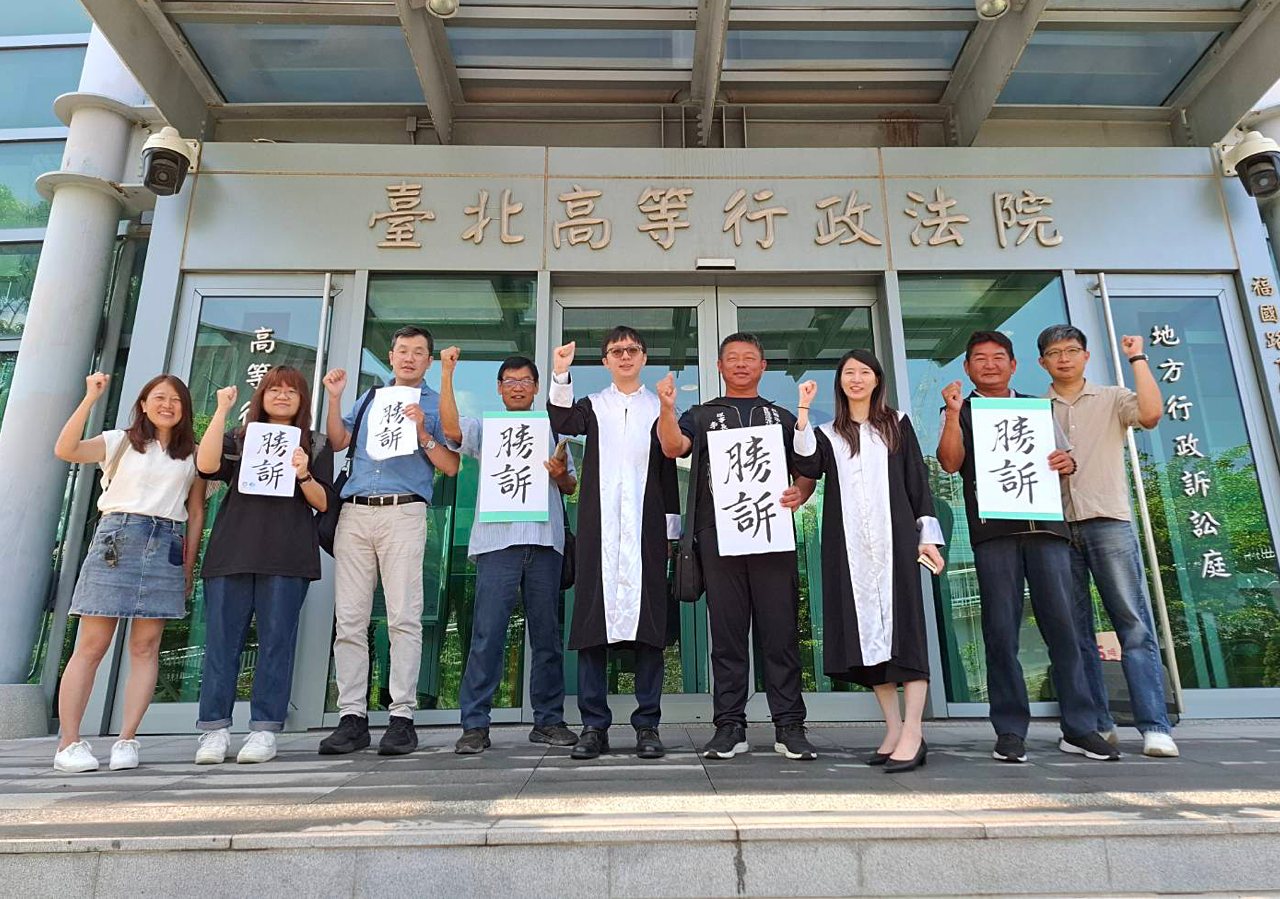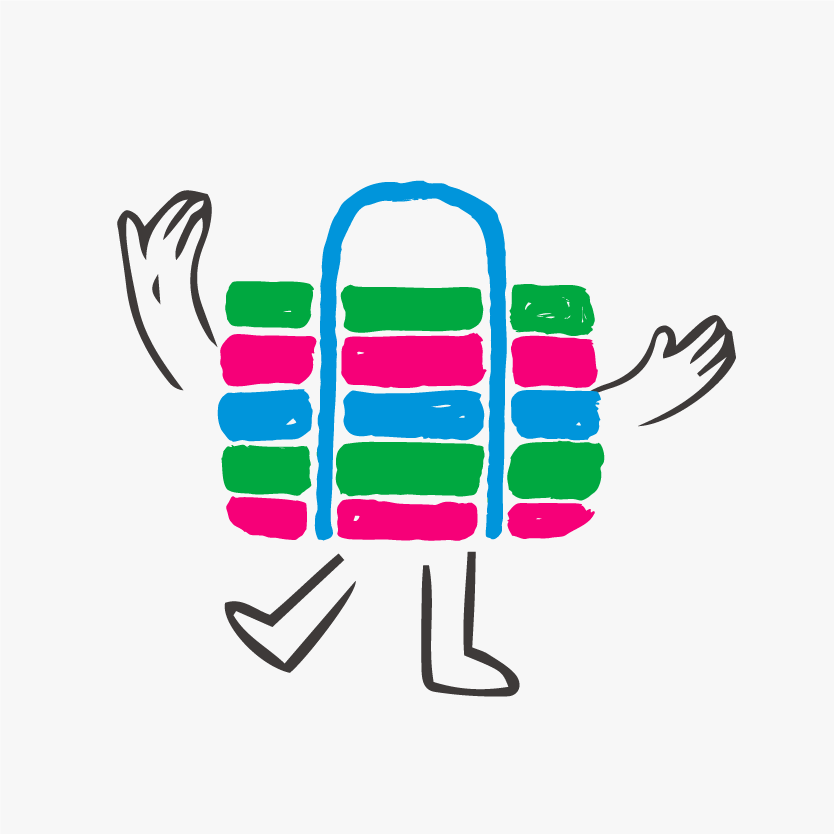根據動物社會研究會統計,台灣一天平均進行2.1次放生、年次數高達750次,昨日立院召開公聽會,針對《野保法》修訂方向提出討論。宗教團體基於放生有消災解厄、護生救生的益處反對修法,認為目前法律早已限制放生行為,而《野保法》修訂將強化國家允許的權限,形同違反《憲法》保障的宗教自由。
動保學者強調並非反對放生,但放生應有更審慎的事前評估,甚至做到事後監測,以清楚掌握放生對生態造成的具體影響;例如福智基金會便長年和林務局、特生中心合作野放黑面琵鷺、海龜和經濟魚苗等,宗教與生態觀點都可兼顧。

放生依地點適用法律不同
其實一個「釋放動物回到大自然環境」的動作,白話又帶有宗教意涵的解釋稱作「放生」,在野生動物學者口中則是「野放」;而這同一個動作,其實又會因釋放的物種和空間有不同適用的法律。
以一個簡單、釋放魚體的放生行為來說,在水庫涉及《水利法》,在國家公園有《國家公園管理法》,在海洋則有《漁業法》,如果魚苗本身是經濟魚種,則又涉及《水產動物增值流放限制級遵行事項》,必須在放生日15天前申請;而以上種種放生行為,若又干擾原始野生動物,恐會觸犯《野生動物保育法》(簡稱《野保法》)中的騷擾野生動物行為。
依現行法規,其實已對放生行為作出一定規範,只是各法規散落在不同的主管機關中。而現行的《野保法》第32條也強調,主管機關同意後,才能進行放生,但在這次的修改條文中,對放生的法律定義又更加仔細:
釋放經飼養之野生動物者,應經主管機關同意,始得為之。但其他法律另有規定者,從其規定。前項野生動物釋放之程序、種類、數量、區域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宗教團體認定申請放生太困難,更無法「隨緣護生」
宗教團體基於放生有消災解厄、護生救生的益處而反對修法,認為目前法律早已限制放生行為,而《野保法》的修訂強化國家允許的權限,形同違反《憲法》保障的宗教自由。
中華護生協會常務理事吳秀慧便說,「全台管制(放生)的法令有很多,到底有幾件是通過申請的?又有幾件是違規的?」她強調政府應該公開數據,才能了解《野動法》的修法是否能達到修法目的,否則「請政府尊重民間宗教信仰自由。」
而許多團體也指出,台中市為國內最早有關於放生自治條例的城市,但就是因得在放生前15天前申請,且程序複雜,所以2012年通過後一個申請通過的案例都沒有。
台中市農業局林務自然保育科長邱淑敏說「零案例」是事實,但據她了解自治條例並非特別困難,也有和宗教團體溝通、協調,只是對方多希望野放特定物種,例如眼鏡蛇,需要更完整的評估而沒有通過。
野保學者強調要合理放生,最好做後續動態監測
野生動物學者和保育團體強調,先前有太多對生態未能有完全評估而進行放生行為,導致生態受害的例子。
像是烏頭翁,本屬於花蓮、台東、恆春半島等地的鳥種,長相、生態習性均和白頭翁類似,但由於中央山脈的阻隔而演化出特殊性。結果在宗教放生的盛行下,從西岸帶來不少白頭翁而和烏頭翁雜交,打亂生態既有的多樣性。
東海大學生命科學系教授林良恭、東華大學野生動物保育所教授裴家騏認為,宗教團體在滿足放生需求的同時,應先行了解對生態的衝擊,並做後續放生後的動態監督。
不過長期對此議題關注的中山大學生命科學系教授顏聖紘強調,並非所有宗教團體均能一以概之。例如福智基金會,便關注到放生行為對生態的影響,因此近年和林務局、特生中心合作施放受傷海龜、黑面琵鷺等。
僧伽醫護基金會也強調,放生造成的環境、生態問題是方法錯誤,不能因噎廢食、禁止放生。因此僧伽基金會也有拜訪以研究生物多樣性聞名的中央研究院士邵廣昭,並建立一套從救護野生動物、選擇放生地點到生態教育、施行放生的作業流程。

動社:應正視商業放生
另外,放生行為恐還有「商業化」的問題。動物社會研究會執行長朱增宏曾表示,台灣一天平均進行2.1次放生、年次數高達750次以上,同時研究會在2009年時也發現,有鳥店為迎合放生者的特殊喜好,而捕捉畫眉、喜鵲、長尾四喜供需求者購買、放生,「商業放生」是已存在的事實。
不過他也強調,新修訂的法條對「經飼養」的定義太過模糊,若下午要放生的野生動物,在早上購得、餵給簡單飼料,算是「經飼養」嗎?
海龍王愛地球協會執行長林愛龍則說,漁業署雖也在公聽會上強調只要放生得當,對海洋資源復育亦有相當成果。但據她所知,目前漁業署已放生1億萬委的魚苗中有做標記、可追蹤的魚苗數非常稀少,成效猶未可知;且放流魚苗應以更細緻的作法,例如在廢棄漁港中以限制活動範圍的方式,讓魚苗適應後再野放以提高放流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