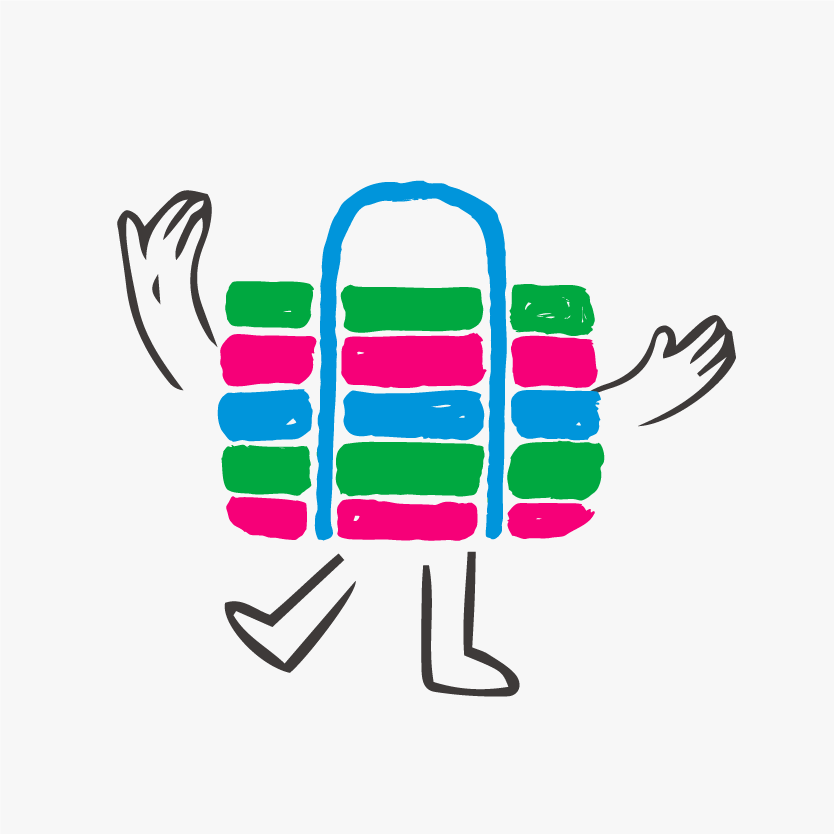2019年行政院宣布為地方創生元年,期望如同日本一樣,透過基層公務員也能翻轉地方,開啟鄉村地區的新契機,並且回應臺灣的鄉村問題、都市問題。但是不少人質疑,在一個以鄉鎮公所作為主要提案者的機制下,是否能夠避免現有已知的民主制度相關弊病?基層公務人員又能否突破地方的派系、政治酬庸的常態,以及臺灣地方鄉鎮公所的政治情境?若是在鄉鎮公所首長支持,地方創生政策又要怎麼貼合地方需求,突破少數菁英的困境?
今年度花蓮縣瑞穗鄉公所的案例,將社區營造與審議民主共同結合,作為他們地方創生的前期準備工作,期望突破公所困境,建立跟社區之間的夥伴關係。他們這一年的案例,值得我們省思。

「投打對決」中的地方創生
瑞穗鄉公所民政課課長鍾亞霖、民政課課員潘美琪,便是這一次案例的主角。他們明白,作為地方創生政策的元年,最首要的事情並不是立馬規劃提案,向中央提出地方創生政策。他們反而開始重新關注鄉鎮內的社區營造協會。潘美琪認為:「地方創生政策若意圖解決地方問題,那麼過去長達25年的社區總體營造,其所積累的社區能量與地方意識,會是地方創生的前哨戰……」。
這一番話其來有自。社區營造在1993年提出的當下,便有意地繞過鄉鎮公所,其積極的意義,是期望社造政策能避免在草創的階段,面臨到鄉鎮公所這個以民意為依託的「龐然大物」,使得各個社區協會淪為鄉鎮公所操作下的傀儡;其消極的意義,則是鄉鎮公所作為一個地方自治機關,坦白地說──即是中央機關拿它沒轍,因此乾脆期望民間的能量能夠彌補公務機關的延宕、程序等的問題,真正的貼合地方產生實踐作為。
經過25年的社造歷程,鄉鎮公所在社區總體營造中,成為了一個曖昧及尷尬的角色,許多時候一眾社區看見便視若無睹、自動繞道。長久下來,社區總體營造的實踐一旦面臨到鄉鎮內的公家機關與政策時,難免產生掣肘,或相關地方實踐工作並未能整體推動等的問題。

在地方創生政策提出之前,文化部在社造政策中,便積極地透過「行政社造化」期望回首解決鄉鎮公所與社區之間的問題。但不論公務機構的社造培力與行政社造化的推展效益,在地方創生元年的當下,國發會悍然地以鄉鎮公所作為提案者,某種程度上強迫公所與社區之間必須互動。
有些論者認為,在地方創生中社區與公所會處於如同「投打對決」般的情境,輪番站上打席與投手丘;於是鄉鎮公所與社區在系列的攻防戰中,看對方投出「長照」球、「閒置空間」球、「在地就業」球⋯⋯,另一方又要如何揮棒(偶爾也有「外援」入場);居民們便且看雙方在這樣的對決中,是否真的能夠拋棄勝負,為彼此獻上一場重喚球迷熱情的比賽。

但是瑞穗鄉公所,他們並未選擇將彼此放在投手丘與打席上,他們尋找社區與公所在地方實踐上的另一種可能。
以審議民主結合社區營造與地方創生
今年四月,花蓮縣文化局的社區營造三期徵選報告中。鍾亞霖課長偕同潘美琪二人在台上報告。他們坦言:雖然文化部近年來倡議審議民主,期望協助公所機關避免陷入民主制度中的「多數決」與「寡頭政治」問題;但在地方創生元年的當下,他們更期望的事情是,藉由審議民主的方式,迫使鄉鎮公所必須得聽到社區的聲音,同時也讓社區拋棄原有的村落為疆界,以「鄉」或擴大至文化生活範圍,重新思考地方問題。
過去少有鄉鎮公所願意以審議民主的方式傾聽地方聲音,因為一旦民眾的聲音透過文字、會議等記錄下來時,他們便有必要解決民眾所提出的問題。多數的公務人員與機關不會給自己「找麻煩」。但是瑞穗鄉公所反其道而行,這令當時列席的委員與花蓮文化局都感到驚訝。
詢問著他們原因,潘美琪的回答值得令人省思:「如果地方創生政策面對的是地方不可迴避的問題,要公務員們坐在辦公室想著要提什麼樣的內容,一面擔憂失敗,一面又畏懼著民意代表或議員的質詢;那麼為何不讓民眾直接告訴我們如何做?……如果真的不幸地,最後的內容未達到我們所設想的。那也沒關係,我們與民眾一起承擔、一起討論,就算再失敗,又能失敗到哪裡?」。

獲得花蓮文化局的鼎力支持,瑞穗鄉公所在今年五月正式「開始」他們的「地方創生」。他們並未向國發會提案,反而是先邀請公所成員與社區協會、居民,一同來學習何為審議民主。他們期望用整整一年的時間,學習審議民主,蒐集聲音,並在其中創造鄉公所與社區間的伙伴關係;直到第二年,有了前期的夥伴關係與意見蒐集後,才正式地針對地方創生所面對的問題進行提案。
地方消滅問題不存在觀眾
計畫之初,課長帶著潘美琪,在一個月內開10數場的說明會,進入到社區協會、社團、樂齡中心、據點、文健站,以及農民組織等團體之中。再藉由2個月的時間開設審議民主課程,內容從審議民主的教學、地方創生的日本經驗、臺灣的地方創生政策、社區營造歷程;甚至邀請不同鄉鎮公所的承辦人一同來分享公務經驗。
最令大家感到「詭異」的課程,是一堂「戲劇課」。他們以社區劇場的操作模式,將社區居民們以角色扮演、肢體,如實境劇場般的方式,將地方議題透過演出的方式呈現,再藉由「觀劇之人」的感受分析問題,提出解決方案。

過程間不僅盤點鄉內的公有建物、高齡者需求、青年創業支援,更重要的是連結鄉內4個社區、1個部落願意加入夥伴組織,共同與鄉鎮公所推展不論是來年的地方創生政策,又或者是跨區域、組織的地方實踐。
潘美琪說,這些課程有一個很重要的結論,面臨地方創生背後的探討的「地方消滅」危機,他們並沒有在課程中談論彼此的身分能夠做什麼事情,應該負起什麼樣的責任,而是純粹的將彼此視為居民,一同思考地方的問題:「只有拋棄我是理事長、我是公務員、我是課長的時候,大家才會發現,我們彼此面對的是同一個問題。」地方創生不能淪入鄉鎮公所與社區之間的「投打對決」──因為地方消滅問題不存在觀眾。
不過4個月的時間,他們二人可謂是抓住社區的心。在一場僅有行政意義上的期末訪視中,來自5個社區的協會理事長、總幹事,以及一般民眾紛紛出席支持他們二人。在其中,移居青年的發言尤為感人:他從外地搬到瑞穗,人生地不熟,但是這一系列的課程與工作坊,有人願意傾聽他的聲音,有人願意解決他的問題⋯⋯。
在地社造經歷二十年的社區總幹事,說的話更令人玩味,他說:「做社造這麼久,第一次與鄉公所們結合,才發現原來還有更多的事情可以做……」。

計畫結束時,鄉公所與社區並未真正的產出一個實質的地方政策建議或內容,僅僅只是創造彼此深厚的夥伴關係。但這樣的關係,便能夠成為他們來年地方創生政策的關鍵;他們不再區分彼此的責任,而是認清彼此所能及與不能及的職責,從中分工、面對問題。
地方創生的基層公務人員時代真的來臨了嗎?
從審議民主結合社區營造與地方創生的案例,突破寡頭菁英,以及多數決的民主弊病,整合內部多元聲音,同時也迫使鄉公所必須回應民眾意見,在地方創生政策中避免一意孤行。這些過程固然值得我們眾人省思與學習,瑞穗鄉公所與在地社區協會的攜手,也讓我們看見過去社造少見的風景。
但同時值得我們思考的,則是接下來發生的事情:潘美琪在這麼成功的計畫中,得到社區協會、居民的共同支持。最終卻也免不了一紙調職令,在今年10月,必須得離開現有的工作崗位。
雖然在交接職位時,接任的新承辦人亦努力的向潘美琪學習,了解後續的規劃,以及跟社區重建關係⋯⋯,或許還能樂觀瑞穗鄉公所來年能夠持續保持這樣的步伐前行,與社區、居民共同攜手創造地方之「生」。這過程底,我們看見公務員真的能夠開創地方的新契機與未來,卻也發現這個充滿著希冀的火苗,在台灣現有的公務員制度之中,仍然岌岌可危。
若不從根本的公務員制度嘗試省思與改變,地方創生喊出的「基層公務人員時代」,少數公務員突破公務制度的侷限,仍然可能僅是曇花一現,抑或步履薄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