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守喜的田,時常破紀錄。他不用農藥、肥料,這四年參加新竹縣竹北市農會稻米競賽,不是第一就是第二。中年轉業,不賣書改種田,十多年來他的田被徵收兩次,祖先留下來的田跟老家都不保,就連現在租的六甲地,也是在璞玉計畫的區段徵收範圍內,隨時可能失業。
不用農藥的日曬米 不交公糧自己賣

最近正值一期稻收割期間,田守喜自己有烘米、碾米設備,但是沒法一次密集烘完,只好賣部分的米給糧商,「我是忍痛賣給糧商,工人來搬米時,看到我的米顆粒飽滿,直說沒看過這麼好的米」。
老家被徵收,田守喜一家四口只好住鐵皮屋,屋前空地這幾天陸續曬了近五千斤的稻榖。一旁已經預留一批穀種,浸在四個橘色大桶,為下一期稻作做準備。
種田十多年,田守喜沒有拿出任何一粒米交過公糧。
他對自家種的米有信心,「我不用農藥、肥料,自己種自己賣,收入比交公糧好多了。」

幫忙農活 哪個農家子弟逃得了

田守喜在父親經營的碾米廠裡頭出生,從小跟著父親去農家收榖子,也坐著馬達三輪車送米到新竹市區賣。他今年五十七歲了,但是左腳腳背還是有一排清晰可見的疤痕,那是他國小時受的傷,在家中碾米廠幫忙,有次不小心被輸送流籠捲了進去,就此留下這個印記。
讀高中時,田守喜每週五晚上固定從竹北搭火車上台北,轉公車到關渡,週日下午才又搭車回竹北。那時適逢台北港開發,不少投資客在附近買地,但政策規定土地不得閒置,田守喜的父親成了代耕業者,北上關渡種五甲的稻田,老家的田則交給田守喜的叔叔照料。
「我爸爸在關渡種稻五年,住在田邊的簡單工寮,不到十坪,睡地板、在大水池邊洗澡。」田守喜說,農家子弟怎麼逃得了家中農活,他的高中生活就是在每週末往返竹北關渡兩地中度過。

北上台北打拚 心繫農家老父
退伍後,田守喜沒有留在老家種田,他選擇到台北打拚,找了個賣書員的工作,「 我書讀的不多,想說可以一邊賣書,一邊讀書學習」。
家中農活繁重,但一旦離開,田守喜反而不習慣。有次適逢收割期間,他人在台北忙工作,抽不出身回家幫忙,年輕單身的他,下班後一個人在台北租屋處,一想到沒法幫父親收割,難過的一直哭。
土地的召喚,越來越強烈。在台北打拚十多年後,田守喜回新竹開書店,又過了三年多,年近四十的他,決定將書店頂讓出去,回竹北老家務農。
開書店那幾年,田守喜每天忙到晚上十二點,每到月底要開出上百張支票,開支票開到手軟,「商場的複雜,現在我回想起來都會怕。還是赤腳踩在土地上,比較舒服自在。」

土地的價值 不只是數字
沒想到,返家務農卻被捲入更複雜的金錢遊戲,竹北高鐵附近的公告地價一路上漲,一平方公尺從兩千五一路上漲到八千八。田守喜的祖傳農地、老家先後被徵收,不賣都不行。就連現在他承租的六甲地,都是在璞玉計畫的區段徵收範圍內,隨時可能面臨第三次徵收。
田守喜被迫發展第二專長,他是種田好手,也是上街頭抗議的常客。他曾被支持璞玉計畫的居民批評為「假農民」,說他沒有農地卻整天上街抗議。但田守喜無奈說,沒有自己的農地是因為被徵收了,「頭前溪的左右岸,是祖先辛勤開墾留下來的良田,為什麼要被徵收?」
「一坪不管八萬、十萬,當別人都敢出手買的時候,表示投資客有利可圖麻,你還要賣嗎?」田守喜沈痛無比,「土地留下來,要吃什麼就自己種,多麼好的事情呀!買一棟鳥籠有什麼屁用,土地的價值不只是數字呀,一想到土地隨時可能又被徵收,我的心就好痛。
(田守喜的聯絡方式:0921-093-84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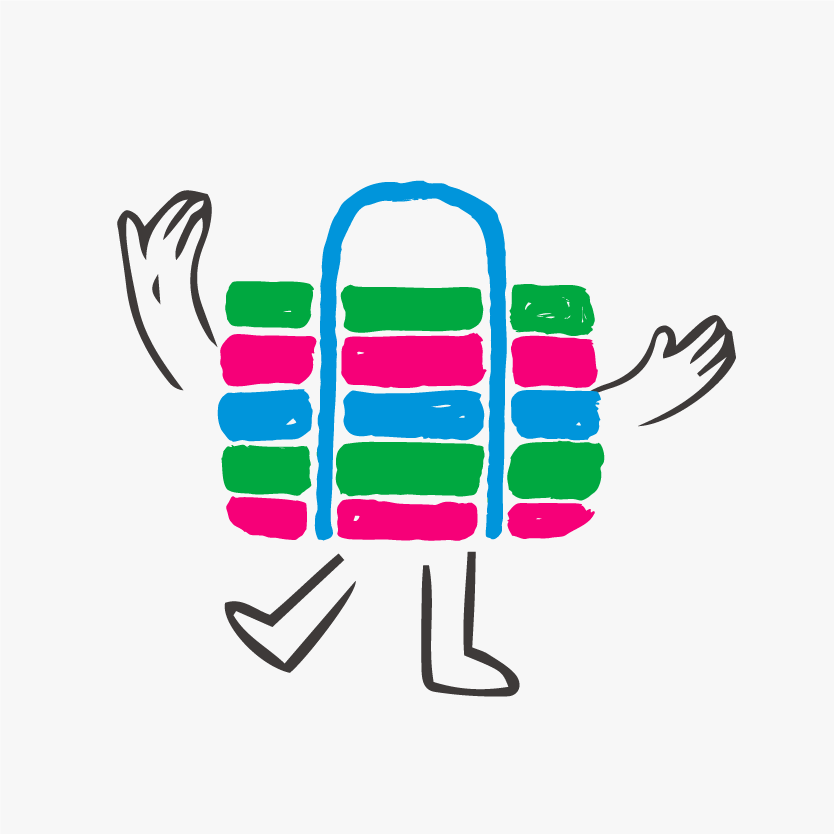
因為很多人一輩子打拼就是要間房子˙土地種米以非一般人民所需˙抗議的方式˙可請政府設農業特區˙其與土地拿來發展也並無不可
因為「官」啊,是財團、投資客、建商、企業家養的傀儡,台灣的房子已經多到爆了,一堆空屋養蚊子,台灣人口都老人化,小孩生不出來,因為台灣的「官」、「企業家」、「科學家」只會發展破壞環境的科技工業,搞得下一代都生不出來了,不然就生出身體有問題的小孩,也活不了多久,蓋那麼多房子是要給鬼住喔!「官」啊,是你能用抗議就會良心發現為你平反的嗎?農業特區,哈!等現在那些在政治舞台上的老人都死光了,看能等到下一代新生的政治家能轉性嗎,等到民國500年可能都等不到喔,小朋友們別夢了,塗了一蠟的爛蘋果,就算表面美好,裡頭已經爛到都生蛆了。
「官」啊,是不會做無關他的贊助商和他自己利益的事的。對自己無利可圖事還拼命做的,早就已經在墳墓裡長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