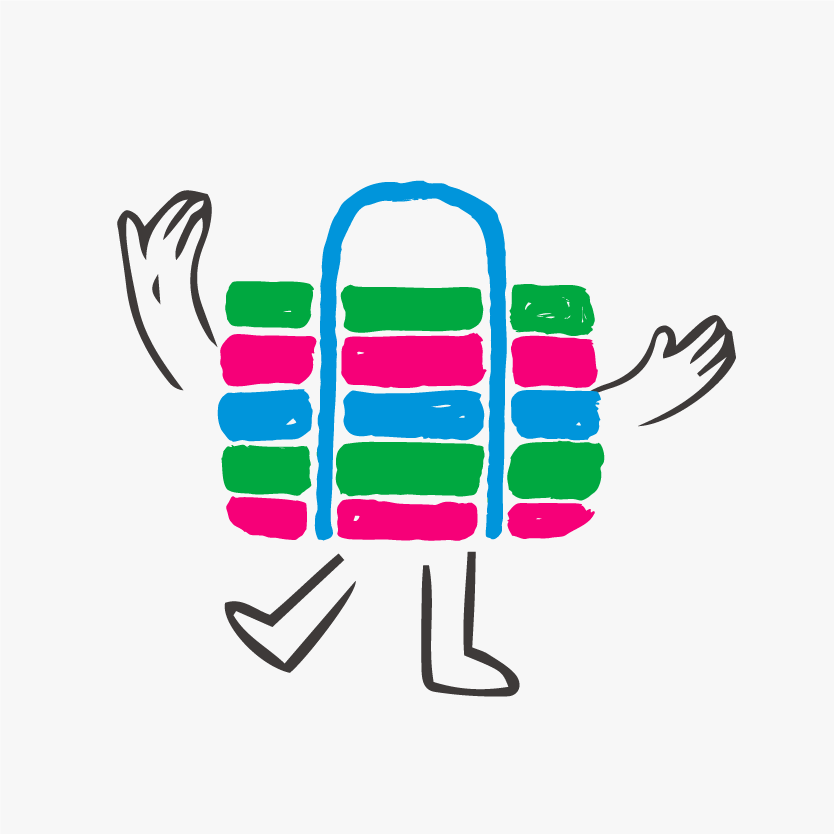文/2018世界新聞攝影大賽得獎者、《白熊計畫》創作者・羅晟文

八年前的秋天,開學後不久的一個午後,一段巧妙的機緣使我走進了新生大樓204教室。那是我第一次到外文系聽課,並不曉得「文學、動物與社會」課程會講些什麼,也很期待能不能讓我那僵化的研究所生活有些調劑。最初兩週,宗慧老師分別介紹了〈峇里島的雞為什麼要過馬路?〉與〈雨中的貓〉兩篇故事;我很驚訝原來文學能被分析得這麼精彩,而且可以和生活中曾接觸到的動物,或動物事件作對應思考——我未曾作過的思考。
第三週,當我還在想著前兩篇故事時,我們讀到了史坦貝克的〈蛇〉。故事中的女主角闖入了一位年輕科學家的生物實驗室,並下達了想買蛇、想看蛇吃老鼠等一連串命令,讓科學家難以招架。蛇女與科學家的對峙猛然喚起了我兩段埋藏許久的回憶。
國中一年級時,自然科學是我熱愛的科目;我想當科學家,也喜歡作實驗。當時學校有「獨立研究」的課程,我們必須自己找一個科學題目來研究一個學期。由於家住高雄,離海不遠,我和一位同組的朋友選了寄居蟹作研究對象。我們打算研究寄居蟹的選殼機制,或是牠們的視覺與嗅覺。那時網路搜尋引擎並不發達,而研究台灣寄居蟹的文獻也不多,我們不知道該怎麼開始。
隨後,我們很幸運地聯絡上一位研究寄居蟹的海洋生物學家;他十分熱心,也歡迎我們參訪他的實驗室。在實驗室裡,他和我們分享了他在潮間帶的研究、探險經歷,以及他整齊、潔淨的大規模實驗裝置,令我們大開眼界,十分興奮。
當我們請教他關於研究選殼機制時該如何讓寄居蟹先暫時離殼,他說「用火焰稍微加熱貝殼尾端」,但要很注意,因為「有時一不小心,寄居蟹會被燒死」;而若要研究視覺、嗅覺的影響,為了控制變因,最簡單的方法分別是「剪眼睛」和「剪觸鬚」。我當時很錯愕,想了很久但終究沒有提出質疑,心想也許這就是專業科學家做研究的正確程序。
回校後,我們跑去問生物老師,她認同了海洋生物學家的說法。雖然我沒有故事中蛇女的霸氣,可以直接挑戰科學家的權威,但這段訪問讓當時我景仰「科學」的心,首次產生了些許動搖。最後我們決定不研究那些東西,改研究牠們的記憶能力,讓寄居蟹練習走迷宮。
第二段回憶同樣發生在我們的寄居蟹研究。有一回寒流來襲時,我在海邊採集了數十隻寄居蟹(註),傍晚回室內時,我擔心夜晚太冷,所以調製了室溫海水給牠們。結果隔天早上,這群寄居蟹死了大半——寄居蟹是變溫動物,夜晚根本不應該用室溫海水;更讓我難過、懊悔的是,我竟然誤用人類的感官知覺來斷定另一個物種的感受,從而害了牠們。當時數個月實驗期間,我把寄居蟹當成我的寵物看待,許多甚至還取了名字;然而因為我的無知,最終實驗結束後,存活、放回海邊的的寄居蟹並不多。
這項在我國中時以科學之名進行的「動物實驗」給了我很多遺憾,但卻沒能記載在最後的科學報告中;隨著課業量增加,我回想起這件事的頻率也逐漸減少。直到讀了〈蛇〉,我才驚覺,如同宗慧老師在〈一種寂寞,兩樣投射?〉文末提及的那隻她不曾伸出援手的「雨中的狗」,寄居蟹事件在我心中,其實一直都沒有結案。
每個人的心底,可能都深藏了一些無法結案的動物事件或疑問;它們也許被封存了好一段時間,且值得被重新面對與思考——並非為了結案,而是持續探索事件背後的人與動物關係中,還存在哪些可能性。但如何催化、喚起這些思考?宗慧老師在文學的脈絡下,以短篇故事巧妙地映照了動物在當代社會中的許多面向。雖然這些故事本身並未試圖訴說任何動保理念,但讀完後,許多情節仍不時在我腦中繚繞,並允許我慢慢推敲出自己的提問與想法。
在「文學、動物與社會」課程結束後,我發現身邊不少修課同學也逐漸釐清了自己的定位;有的甚至投身第一線,親身協助動物。佩服之餘,我也不斷問自己:那我能做什麼呢?我會做什麼呢?我是否能將「獨立研究」轉化為視覺創作,探索動物問題?我相信,每個人都有其脈絡與專長,而《以動物為鏡:12堂人與動物關係的生命思辨課》宛如一面明鏡,讓讀者有機會以多重的角度凝視、發掘屬於自己和動物間的關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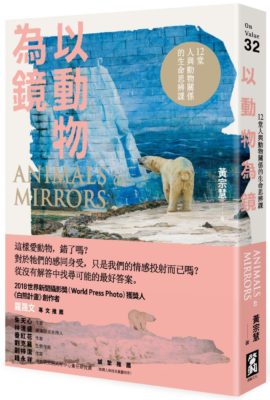
(註)任意在野外採集生物會破壞生態,應與所屬管理機構審慎討論,並申請採集證。
羅晟文/2018年9月15日,寫於荷蘭海牙







-293x293.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