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茉莉
昨晚麗花姐把我們安置在阿寶別致的小屋裡,古早味的木床充滿光陰的故事,好像一早就等著被窗外的朝陽洗鍊,這種懷舊氛圍的新鮮感,令人想不早起也難。
伸伸懶腰雙手推開門扉,迎接環島的第三天,聽說阿寶離開後好一陣子沒人住了,灑進屋裡的的日光裡吐露著莫名雀躍的訊息,龍貓卡通裡面那些躲在案牘躲在藍色的布簾躲在書櫃裡的黑鬼鬼瞬間一掃而空。
野生的銀合歡
春天很多銀合歡都開了花,和來自桃園的一家人(兩個三歲、五歲小男孩和年輕的牙醫爸中醫媽,他們也是華德福的家長,想要到紐西蘭WWOOF,所以先來農援團練習一下,很難得的幸福家庭)一起吃完早餐,兩個小孩就拉我們往外跑,花田厝對面一整片的銀合歡讓台北俗看得出神,這麼美的樹竟然是野生的。
我們倆一開始不知道它是什麼名字,看那嬌小的小葉對生的羽狀複葉上頭掛滿白色、咖啡色飽滿的球球,就暱稱它為聖誕樹。銀合歡又名白相思子,豆科可以固氮,銀合歡屬。因頭狀花序上開著白色球狀小花,所以種加詞譯義為白頭的,以前種來造林當綠肥,可惜太強勢目前算是需防治的外來種。
吃過早餐前往援農團第二位農夫工作的所在,我們今天的褓母,大三就聽過他動人的演講,我們倆都很崇拜這位謙卑的名人:賴青松,他沒有手機。青松一家人回到太太的娘家宜蘭,在蘭陽溪北岸的員山鄉深耕,以「預約訂購,計畫生產,平分風險」的方式來行銷稻米,是將農夫與消費者緊密地結合的先驅。
赤腳踏進黑糯米水田,軟細的泥漿在腳底下,像踩到奶酪。好似我遇到的農夫們永遠努力向前,除草的動作也是得直直地向前進,只是好一陣子我都還是禾稗不分,因為演化的關係稗草都變成沒兩樣了。
青松大哥徐徐道出秧苗和稗草的差別,兩者顏色上、葉的軟硬度、根的長度都有些微的差別,稗草沒有耳毛、葉緣帶有紅色。
春節過後插的秧已經長到第四小葉了,青松一邊插秧一邊笑瞇瞇地和我們聊了好多好多,他說他好喜歡種黑糯米,因為在結稻穗的時候風吹過都有濃烈的撲鼻稻香。
後來有個年輕人也來幫忙,林宏泰,在室內設計工作好幾年的他,老家也在傳藝中心附近務農,家人不支持歸農但仍執意走上半農半設計的路,林說:「家人總有一天會懂的」,令我們倆心有戚戚焉。聊到環島,林建議我們去南澳的「自然田」看看他們的自然農法。
中午到青松的家屋,可能是留學日本的緣故吧,他們家有日本鄉下房子的風味。
自力拆屋,花了一個月去拆舊工廠樑柱所打造的屋子裡,滿是書籍,象徵農人應該要晴耕雨讀。我們還在牆上的地圖簽名。青松太太美虹姐自製的豆腐乳飯糰,噢我最愛的豆腐乳,她說飯糰打包當田間點心是農忙時的懶人便當,我們還在靦腆,青松笑說什麼都可以輸,但吃飯一定要搶第一,所以我們就不客氣地大快朵頤了,這真是自古做田人的搞笑哲學。
飯後,早上就來拍攝採訪的蘋果電視繼續和青松聊到快下午三點,我們早就疲累得在塌塌米上睡著了。
下午轉換到秈稻田去工作,和早上的黑糯米田距離不到百米,但很奇怪,每畝田都有它的個性。這裏的土質不同,我們還發現紅冠水雞的腳印,以前在生態池常看到,頭一推一縮地很可愛,青松大哥聽到此稍微嘟噥了幾句,過一會特意叫我們過去田的另一端看被紅冠水雞肆虐過後的慘狀,有一區塊兩排的秧苗都東倒西歪,「這樣妳們還說它可愛!」青松大哥的憤怒,我們都笑了。
秈稻是台灣野生稻演變成的栽培稻,和黑糯米一樣都比蓬萊米(梗稻)來得強健,耐熱少病蟲害,因此所以友善耕作常常會選擇秈稻。蓬萊米是需要較多農藥的梗稻,由於日治時期日人愛吃口感較軟黏的米飯,經過政府大量推廣,現在我們吃到的很多都是梗米。
赤腳踩在健康的水田裡是一件很舒服的事,彷彿能感應大地的脈動。
宜蘭稻米原可一年兩作,但因應加入WTO政府推行二期稻作休耕,如果執意要種的話,全宜蘭的鳥都會來吃你的稻米,所以沒人敢種。
傍晚一行人去參觀古老的大碾米機,碾米爺爺把米倒到地底下,米卻會在滿屋子的軌道裡溜滑梯,青松大哥和我們說,你看老爺爺他拉這麼多的環讓機器開始碾米,有沒有像神隱少女的鍋爐爺爺的樣子呢。
傳統手動的碾米機,碾一斤米2元。
碾米爺爺說他從年輕時就繼承這間工廠,開始操作這個機器,米經過一次次循環,漸漸開始變得白皙,碾米爺爺戴上老花眼鏡來確認米的顏色,承承和淼淼天真無邪地跟著在米道上,用手收集掉落的米粒。米滑過碾米爺爺一雙佈滿皺紋的手,兩個小鬼小小厚厚的手掌,又承接得了多少農村沒落的哀愁。
老爺爺問承承,玩得那麼開心要不要留在工廠呢陪爺爺呢,承承靦腆笑著搖頭。米裝進袋子裡,老爺爺用封袋機時還作勢要把承承的外套封起來,大夥又笑得合不攏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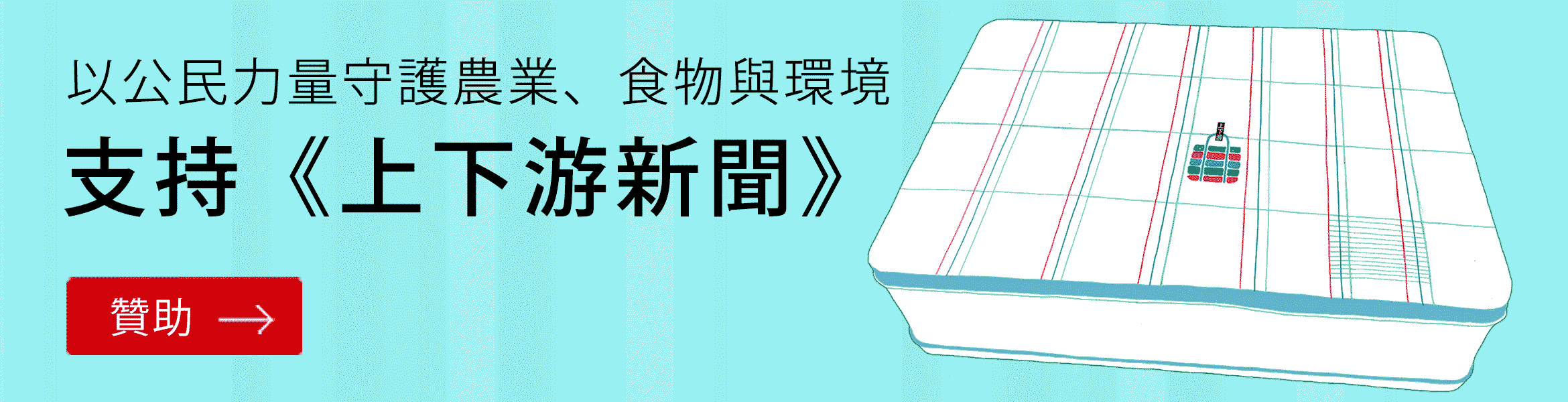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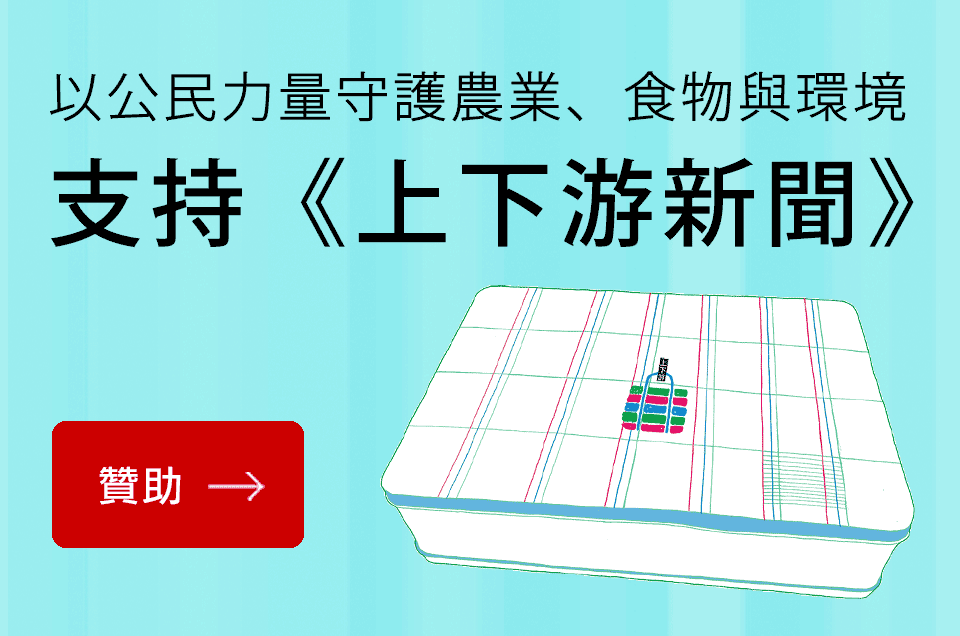











東方室內設計是一件事,很自然舊屋翻新的人生活在世界的東方,但是當你生活在西方世界
http://www.yestudio.com.t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