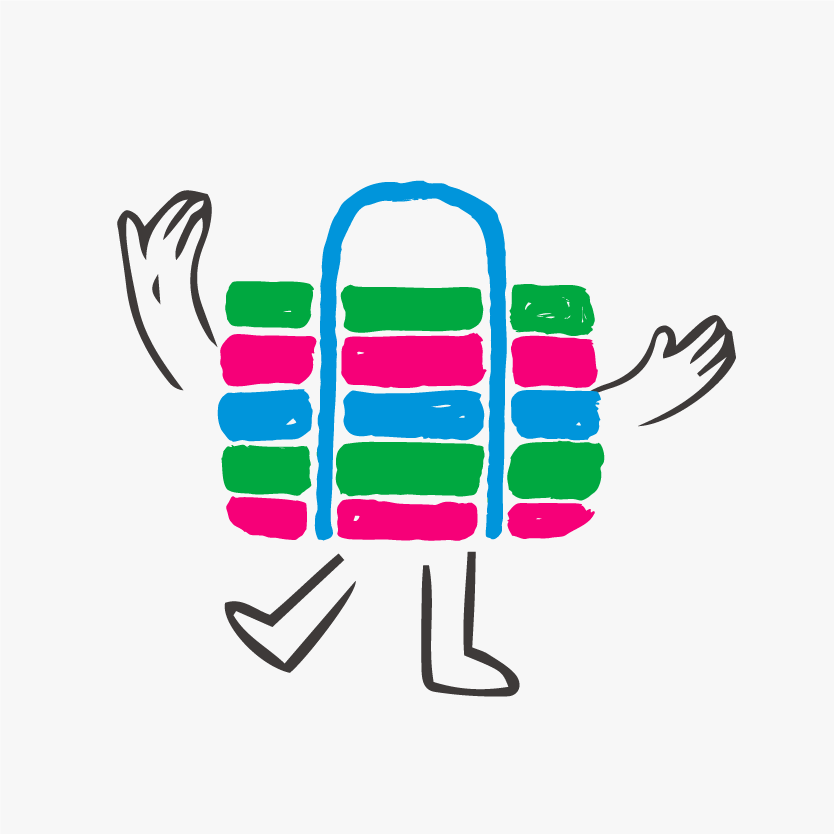(續前文)因為跟隨者眾,賴青松必須面對新農們的生存和夢想永續的問題,他成立慢島生活公司,在商業邏輯中找尋解答。在時代巨輪前,他拒當滿腔壯志但無力回天的唐吉軻德,而是蹲下身來守護土地,設法讓理想與現實扣合。
對於「是否堅持農地農用」、「是否棄農從商」以及對《農發條例》的功過評價等提問,賴青松直抒胸臆,坦承以對,「一個可以回去耕耘的所在,一條能夠親土返鄉的道路,是我生命終極關注的命題」,廿年的奇幻之旅,說到底就是這樣一句心裡話。
台灣社會在改變,農業從過去工業化形式慢慢鬆綁,給了「服務業化」的農業生存的空間,這是一種典範轉移,而賴青松、楊文全以及「反向移民」的宜蘭小農們,也用思維與行動造就另一種典範轉移,這些新的典範能否為新農村時代拉開序幕,值得社會繼續觀察。
.jpg)
Q6:是否想過從體制內進行農業改革?怎麼看待楊文全擔任農業處長的經驗?
A:2015 年,當時的林聰賢縣長到家裡來拜訪,詢問我是不是願意擔任農業處長?雖然我也關心政治議題,但不覺得自己有很高的政治敏感度,我也不太受規範約束,所以最初才會走上穀東俱樂部這條路。
相對來看,文全才是「天選之人」。他有十年博士班的訓練,也曾與公家單位合作許多大型規劃案,是一個具有鄉村空間規劃背景的專業人才,有機會能夠坐上決策者的位置,非常難能可貴,因為台灣常被詬病是非專業領導專業。
後來在任上大概一年的時間,文全對台灣農地問題的解套做出具體貢獻。當時法律上已經同意農地興建農舍,但他要求十分之九維持農地農用或者是儘可能維持它的完整性,而且現場的施工裁量必須合法。光是「必須蓋到馬路旁邊」的要求就讓很多人對購買農地、興建農舍有所猶疑,因為他們想像的是美式別墅(按:房舍在中央,前有院、後有庭)。
.jpg)
Q7:您的身分從單純的農夫往農企業偏移,成立公司後又與政府合作,從商後看似向現實妥協,這跟您早年的理想有沒有矛盾?
A:我必須承認這一關不好過。我當初是放棄了都市主流的操作方式,選擇回到宜蘭的土地跟農村。廿年歲月後,我發現時代的風往這裡吹。當時我是少數的先行者或說是異議者,但似乎走著走著人愈來愈多,而時代也開始關心農業及食物,甚至連全球主要企業和聯合國都提出類似的倡議。
即便我們慢慢從非主流變成潮流,存活的問題並沒有因此比較容易。早年來深溝,我們一家人可能在夾縫當中就能過得不錯。可是當愈來愈多的半農種子在這裡落地,希望長出一片生機蓬勃的花園,但原有夾縫當中的養分不夠用,該怎麼辦?
.jpg)
一個森林應該有地表層、樹冠層還有林下物種,應該是百花齊放、百工分業的狀態,都市就有一套分工繁複的邏輯,透過資源的創造跟分配讓社會運行。反觀深溝,在農村復興、活化後需要的公共空間創造或系統營建,難道該由我們私人口袋拿錢出來做嗎?這不只不合理,而且也做不起來,我們沒有這麼大的財力,但這事我卻已經做了很久。文全早在 2008 年穀東俱樂部 1.0 轉 2.0 時就曾經告訴我:「你是用私部門的資源在做公共部門的事情」,當時他有一句話保留沒講:「你這樣做不長久」。可是後續我們還是用這種方式在做,只是動用更多人的私領域去做一個公部門的事情。
農村原來的居民不斷離開,人數越來越少,但有一群從外面進來務農的人卻拿不到農民身分,也不在政府的農村編制中。政府高喊「地方創生」、「創造關係人口」,但操作手法卻是自己打架。試問:你們到底是要人來還是不要人來?到底要什麼人來?等了十年、廿年不來的人還要繼續等嗎?
我們成立慢島生活,並與政府合作,這些事情建立在一個前提上:我們忙的到底是誰的事情?既然深溝已經聚集足夠多的人口,公部門又不把半農當農民,我們只好引進外力協助。慢島生活的執行長若甄決定爭取國發會的資金挹注,我們全體股東都同意,某種程度上我們是用夥伴關係來看政府。我們擺設一個舞臺,把系統建構起來,然後確立開放分享的原則,就讓年輕人去發揮,因為未來是他們的。
.jpg)
Q8:您認為深溝經驗可以複製嗎?
A:我希望深溝村以及我現在喜歡的生活是可以長久永續,如果深溝村都做得到,其他村子應該也有機會。我創造了一個可能性,既然案例一能存在,那勢必會有案例二,否則可能是這個時代的幻想而已。
這個問題我在很多場合都被問到,這次我的回答是具體寫出這本「誠實之書」,把我們 20 年的經驗「說好說滿」。我想我們應該是找到了一些農村活化復興的關鍵零組件,其中有一些應該能被其他農村套用,至於在不同的風土人情、社會脈絡上要怎樣重組零件,哪邊要加權?哪邊要省略?這個我們不明瞭,但是我們很樂意跟大家對話。
2015 年文全還在農業處長任內,我們曾舉辦「東亞慢島生活圈」論壇,邀集來自海南、檳城、九州、京都跟香港新界的朋友,我們也跟韓國的農業夥伴有往來。其實這些地方面臨的困境,像是城鄉之間的糾結、都市人想要離開的慾望等等都很類似,如果我們在深溝找到的一點小小的經驗能夠拿出來對話,這應該就是我們最大的願望。
深溝是廿一世紀水稻文明的實驗基地,我們確實吸引了東亞其他水稻文明、甚至跨越水稻生活圈的人來觀摩,似乎有驅動農村移民的動能。如果每個農村都吸引 1,000 人進駐,大家拿號碼牌等著要搬進來時,農村怎麼會沒落?
.jpg)
Q9:農地農用仍然是您的立場嗎?
A:我覺得不容易回答這個問題;我甚至會更挑戰地問說:農地是如何決定的?台灣在法治上是將農民跟農地綁在一起,擁有農地的人接受台灣政府對農民認定的福利和約束,但是當農民無力耕作或者已經離世,而他的下一代拒絕世襲農民身分時,請問流浪農地怎麼辦?這是一個始終沒有人能回答的問題。
我是個文青,我經常認為農夫就是農地的靈魂,一塊失去農夫照顧的農地放上三年,就是一片還諸天地的森林,也就是說,農夫的存在是農地存在的最高前提。當一塊田沒有人要種的時候,好啊,你把農地保留給我看啊。
當年食指浩繁,不斷開山搶地,填海造田,這種事很多國家都發生過,但是當人口開始減少,糧食轉由進口替代時,你們說農地很重要,對,我也同意很重要,但是誰去種?誰去種?無法回答這個問題時,憲法的確保障人民有自由處分財產的權利。
.jpg)
Q10:《農發條例》修正至今 22 年,可否談談您對它的功過評價?
A:《農發條例》是打開了農地鬆動的可能性,但它的前提是「那塊田沒有人要種啊」,這是農村瓦解的過程,政府開放農地買賣是去化農村因為老農凋零而產生的壓力,所以如果我們不從瓦解的部分重新建構,只堅持農地農用,根本沒有解決問題。
農地無人耕作並非台灣的專利,日本緊守農地不能自由買賣,但農地、老屋舍都沒有人要繼承,結果農村變得更加蕭條、農地價格一落千丈。
另一個極端是台灣,農地全數解編,所有都市空間壓縮到沒有辦法抒發的想像力都在農村土地上併發,農地價格高漲又不能生產糧食。
那些批評台灣政策的人,能夠接受日本的現況嗎?我認為光譜兩端之間有沒有其他可能性才是關鍵,可能性很多,半農理想國不過是《農發條例》存在的現況下,我們在夾縫中找到的出路。我們的能量不是靠《農發條例》蓄積,其實我從台北移居宜蘭,某種程度就回應了這個問題,我已經離開倡議的位置,走上創造的道路。
延伸閱讀:
賴青松誠實剖白 01》如何再創農村的盛世?20 年磨一劍,「半農理想國」實戰心法大公開
【書摘】從種稻、種人到種村,深溝村經驗大公開!《半農理想國》開創農業新時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