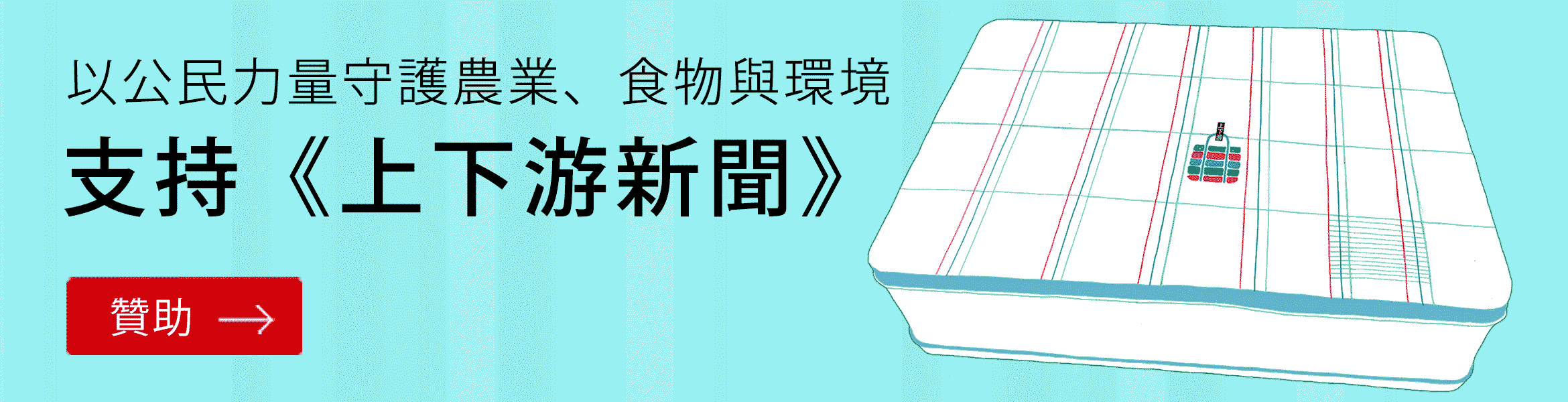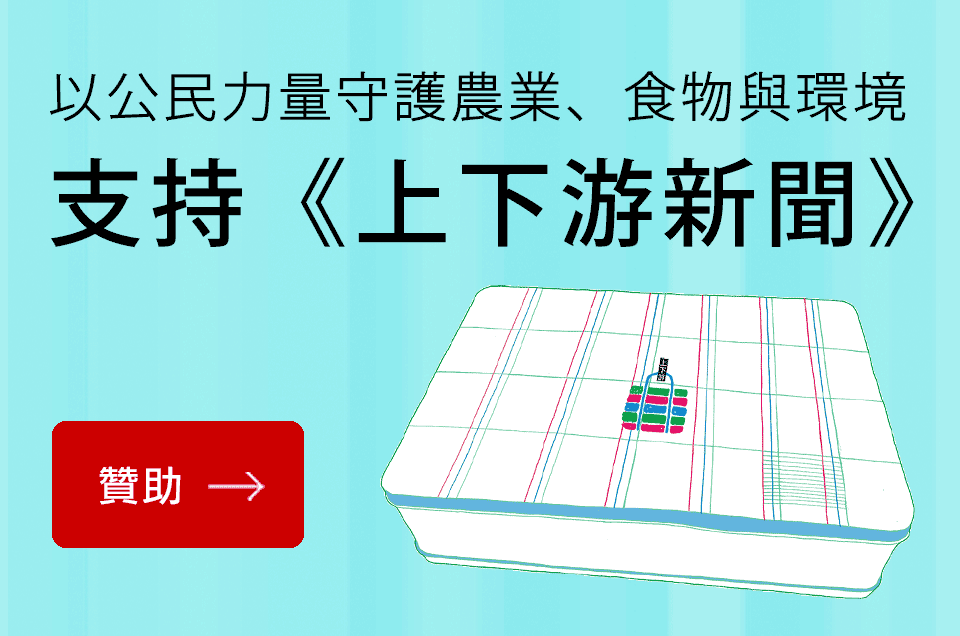入夜,通往嘉明湖的山徑上一片漆黑,整條路上只剩下c一個人點著頭燈悶聲地前進。他踏在由板岩、頁岩堆疊成的路面上像疾步夜行軍般,路徑光禿禿的,因為每年都有太多的人要向這“天使的眼淚”朝聖,光是這兩天,這條路徑就有三百多人魚貫來回,這樣一去一回之間可是踏足了六百多次,要是默默米田裡有這等光景,田間肯定也是寸草不留。可今晚只有c一個人在這條路上走著,有時一不注意黑色的雨鞋踢到質地清脆的石板,石頭相互撞擊發出猶如鋁棒擊中棒球的悅耳聲音。在這海拔三千四百公尺的高度,入夜氣溫頂多七度,c就這麼像要把自己逼垮那樣子地快步走著,肺只是不停地貪婪張縮想吸到更多稀薄的冰冷空氣…
今天是c待在山上工作的最後一天,也是c住在山上的第六天。c心裡很掛念山腳下的默默米,每次看到山腰間的雲海,總會掛心山下的天氣是晴是雨? 田裡的土壤是否濕潤? 默默米是否個個都吸飽了水份精神地長大? 默默米自插秧已過60日,分蘗的情況雖不像一般慣行農法這麼大叢,平均株數只有約10~15株,間距寬敞通風,沒施過肥,也從未見其枯黃。無農藥無肥料的自然栽培,c不用擔心施肥過度造成的稻熱病,也不怕稻子間隔太近互相摩擦而有白葉枯病的可能。趁著曬田期間田裡較無農事,c又跑到山上兼差做porter,想說一方面可以爬山,一方面又可以把房租賺進口袋,還有那台尚在分期付款中的二手鐵牛(耕耘機)。
入秋,c家裡後山上的竹林是最早向c透露秋意的朋友,只見山中竹林轉黃,天空在強勢的高壓氣流下萬里無雲而顯得蔚藍,附近的鳳梨田最近都在忙著採苗,一顆顆小鳳梨成堆堆滿卡車,馬路旁的台灣欒樹已經開出成片玫瑰色的蒴果。c不懂植物和水果,那些都是朋友告訴他的,但他老早就已經感覺到秋天涼爽乾燥的空氣,白天就算曬太陽也不會濕黏流汗,秋天的來臨在台東是再明顯不過。c愛極了這樣的季節,因為這樣的季節最適合爬山溯溪,天氣和溪谷的水量都會很穩定。
這一個禮拜在嘉明湖的日子天氣好得令人捨不得眨眼睛,c每天揹著30公斤的重量上山,在山屋住上一晚,隔天天一亮就又下山準備再揹上山。這樣一趟來回的工錢就可以拿來支付一個月的房租,但沉重的鋁架讓c感覺這一步步都是辛苦,揹帶在肩膀上留下的深痕壓得讓人無法喘息,不時得用汗水濕透的頭帶將重量分配一些到脊柱上。行囊裡的東西五花八門,大部份都會拿來吃掉,像是蔬菜、白米、乾貨、火鍋料甚至是萬巒豬腳真空包,還有一些必要的物資如瓦斯罐和睡袋帳篷。c也揹過一些比較奇怪的東西,像是水泥樁或是無線電基地台的天線,那天線長達五、六米,裹在一層厚厚的紙捲中,要在曲折蜿蜒、樹林密布的山路用人力扛上山真的是要人命地折騰。
但這會兒夜空下只剩c一個人而已,他晚上七點早早洗完供今晚一百七十人晚餐的二十五個鋁鍋和數不清的菜夾子後草草收拾了必要的水和食物,塞入保暖衣物和雨衣雨褲,點亮剛換好電池的頭燈後就飛也似地奪門而出,別人問他要去哪裡,他頭也不回只說要去嘉明湖看水鹿,一秒也不停留地離開了營地。他大步跨在高低起伏的廣闊箭竹草坡上,稜線上冷風颼颼,山勢清晰可辨,只因那黑壓壓的群峰山頭就像被剪刀硬生生剪出一個個黑洞般,夜晚的光線在山的身上有去無回,看不見山上的峽谷、森林和巨石,但卻讓那漆黑的山勢越發險峻。c越走背脊越涼,剛出發時他只有一點害怕,感覺興奮極了,但隨著離營地越來越遠,他的安全感就越渺小,興奮感消失了,大部分變成恐懼、不安和緊張。他腦筋一片空白無法思考,越走越急。他緊張地走著,不斷地向四處張望,腳步凌亂不斷地絆到石頭。有時候,他會和那一對對隱藏在山坡之後的水鹿四目相接,水鹿的兩顆眼睛發出如彈珠般的亮光,倏地起跳奔跑,有時陡下沒入冷杉森林間,有時猛力地向草坡上攀爬再回頭對他回以兩顆寒光。c對水鹿的好奇很快地轉為不安,牠們的神出鬼沒,兩對蹄子踏在地上會發出奔騰懾人的聲響,卻在還來不及看到他們之前就已聽見聲音遠去。牠們總在c沒有防備的時候在他耳邊發出一種尖銳短促的鳴叫,每一次都把他嚇得一身冷顫,拼命用頭燈四處張望,提心吊膽,在那小得可憐的視線內,保衛他那最後一點點的安全範圍。
這山讓他害怕,雖然他知道沒有東西會傷害他。
他沒有回頭,這個想法甚至連片刻也沒有出現在他的腦海裡過。他敬畏地停下來對著遠方的水鹿(眼睛)自我介紹,說出他的名字和來意,贖罪似地說著抱歉,他說他只是想來看看牠們,而他也不知道為什麼。
這幾天和一大群人擠在山屋裡過日子是向來在山裡獨來獨往的c從來沒有過的經驗。他愛山,就像大部分的人一樣,但他從來沒有看過這麼一大群人同時在山上的景象。然而這一兩百人待在山上的小屋吃喝拉撒,就算是每個人帶一點點人類世界的東西上來,也就足以堆出成包成包。在山上有些事是c和大部分的山友不會做的,尤其像洗碗、刷牙、洗澡甚至洗腳這種耗費水源的事情,因為山上的水太珍貴了。如果吃完飯碗裡有油膩的菜渣,那也一定是倒進一瓢熱水拌一拌,把洗碗水當成今晚飯後的熱茶了事。刷牙是一定不會用牙膏的了,不然漱口水要往哪裡吐? 早期爬山的前輩還留下一個迷信說,要是在山裡刷牙,明天包準下大雨。c一直以為這些都是大家上了山理所當然共有的默契,山上有另一種約定俗成的生活模式,而也正是這些讓暫時活在山上的人們有別於以往的自己,暫時地離開文明,放手感受自然的原貌。但是這幾天c看著好多人帶上來一堆吃不完的食物然後毫不珍惜地丟掉,用水的樣子好像水是從自來水廠裡接來似的。這些,c全部都看在眼裡,不斷地忍耐著,他冷眼旁觀,還要縱容自己用沙拉脫洗著他們吃剩的鍋碗瓢盆,c內心充滿掙扎…
兩個小時的路程,c只花了一個半小時就來到湖邊,距離嘉明湖不過兩百公尺。四周一片黑暗,他看不太到,但他知道祂就在那裡。他很驚訝地發現自己有一點點失望,他原本有一點期待能在湖畔邊看到一頂或兩頂帳篷亮著燈,那他就可以下去和他們一起攀談,取暖,也許喝杯熱茶。此時他居高而下,頭頂上的夜空滿天星斗,山凹間瀰漫著雲氣,雲氣平坦厚實而遼闊,反射著星光,覆蓋住眼前所有低於海拔3000公尺以下的世界,好像覆蓋著大地的海洋。一座座高山頓時化作漂浮在夜空中的島嶼,而c就像是其中唯一的島民。
c決定坐下來等待,於是穿起預先準備的雨衣雨褲,在穿雨褲前還先在附近撒了一泡熱尿。他把頭燈關了,四周安安靜靜的,只有微微的風帶來箭竹的搔搔聲音。
等待什麼?
c也不知道,他甚至還沒來得及想清楚今晚那股衝動的來由,他只知道他在山屋裡感覺到強烈的憤怒、羞愧與無奈。四周仍然漆黑得可怕,c感覺自己的感官放大到了極限,他的耳朵、他的眼睛、他的鼻子和身上的毛孔,都在偵查、警戒著。就好像一隻害怕被掠食的動物,捕捉著任何風吹草動,任何東西的接近,連天上一閃一閃的星星都似乎在他的覺察裡。他覺得夜晚的山可怕極了,腦袋止不住地想著會有水鹿在他沒有防備的時候出來嚇他,也許舔他剛剛撒的尿,牠們最喜歡尿裡面的鹽份了。想到這裡,他卻又感覺到內心的興奮和期待。他突然覺得矛盾極了。
看看發出冷光的手錶,坐下來才剛過五分鐘,卻覺得已經過了很久。c覺得自己可笑,大老遠像要遠走高飛似的遠離人群來到這裡,才短短五分鐘,卻已經開始在規劃停留和回程的時間。
到底,人是為了甚麼原因而爬山,而想要接近自然呢?
c強迫自己不開頭燈,在四周摸索著,用手確定四周除了粗短的箭竹以外沒有像刺柏或高山薊那樣刺人的東西,於是他躺下,整片的星海瞬間向他襲來,自從住在台東以後,整片的星星對他來說已經不是稀奇的事,映入眼簾的這熟悉夜空反而使他放鬆。望著浩瀚無垠的宇宙,對於山的愛與害怕,對於離開人群和渴望人群的念頭,此時皆同時存在他的心中。
隔天一早天未亮,山屋旁已經形成一整排用Gore-Tex外套把身子裹得緊緊,顏色繽紛的人龍,人人呵著白色的霧氣,手持相機對著東方準備捕捉日出的那一瞬間,而c已經穿著七天未洗的破褲子,揹著輕裝走在下山的路上,當他拐過向陽主峰的最後一個腰繞時,太陽出來了,一道紅光灑在整座枯黃的箭竹草坡上將向陽山染成了一片紅銅色,同一瞬間山屋出現了此起彼落的快門聲音和驚呼連連的讚嘆聲音,c則留在還沒被陽光照射到的這一面,他愣愣地站在黑暗與白天的邊界,遲遲不敢跨越,只因為這一切太美了,美得不可思議,美得令人害怕如果再踏出一步魔法就會消失。而祂還是消失了,隨著陽光的增強,讓山屋裡的人無法直視,讓c還來不及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