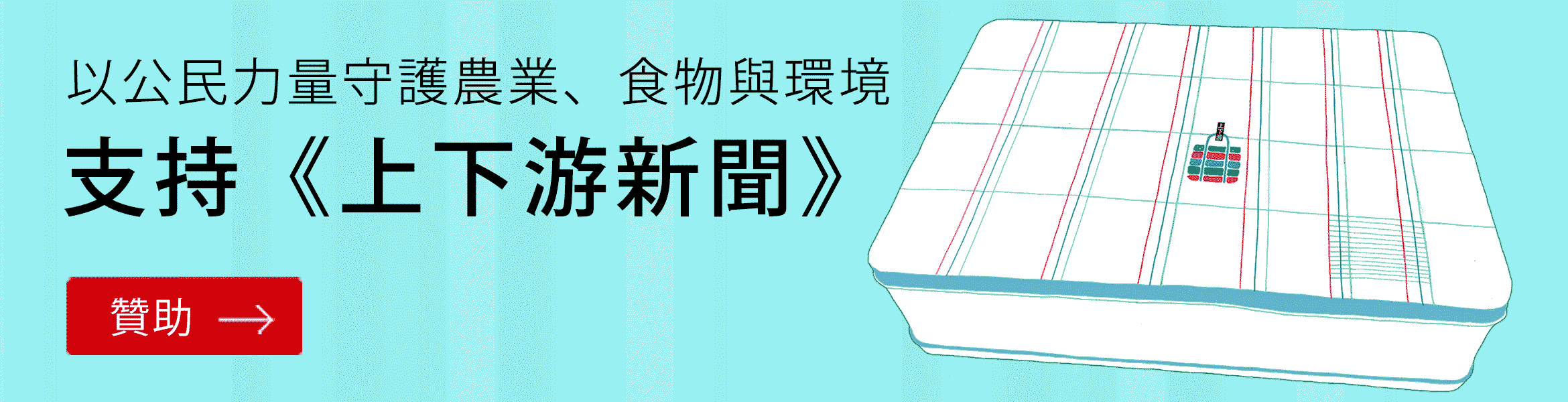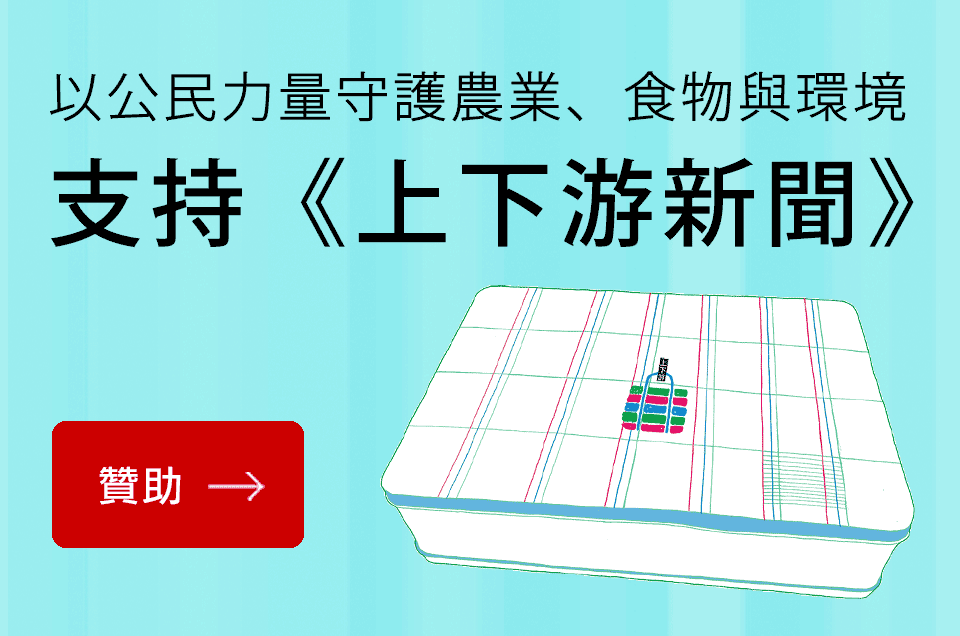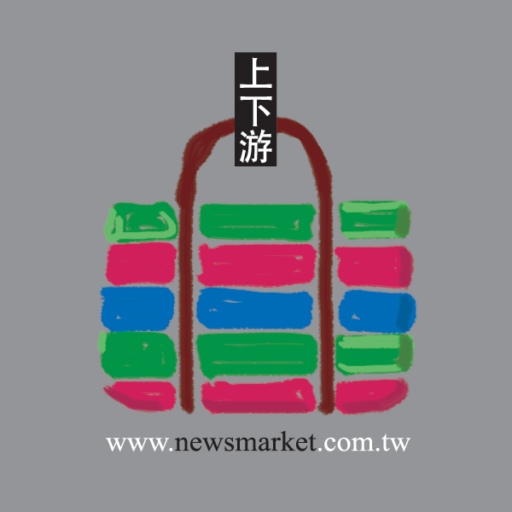同樣稱為「學校午餐」,但在台、日、韓的餐桌上,卻呈現截然不同的世界;不單是台灣各縣市學校午餐始終落於「餐費」、「品質」之間的拔河,甚至偏鄉小校「斷炊」問題更是再三浮上檯面;就連早在1954年就制定了《學校給食法》的日本,也傳出各地方政府執行力度不一,以致給食情況落差極大。
和食給食應援團西日本代表高木一雄直言,「雖說是孩子們的學校午餐,卻由大人的政治角力決定一切。」

過去日本各校營養午餐不同,用心程度不同
日本早在1954年就制定了《學校給食法》,但該法僅為指導範本,文部科學省角色薄弱,實際學校午餐自治權限仍回歸市、町、村地方政府,地方政府全權擔起營養師、調理師廚房設備成本,家長僅需負擔每餐約280元日幣(相當於76.5元台幣)食材成本。
雖然學校午餐與文部科學省(同台灣教育部)有關聯,「但教育單位對於午餐的思考並不深。」同樣以柴魚昆布高湯來說,文部科學省官員就認為,只要能用水調出來就好,在午餐議題上,施力點不足,故日本學校午餐仍仰賴地方政府主導。
隨著各地方政府訂出的營養午餐規格不同,本身是廚師的高木一雄指出,各地學校開始出現給食落差,「有的能吃精緻和食,有的還是只能吃難以下嚥的炒麵、以及昆布粉調出來高湯。」在他看來,根本問題在於「用心」與否。
而現,西日本有60名與高木一雄同樣懷抱熱忱的料理人投入「和食給食應援團」行動,欲透過料理人力量,扭轉深受地方政府主導的給食情況。

60名地方料理人組成「和食給食應援團」,協助設計菜單
「和食給食應援團」在西日本招募60名地方料理人,協助營養師設計出美味、容易操作的和食菜單;雖每個學校營養師、調理師配置狀況不盡相同,但有一套簡易菜單,「5名調理師做出800人份沒問題。」而學童也可在和食午餐中,吃到番茄、雕花紅白蘿蔔等時令食材,高木雄一表示,這也正是「吃當季」的和食精神。
「吃當季」是和食基本概念,也可透過營養師菜單設計,融入學童生活;但高木一雄卻也直言,「吃當地」仍是日本學校午餐難以到達的理想。
高木一雄表示,雖農林水產省主推「吃當地」,學校午餐卻講求「穩定供應」,「如果真的只跟當地農家買,今天一早臨時說沒菜,老師就頭痛了。」再者,所謂「自產自銷」,通常指與自身所在縣或隔壁縣形成產銷供應,「但人口多的都市區不可能種這麼多菜;而鄉村學校若無力經營自有廚房,而仰賴中央廚房供餐,也多會向大盤商叫菜。」
種種實際操作問題加總,以致「吃當地」難以圓滿運作於日本學校午餐供餐鏈中;但高木一雄仍強調,「雖然自產自銷理想很難在營養午餐上實現,但可以確定的是,使用『國產農產』是全國共識。」

韓國:組織學校午餐連線、推動「共同購買制」
不只是日本從草根長出影響學校午餐給食系統的力量,韓國也從2003年開始推動「友善環境免費午餐」社會運動,不僅主張食材使用安全本土農產品,甚至進一步建立學校直營給食系統,要求中央、地方政府分攤補助,讓學校午餐成為安全、營養、且具社會公益價值的一環。
友善環境免費供餐草根國民連線常代表朴仁淑表示,目前韓國全國有70餘個供餐給食支援中心,而各中心營運委員會由市政府、教育廳、專家、公民代表、家長代表共同參與;甚至還開始組織「學校午餐連線」,每年都有兩百餘名家長代表介入參與廠商檢查、午餐監控、以及飲食教育工作。
而為提供安全供餐食材,供餐支援中心、教育廳紛紛推動「共同購買制」,由供餐支援中心共同購買米、泡菜、水產物等食材,而各地方教育廳也個別推動共同購買做法,「以京畿道教育廳來說,共同購買項目包括韓式醬油、辣椒醬、大醬、玄米油、甜玉米等25個品項。」朴仁淑表示,如此一來便可解決學校各別採買食材成本高,且各校也無力判斷食材是否符合安全、友善環境標準問題。
在朴仁淑看來,學校午餐不僅是一天當中的一頓飯,更是教育的一環,甚至還會涉及農業、社會福利、民主自治等公益議題;而韓國供餐系統因為有家長參與,且連同市民代表串聯,讓學校供餐草根運動有更穩固基礎、得以持續發展。

高木一雄:營養午餐難吃,有什麼資格要求小朋友上課?
親眼見證日、韓兩國學校午餐實況,富邦文教基金會校園午餐22計劃主持人黃嘉琳感嘆表示,台、日、韓三國學校供餐均始於二戰美援,但近幾年來,三者的發展差距卻越來越大。
黃表示,日本首在1954年就制訂《學校給食法》;韓國已確立《學校給食法》,且建立出一套類似社會福利的給食政策;反觀台灣,「卻幾乎在這二、三十年內產生停滯狀態,台灣營養午餐到底出現什麼問題?」
在日、韓角度看來,學校午餐早已是學生「基本人權」問題,高木一雄直言,「吃難以下嚥的營養午餐,學校有什麼資格要求小朋友要上全天課?又有什麼資格要求小朋友寫作業?」
站在料理人立場,高木一雄現僅能竭盡所能,串起地方料理人與學校營養師的互動關係,「一天一餐而已,不用很豪華,但是好吃、營養、美味,讓小朋友好好過一天,這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