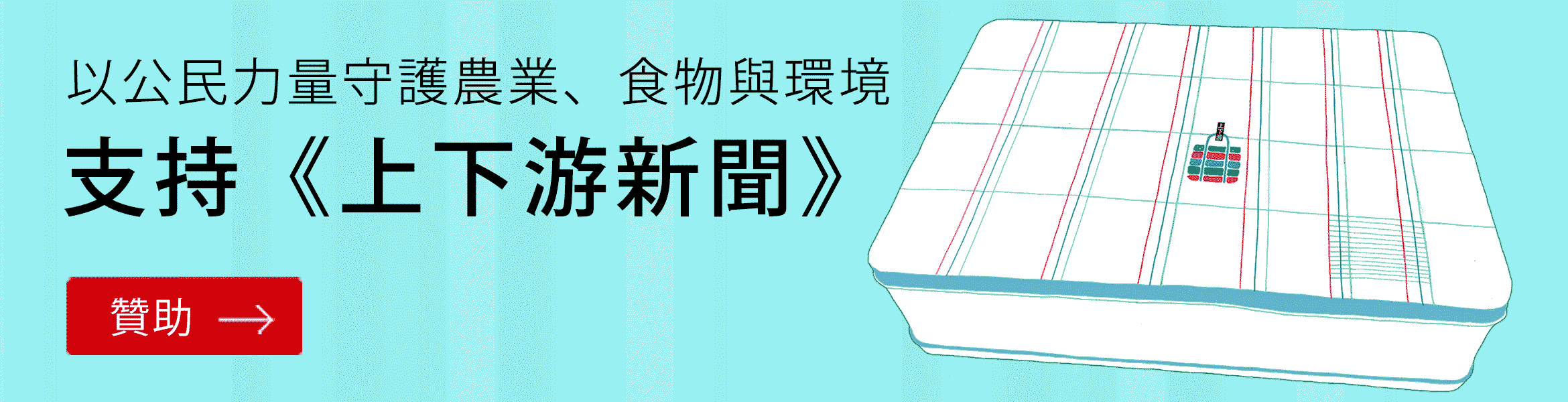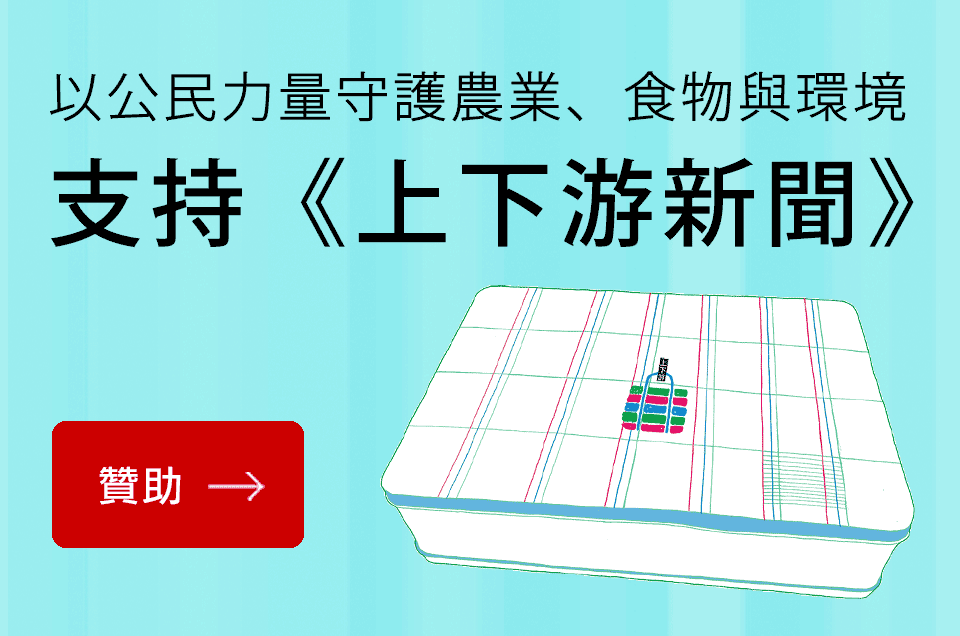晚上九點,阿義農機行的鐵捲門還開著,自裡向外,孤獨地在漆黑一片的稻田中央透著白光。阿義坐在他家的客廳,他工廠的辦公室,坐在一張不大不小的茶桌旁,一壺滾水正嘶嘶作響冒著白煙,茶壺茶杯上沾著厚厚茶漬,看起來用了很久,電視螢幕安安靜靜,除了日光燈管發出的嗡嗡聲,只剩下阿義不規律的呼吸。
阿義坐著發呆,右手的菸早已燒到只剩菸蒂,長長的灰燼硬是還連在上面。老婆和兒子都在樓上睡覺,今天也真是辛苦他們了,念國中的大兒子為了踢足球飯都可以不吃,一有機會就只知道要踢球,但今天乖乖地開著這一期最新貸款來的插秧機陪了媽媽一整天,一口氣種完家裡的三四甲地。其實種田對開農機行的阿義來說只是順便兼著做,反正不管是曳引機、插秧機、割稻機和載穀車都是家裡的自有機器,只吃油錢,工錢就算自己的。他真正的目的是為了和米廠打好關係,必要的時候才方便週轉資金。大家都以為阿義的農機行很賺錢,畢竟各大米廠聯合把持收購價格的情況下,農夫大部分的利潤都被機器代耕的費用吸收了,如果遇到歹年冬,天氣出了差錯,種得血本無歸的人也是大有人在。阿義嘆口氣,抖落手上的菸蒂,隨抓了一把茶葉丟進茶壺,沖上一泡熱水。
確實阿義應該要賺到錢的,當初他白手起家在祖產的地上蓋了這間大工廠,就是看準了大機械耕作的時代就要來臨,誰知道他只看準了趨勢,卻漏看了人心,農忙時期四處替人翻土佈田,辛苦了一個月,卻常常落得收不到錢的下場,等來等去,每次去收帳總是等到一句: 「等收割了再說。」,阿義有時候暗自咒罵,「幹,拔郎ㄟ囝仔死抹了…」。現在生活甚麼都要錢,那個互相用人情和人力交換的時代早已過去,家裡光是那些農機具的貸款就是一筆不小的數目,兩個兒子念書要錢,家裡還有老爸老母要養。
現在,又多了一條看病錢。
茶泡好了,那是40歲的阿義要拿來配藥的,凌亂不堪的櫥櫃的最外頭堆放著老婆替她整理好的大小藥單,一次就是好幾種阿義也搞不懂吃甚麼意思的藥丸子,阿義只知道不吃就會痛到送醫院,但吃了他知道今晚又一定會睡不著。他以前太愛喝酒,過去的日子醉得一踏糊塗,日還沒過午,就可以看到他不醒人事醉倒在田埂邊,酒就像是他生命的來源,好像如果失去酒精的濛茫,他就不再叫阿義了。如今醫生警告他再碰酒精就等著被抬進棺材,阿義從此滴酒不沾,但菸和檳榔倒是吃得更兇。阿義對此沒有感覺頹喪或悲傷,或任何一點點的不安與焦慮,他只是覺得命運給他這樣的安排讓他覺得很背。
「幹。」
阿義一口氣吞了所有藥丸子配一大口嚐來苦澀的茶就起身穿了外套向外走,拉下鐵門,外面的世界突然陷入漆黑,沒有路燈,沒有鄰居。阿義熟練地跳上200匹馬力的曳引機,發動輪子比人還高的大車隨即踏足油門揚長而去。在家家戶戶都要熄燈,阿公阿嬤們都把電視機裡的鄉土劇關掉的此刻,阿義曳引機卻轟隆隆地吵鬧著,車子開進田裡,靠著月色和車燈,阿義精準地將車後的螺旋刀片埋進土中,田裡的土頓時像是水煮開了那樣翻騰起來。
正當現實的一切排山倒海而來等著阿義去面對,阿義選擇在夜晚辛勤的工作,既像是一種勇敢又像是一種逃避。今晚的月亮又圓又亮,就算不開車燈也能夠看見照得銀閃閃的大地,東邊的都蘭山像一塊盤古劈天的巨石,黑啞啞地落在阿義的心頭,阿義操控著曳引機,在田裡來來回回畫出一行一行的黑色直線,遠遠看好像是在看一場骨牌秀,你期待骨牌全倒後會出現甚麼美麗的圖案,到頭來卻只等到另一種黑暗。
車子很快做完這一塊,正往比較遠的武陵駛去,阿義注意到隔壁的田已經粗耕過了,還架著一個棚子,裡面擺滿了秧盤,秧盤裡還看不出來有長出甚麼東西。
「幹拎鬼勒,這個少年人真的是頭殼燒壞去…」
阿義搖搖頭嘴角上揚露出微笑,他其實還蠻喜歡這個年輕小夥子的,自己一個人口袋空空到鄉下來種田,連跟阿義買個鐵牛都要分期付款。在這個甚麼都靠大型機械的時代,卻有個少年人還甘願用一台小機器慢慢地做,讓阿義覺得頗有自己當年白手起家的拼勁,因此總是原諒年輕人沒有經驗的笨拙,願意幫他一些。但阿義實在對少年人做的甚麼自然農法斥之以鼻,他覺得年輕人的頭殼壞去,盡是做一些賺沒有吃穿的事情,明明有現成的秧苗不買,硬是要自己育苗,老是跟阿義長篇大論一大堆,搞不清楚到底誰才是那個種了一輩子的田的人,跟他講說稻子要打藥施肥也不聽,還真以為稻子光是吹風喝水就會長大,上一期要不是那塊田好,年輕人的稻子才沉澱澱的,但是收成只有人家的一半,這樣哪有錢賺? 如果阿義種的田沒有七割(註1)可是要賠本的,誰還顧得了甚麼自然不自然的農法? 只是阿義聽說年輕人的稻子都賣去台北,賣得奇貴還賣光光,讓他覺得台北的人大概都是好命人,不像他們的穀子只能賤價給米廠收購。
車子繼續幹著活,阿義突然覺得一股強烈的睡意襲來,轟隆隆的低頻噪音變成一首反覆播送的催眠樂曲,車上的沙發椅突然間變得好軟好暖,沉沉的眼皮眨阿眨的,像是用久了的日光燈管昏暗地一閃一閃,隨時都想放棄的樣子,阿義好久沒有這樣愛睏了,他的額頭漸漸靠在方向盤上,深深地睡去,那台200匹馬力的龐然大物,還在天色將亮的清晨裡發動著,發出轟隆隆的無言抗議…
註1 : 七割為成數之意,指一分地可收700台斤的穀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