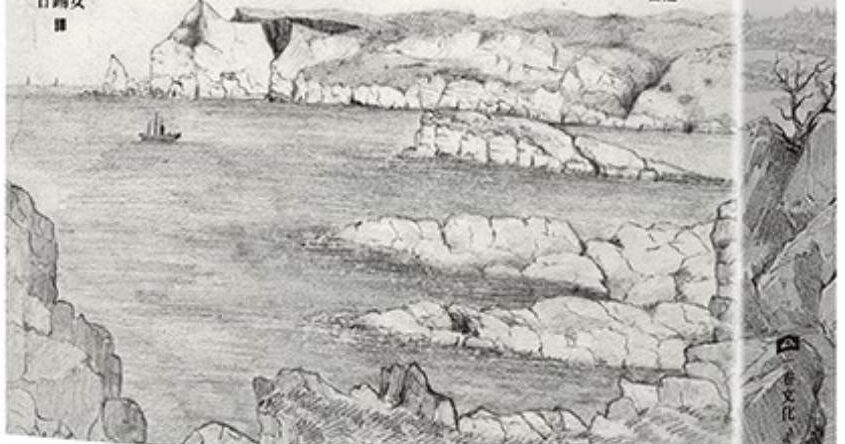這個化石是否可能是單一事件,有一隻布西櫛蟲很早就出現在寒武紀期間,但下志留紀才是它的全盛時期?如果確實如此,他們朝東走向英格蘭邊界年代較近的岩石時,布西櫛蟲等生物應該會變得越來越常見。
一八四一至四二年冬天和春天,對塞吉維克而言一定相當難過。莫奇森已經從俄國回來,自信滿滿,現在自認為是已經登上國際舞台的重要人物。他可以宣稱已經測繪歐洲和俄國許多地區的地質,而且鑑定出三個新的地質時期並獲得國際認可,成就超越所有地質學家。此外,他的妻子夏綠蒂剛剛繼承一大筆遺產,夫妻兩人從位於倫敦布萊恩斯頓廣場(Bryanston Place)比較低調的住宅,搬到貝爾格雷夫廣場(Belgrave Square)的豪宅,這裡是英國首都最高級的地區。
莫奇森現在定期舉行盛大的派對和晚會。一段記述提到:「國務大臣、貴族、科學界、文學界、藝術界人士和旅行者都在這裡聚會。」[1]年輕且剛嶄露頭角的作家約翰.拉斯金(John Ruskin)寫道:「我不知道莫奇森多有錢,但這真是有夠誇張的。房間都是淺灰色和金色,華麗的屋簷和阿拉伯式花紋,就像彩色的龐貝城。家具都是深紅色花緞絲綢和黃金,完全看不到木頭,至少四名男僕來來回回把每個來賓的名字傳遞到樓上。」[2]莫奇森過去的失敗,不怎麼傑出的軍旅生活,以及無法成為鄉紳的過往,都已經煙消雲散。據說他現在刻意培養「退伍軍官的特質」,而且在無數的晚餐後演講中「不厭其煩地提到他早年在半島戰爭中的功勳」。[3]
這一切都有賴夏綠蒂在背後協助。她累積了不少自己的化石收藏,頗受敬重,被評價為「文雅、聰明,又能談論各種主題」[4]。朋友們發現莫奇森在這一年內變得更自大也更高傲,依據某個同事的說法,他「對反對意見越來越不耐,而且越來越喜歡要求其他同事在他們的作品中特別肯定他的貢獻」。[5]另一位同事則說,此外他很容易「以高人一等或居高臨下的態度談論同時代的其他學者,尤其是年輕人。他以前可以說是軍隊的團長,現在更覺得自己已經擁有師級將領的權力」。[6]
塞吉維克平凡單調的生活,跟莫奇森對比之下落差極大。不過塞吉維克現在也擁有舒適的房屋,俯噉著三一學院美麗如畫的大庭院(Great Court),有一間臥室,飯廳裡掛著約克郡谷地、諾里奇和湖區的風景水彩畫,還有許多椅子和沙發,還有一間擺滿書的房間,他大多坐在這裡,桌上和大多數椅子上擺滿信件和紙張[7]。他也舉行和參加派對,經常「不請自來地出現在好朋友桌旁」,他以健談聞名,因此「他開始講故事時,四周就一片寂靜,直到他講完為止」[8]。但這些聚會跟莫奇森光鮮亮麗的晚會相比,只是小巫見大巫,同時,塞吉維克仍然被教會和大學工作綁得動彈不得。
冬天這幾個月,他繼續在諾里奇大教堂執行牧師工作,生活成為單調的例行公事。他在給朋友的信中寫道:「我起得很早,通常是五點到六點之間,早上做完所有工作,通常其他人還沒有開始活動。我的僕人九點鐘來,九點十五分早餐,早上十點在大教堂晨間禮拜,禮拜後處理一些雜務,交代些事情或購物等等,一點鐘午餐,接著是跟我姪女一起騎馬(我有時間的時候),四點鐘又在大教堂主持禮拜,六點鐘晚餐。」[9]在劍橋,他必須面對的工作同樣繁重。他寫信給姪女芬妮:「眞希望你能來看我,我最近脾氣很糟,但又像一塊香噴噴的牛排,周圍環繞著六十九個可憐的大學生。我要這些學生翻譯一大段拉丁文,讓他們苦惱不已。」[10]芬妮是他經常通信的許多女性之一。
在此同時,他的健康也日漸變差。劍橋地勢低窪、潮濕又寒冷。來自北歐和俄國北部的刺骨寒風呼呼地吹過三一街,塞吉維克年年因為流感和痛風而病倒,使他臥病在床,無法工作。他寫信給凱特.麥爾坎(Kate Malcolm)時寫道:「這三個月來……我在流感攻擊下幾乎都待在壁爐邊(一部分時間在臥室)。」凱特是老友的女兒,也是經常通信的女性之一[11]。「只要流感一好,風濕性痛風就取而代之,所以我去泡了今年四月去過的巴斯溫泉,想把病魔趕出骨頭。」[12]
更重要的是,他探討年代較早的雜砂岩的「大作」已經慢慢有了進展。他的傳記作者約翰.威利斯.克拉克(John Willis Clark)和湯瑪斯.麥肯尼.休斯(Thomas Mckenny Hughes)寫道:「它設想的規模太龐大,撰寫時的細節又太多,偏偏作者的生活被其他事物佔據,又苦於持續不斷且越來越嚴重的疾病。」[13]塞吉維克自己在沉思時也意識到這個問題。他深思後寫信給莫奇森道:「我可能會到德國隱居一年,在某個水療地租個房子。這樣我寫書的速度可以輕易提高。我好了之後,就能寫得很快,而且我現在覺得資料都已經準備好了,但在劍橋,各種感覺讓我困擾不已。」[14]
莫奇森相當幫忙,但現在他顯然有自己的計畫。一八四二年二月,他第二次當選倫敦地質學會會長。在會長就職演說中,他回頭談到寒武系和志留系地層之間的界線問題。他告訴塞吉維克:「我在其中加入很多資料,包括國外和國內。」[15]一位聽眾表示:「他在這篇演說花了很大的功夫,在文字密密麻麻的學會會刊中佔了四十頁,光是份量就足以使讀者和聽眾感到疲倦。」[16]此外,他也毫不害臊地自吹自擂,做作地寫道:「藉由自己的獨創研究,為一群岩石加上永久的名字,是地質學家嚮往的最高榮耀。」[17]這是指他自己命名了志留紀、泥盆紀和二疊紀等時期。
但他演說的重點集中在他和其他人早已知道的概念。他主張:「寒武紀岩石中是否有不同於下志留紀的化石,仍然有待確定。如果大自然給出的答案是否定的,則下志留紀顯然必須視為雜砂岩眞正的基底。」寒武紀則應該僅限於非常古老的岩石,其中沒有任何化石紀錄。[18]八年前把吉力格林採石場等地點的巴拉岩石隨意判定為寒武紀,同時把什羅普郡小村莊梅佛德極為類似的卡拉多克岩石判定為志留紀,這個一八三四年的舊論,回頭纏上了塞吉維克。莫奇森現在宣稱巴拉石灰岩在他的範圍內,現在屬於擴展的志留系[19]。這個概念不僅把他的「封地」擴大到接近整個威爾斯,也意味著志留紀是地球史上開始有「生物存在」的時期[20]。
塞吉維克錯過了這次會議。他事後看到會議紀錄時一定覺得十分驚愕。如果要阻止莫奇森試圖奪取巴拉石灰岩和鄰近的岩石,他必須提出證據來支持他的「漸進論」概念。

六個月後,一八四二年夏天,塞吉維克帶著新的進攻計畫回到威爾斯。先前造訪時,他留意到,柏文山中除了有巴拉石灰岩層,似乎還有其他石灰岩層大致呈南北走向通過這個地區的山丘,就像牛排上的雪花紋路一樣。他原本一直認為,在威爾斯北部從東向西走時,岩石越來越古老,所以石灰岩層應該也是如此。現在他的新想法是回頭觀察這些模糊的石灰岩層,希望穿過開闊的泥炭沼地,從史諾登尼亞走到英格蘭邊界時,能遇上一些化石來支持他的「漸進論」。這些石灰岩層是這個地區少數的化石來源之一。
他已經掌握很有意思的證據。幾個月前,塞吉維克收到「業餘」地質學者約翰.包曼(John Bowman)的幾封信件。包曼是雷克斯漢姆的退休銀行經理,四十五歲就賺夠錢,使他可專心研究自然史。包曼近兩年夏天都在刷擦這些石灰岩層。在史諾登尼亞北側山坡最西邊的露頭,他發現了下志留紀的化石,包括布西櫛蟲(Asaphus buchii),這種櫛蟲(三葉蟲的一種)的化石,被視為莫奇森的下志留紀蘭代羅薄砂岩的重要標記。
但史諾登尼亞的位置牢牢被歸類為寒武紀的地區。包曼的發現指向兩個可能的結論:第一個是威爾斯的志留紀岩石範圍遠大於任何人目前的想像,如此一來,志留紀時期的基礎將更加薄弱。第二個是這可能證明塞吉維克的「漸進論」模型正確,塞吉維克當然希望如此。
這個化石是否可能是單一事件,有一隻布西櫛蟲很早就出現在寒武紀期間,但下志留紀才是它的全盛時期?如果確實如此,他們朝東走向英格蘭邊界年代較近的岩石時,布西櫛蟲等生物應該會變得越來越常見。
塞吉維克希望親自跟包曼走一趟,但當年冬天,這位退休銀行經理突然去世。少了他陪同,所以塞吉維克和威爾斯首屈一指的古生物學家,一位「神經容易緊張的人物」約翰.薩爾特(John Salter)一起前往[21]。薩爾特當時二十二歲,專門知識豐富而備受敬重,但這也代表化石研究當時才剛萌芽。薩爾特已經為莫奇森提供重要協助,負責鑑定和分類莫奇森的志留紀化石收藏,並為他的「志留系」繪製插圖。塞吉維克告訴朋友,他是「優秀的年輕博物學家」,「似乎相當喜愛古老的化石物種」[22]。這是塞吉維克第一次感到有必要找古生物學家一起前往,代表他認為這次行程十分重要。(本文摘錄自《失落的三億年 史詩般的地質年代發現之旅》,小標為本刊編輯所加。)

【說說書】
十九世紀三位地質學先驅的發現
文/一卷文化
我們今天所知的地質學年代劃分是怎麼來的呢?古生代的志留紀、寒武紀、奧陶紀等等,大部分是透過十九世紀三位地質學先驅的發現才得以確立的。維多利亞時代的人們,與今天的我們相比,所知道的非常有限。地層與年代的劃分在當時初見雛型,但英國的威爾斯有一些極為雜亂而不連續的地層,難以解釋,在當時始終是地質學上一道懸而未決,等待高手來挑戰的難題。
一八三〇年代,就在達爾文搭乘「小獵犬號」至加拉巴哥群島的同一個時代,英國兩位業餘的地質學家,一位是牧師出身的塞吉維克,一位是軍人出身的莫奇森,他們勇於挑戰這個無人能解的難題與懸案,他們跋山涉水,在威爾斯、蘇格蘭鄉間崎嶇的地形上到處挖掘石頭、化石,推測地層及年代, 他們的發現,令當時的學界為之震撼。而他們既合作又競爭,亦敵亦友,後來不同的觀點引發志留紀與寒武紀如何劃分的激烈爭論,甚至演變為互相攻擊,不惜反目。他們的激烈爭論為既為了學術的真相,也為了個人的名聲與榮譽,是非成敗,成了一團糾纏不清的糊塗帳。
塞吉維克與莫奇森的發現,雖然奠定了志留紀與寒武紀的基礎,但只將懸案破了一半,仍留下不少疑點,直到三十年後,終於出現第三位業餘學者拉普沃斯,發現了破案的關鍵: 筆石,從而確定了又一個新的地質年代:奧陶紀……
三位主角在英國的威爾斯、蘇格蘭與俄國西部探勘成果,揭開了古生代(距今約5.4億年至2.5億年前)這長達三億年期間的祕密。就在這段期間,地球上開始出現了可識別的生命。本書作者戴維森,考證了許多珍貴史料,包括地圖、日記、信件、田野筆記和當時的文獻記錄等,挖掘出這段歷史,讓我們跟隨著他們的足跡走遍曠野追尋線索,讓這三位容易被忽略的地質學英雄,栩栩如生地重現在我們現代讀者的面前。
本書所描述的這些故事,不光僅是地質學的發展歷史而已,在我們跟隨著作者的文章,穿越英國一些最壯觀的地景時,將能夠體會到:歷代的地質學家們,在探索腳下的大地時,所獲得的那種最純粹、最直觀的暢快感,使人不由自主的打從心中,對大自然的奇蹟發出由衷的讚美與讚嘆。
人類由古猿演化而來、地球有四十六億年歷史,對今天的我們來說,是小學生都知道的常識。但我們今天之所以能知道得更多,不是因為我們比較聰明,而是因為我們站在無數前人研究成果的肩膀上,而這些研究成果往往並非一步而成,而是歷代科學研究的先驅們,在一連串不斷的嘗試與錯誤之中,在歧見的論爭甚至互相攻擊之中,點點滴滴的累積,披荊斬棘所開闢出來的知識之路。本書的故事,可說是以這三位地質學的先驅為例,精采而生動地還原了這些過程,堪稱是科學發現史上的重要的一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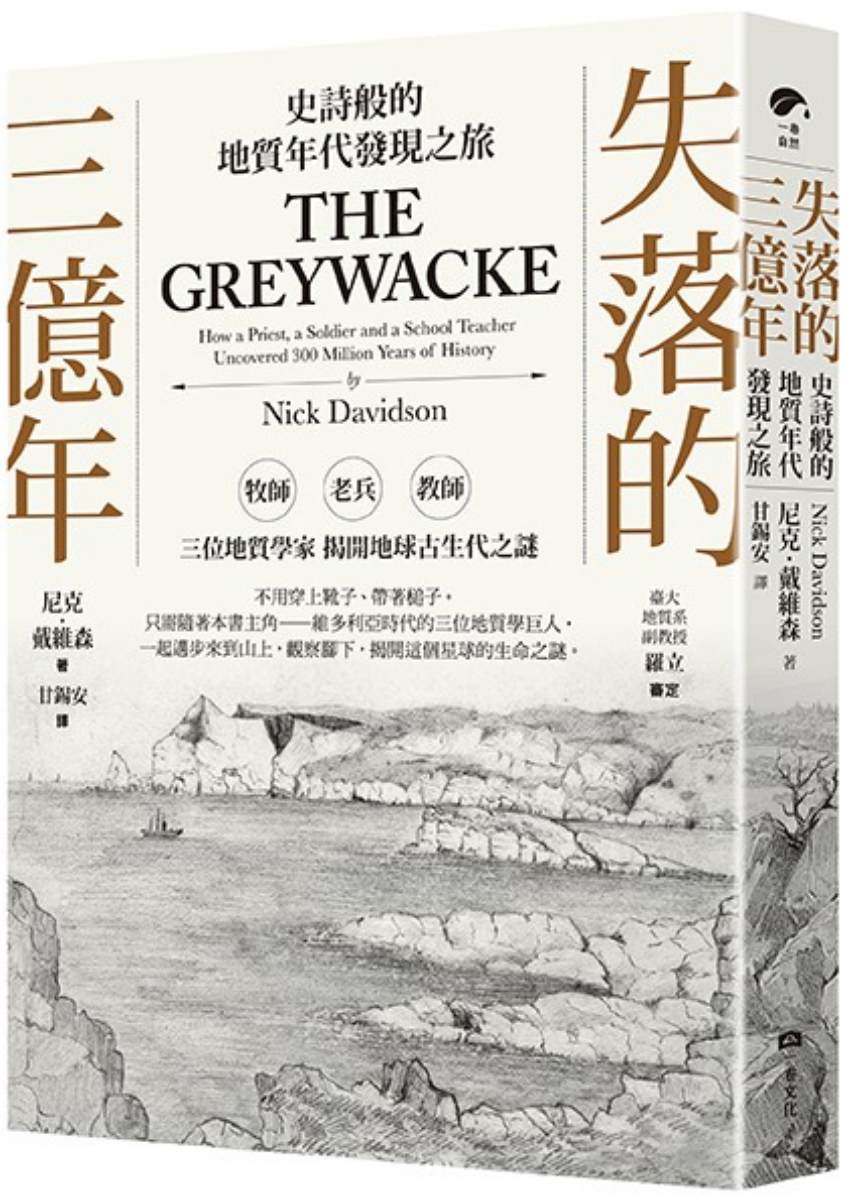
書名:失落的三億年 史詩般的地質年代發現之旅
作者:尼克.戴維森(Nick Davidson)
譯者:甘錫安
出版社:一卷文化
出版日期:2025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