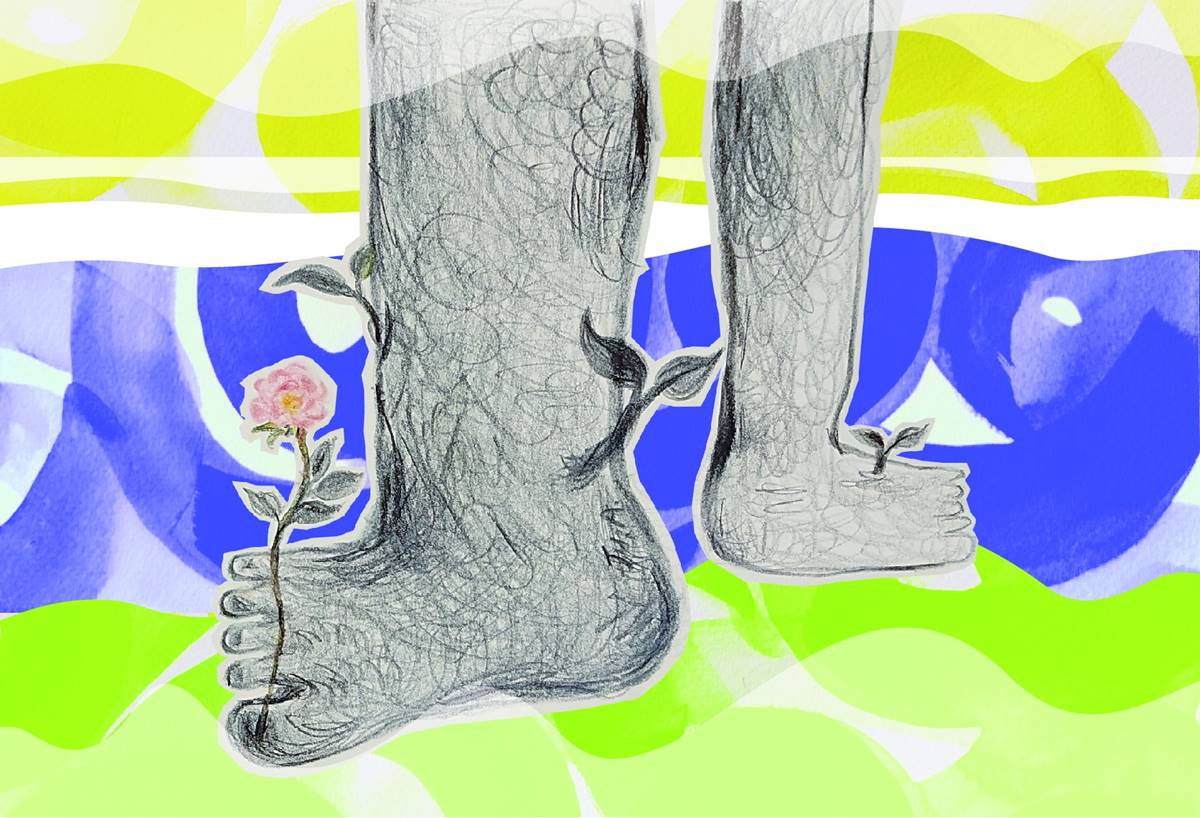{留下來的人}專欄
對於他從何得知阿嬤往生的事情,我毫無頭緒。只能猜想,鄰里間仍有些網絡,哪一輩與哪一輩,還留在豐田或附近村莊,總之,雖然他是離開的人,但,願意來看阿嬤,對我而言,是真正留下來的人。
阿嬤走了。
取消了所有事情,每一天,到靈堂,陪我最親愛的阿嬤。
上小學後,一整週待在豐田,是第一次。
小時候,不知道什麼是城鄉差距,後來,也很討厭這四個字。城鄉?比起花蓮市,豐田是「鄉」沒錯,可是跟台北比,花蓮又成了「鄉」,那麼,台北跟東京或是巴黎⋯⋯
我以為沒有那麼絕對的事情。但,或許除了「城鄉差距」以外,有些更為潛在的事物,在每個人生階段裡,發酵,轉折。
最早的「市井」概念,在豐田,那時,對我而言,它既是城,也是鄉。起床大喊一聲「阿嬤!我起來了!」走下樓,四處是好玩的事。
初次嚐豆花跟愛玉是在市場旁的甜水攤,跟阿嬤去買菜時,老闆會塞給我糖果。有學生整天聚在大型機台對陣快打旋風,好崇拜會打電動的大哥哥,觀戰總叫我廢寢忘食。公車站來往的人們形形色色,不同款式的行李箱,是最讓我好奇的物件,去哪裡,會需要用得上比背包更大的東西?
孩提「入世」
隱隱的生活守則,在鄉間生活流轉,哪家大人跟哪家比較好或不好、買哪一類雜貨時要去哪家、另一類則要去另一家。反正照著阿公阿嬤講的就是了。回憶起這些,在阿嬤的遺照前,浮現一些頭緒。
我時常去髮廊看電視,奇怪,我家也有電視,為什麼髮廊可以看到那麼多日本跟西洋電影。油漆商拿著新的目錄來推銷,上面的顏色都有編號,咦,顏色是用編號分的嗎?阿棟叔叔的雜貨店,某一些醬油跟麵條,缺了好久也沒補,問了也沒有什麼下文,但大家也沒真的在意。這類事情,完整了我的兒時「入世」之道。
這些都是在道路拓寬以前的事情。從省道變成國道,土地徵收,兒時玩耍的前庭(油漆、松香水等器材擺售處)被夷平,我的豐田畫面起了變化。

路寬了,家窄了
老家前面的路,雙線道變成四線道。原先寬敞的房子,硬往內擠,路寬了,家窄了,前庭沒了。鄰里間跟我們家一樣,紛紛移去了店面或騎樓。有不少鄰居將地轉租給做新生意的人,新的店家更迭頻繁,幾乎沒有能做起來的。幾個月沒回去,旁邊那個漫畫出租怎麼不做了?自助餐店不是才開沒多久?閒置的房屋變多,甚至也不貼「出售」、「出租」,一個個,空蕩的,拉上鐵門。選擇賣掉土地,搬離豐田,當然更大有人在。四線道上,人煙稀少,舊有的秩序被新路或時代給重置。
我的「市井」破滅,但又能怪誰。怪時間吧,怪我自己沒有意識到,消逝的概念不止存在藝術裡,真實的世界,你以為來得及瞧,一切就變了。
最弔詭的是,四線道以後,豐田村出現了便利超商。我從沒想過這裡需要便利商店,誰會去啊?鄰里之間根本是「友善監視器」,要買零食飲品,你會去阿棟家;柴米油鹽,講究一點去農會,不然找市場攤販即可;微波鮮食?這裡的人都開伙,誰會去弄個義大利麵吃。我真心覺得,便利商店會倒吧?
這才是城鄉差距?
「人情稅」
全家便利店開設那年,阿嬤要我去張羅年夜飯的飲料,叮囑:「要去阿棟哥哥家買,不要去便利商店買。」
對嘛!在「技術」上,你要如何「步步」經過還留在這的人家,「喜新厭舊」學都市人「追流行」去買可樂、蘋果西打,阿棟哥哥家都有啊,還賣比較便宜⋯⋯
等等,未必比較便宜喔,可是,你得算「人情稅」在裡頭。
「人情味」?我覺得,人情稅好像更貼切一點。稅,是義務。「因為有人情味」,抱歉,在豐田小孩如我看來,是講給都市人聽的情懷。你不課稅,茲事體大。
阿棟家飲料進貨來不及冰,我「犯大忌」到全家去買,兩件八八折,回去之後被阿嬤一陣碎唸,「就叫你去阿棟家買,你們少年人實在是⋯⋯」。
以前,誰人家裡上新油漆「膽敢」不來我家買?買一隻雞,逃不過阿桃家的眼線,不然雞是哪來的?市區買下來的?阿你後生不就很偉大!市區的雞比我們的土雞好吃?!
直到我們家迎來「歷史協議」,年夜飯用叫的,不自己煮了。拿著年菜DM跟老人家討論,哪一家特色怎樣如何,阿公默默的說「咱就叫對面的餐廳」。
從此,吃了不知道幾年對面做的年菜。一家人幾代,用推車穿過四線道,菜餚送了一家又一家。「歷史協議」背後的妥協,是要給對面餐廳課人情稅。別說好不好吃,別問為什麼整個村都要叫他們家的菜。人情稅。
治喪期間,經過阿棟雜貨店,已看不太出來是阿棟的誰在經營了,是我長大了看多了,還是那個店面已經不太算是店面?前往7-11,有個漫長紅燈,老家鄰近一整排荒蕪的商家,都是自己的地,隨意做個生意,賺點補貼。
豐山國小的學生,傍晚佔領超商,與行車往來稍事歇息的遊客一夥。我用行動支付買了咖啡,走回靈堂的路上,那個漫長的紅綠燈,使我感覺到「人情稅」已經停止課徵。
留下來的人,不多了。
人情稅的消失,該是城,該是鄉,制定了新的人情級距。
留下來的人
「我以前住對面,紅綠燈,靠近農會超市那邊,跟你阿嬤很熟,時常遇到。」
「現在喔,沒有了啦,早就搬了。你那時候可能還小咧,鐵路局徵收土地。」
「做這麼久鄰居,一定要過來一趟。」
對他從何得知阿嬤往生的事情,我毫無頭緒。只能猜想,鄰里間仍有些網絡,哪一輩與哪一輩,還留在豐田或附近村莊,總之,雖然他是離開的人,但,願意來看阿嬤,對我而言,是真正留下來的人。
「我要叫⋯⋯我要叫你的阿嬤『姑姑』。」
阿嬤,你的姪子從平和村看你,你要保佑他健康平安順心。
「姑姑以前很疼我。」
目測六十歲上下的男子,淡淡說著,眼眶自然的泛淚。我遞面紙,他揮揮手表示沒關係。我並不認識他,此刻,卻很想與他多談。
「我在外面坐一下,你忙,沒有關係。」
喪家不宜送別前來弔唁的人。我看著他,就這麼坐在那,一陣若有所思,用手擦淚,然後駕車離去。
告別式當天,這些親友,又來了一趟。他們靜靜站在會場外,直到儀式結束,一齊,向棺木鞠躬。
不知道此生還會不會遇見他們,然而,豐田召喚了我,那個當下。
阿嬤留在豐田,直到最後。跟這些留下來的人,一起。
還能夠好好告別,何嘗不是真正的留下。人與人,時間與時間。
阿嬤走了,我才發現,留下來的人不多了,豐田,是荒蕪了。
但同時,我也意識到,肯回來的人,其實都是真正想留下來的人。
就像我一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