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地要農用,聽起來簡單,也可以輕易地成為旗子上的標語,但實際上該如何推動?
宜蘭小農吳佳玲指出,農地是生產要素的首要,沒有農地,遑論農業,農業改革的當務之急,必須要先盤點還剩多少可以生產的良田,更應確保農業生產的優先性,維護台灣的糧食主權與安全;其次,農村生活的基本需求,例如居住、公共設施,皆應有完整的鄉村規劃,而非任由這些實際的需求在農地上恣意蔓延。
綠黨中執委、同時也有多年耕作經驗的農民吳紹文也持同樣看法,她強調農業發展區中的「農一」是敏感地,但到底量有多少?農民都在期待結果出來,若要真正解決農地農用問題,未來農委會就得在盤點基礎上,利用《國土計畫》好好統整現有農地狀況,並把農一區域擴大、同時限制該地不得做農業以外其他使用,「對地補貼」部分也應該加速進行,一來可以提升農民收益,二來將農地租給農民的地主也可分得些許租金。
對於現有的違規,吳紹文則表示在地方政府資源有限、查緝及違建拆除執行成效不佳下,應該回歸課稅的做法,只要初期有過統計,就可按照統計結果每年開徵相關稅額,對財政不無小補,違規的人也要付出一定成本,而不是用取消房屋稅的做法來走回頭路。
農地要農用 徐世榮:回歸《農業基本法》從全盤政策出發
政大地政系教授徐世榮也提出解方。他強調《農業基本法》必須推動,因為農地跟農業是緊密連結,現行的土地主管機關在內政部,儘管《農發條例》第十條載明要尊重農委會,但在經濟掛帥的考量下,農委會很難發揮實質影響力,所以應該由農業基本法來作為主要的改革驅動;
同時,位階更高的國發會更要扮演關鍵角色,應站在永續發展的前提下去規劃農地政策,才不會導致農地非法使用的情形屢屢發生。最後,徐世榮也強調,農業的主管機關農委會也必須在《國土計畫法》上路後,扮演好規劃、盤點及整合農地的角色,如此才能從頭解決農地不農用的問題。

至於外界關注影響農舍轉移資格的《農發條例》十八之一條修正案何時要三讀?立法委員蔡培慧則表明立場,直指問題核心應該在現有法規的執行,農民身份的查核、農業計畫的審核、農舍建照的核發,或甚至是農舍廢水的排放有沒有稽核?她強調,「這些如果都能做到,讓農舍回歸農民使用,後續農舍轉移自然不是重點。」
隨後,蔡培慧也提出三項施政建議:首先,她指出現有的農地使用狀況、面積等,應該做「全面清查」,像新竹尖石鄉有水田部落,其中的梯田就可以種水稻,但從1992年起就休耕,政府的調查應該跳脫「面積」,轉而去盤點出土地的現況,適合種植什麼作物,如此就可以給農民詳細的建議,也提高耕種的可行性。有了清查後,則該將注意力放在農村基礎設施的建設,像是「灌排分離」,因為水源是農田生產的根基,灌溉和排水分開不僅可以提升環境安全,也可減少食安的風險。
「土地儲備制絕對是政府應該思考的做法。」蔡培慧強調,除了上述政策外,政府可以考慮以市價介入買地,讓土地集中,如此一來就可以將地租給年輕人務農,或以低利率賣給農民耕作,才能解決長年農地零散的問題,讓農地真正農用,不再因為繼承或分割轉賣而喪失了農地耕作的可能性。
國發會:不會忽略農業的重要性
對於學者的建議,國發會如何站在永續發展的立場思考農業政策? 遭點名的副主委曾旭正強調,國發會的組成包含經濟發展、國土區域發展和農業發展等類別,都是站在國家整體的立場來思考問題,因此並不會光從「經濟角度」來看待農業,況且農業的產值雖低,但其具備穩定社會的功能,與社會文化、環境生態和糧食安全也息息相關,因此國發會不會忽略農業的重要性。
至於大架構下國發會如何看待農業的發展?曾旭正則強調,國發會對《農業基本法》的立法一直以來都採支持態度,因為這個法條代表了政府對於農業的根本態度,等於是「農業價值的宣示」,確立農業價值後子法修訂就會相較容易;而在這過程中,包含農水路計畫、新農再計畫和各項基礎建設的規劃等,其實都會先送交國發會審查,國發會就扮演協調者角色,並給予極大支持。
在具體做法上,曾旭正則舉例說明說,例如現有的農再計畫不再限於硬體的更新,而是將農村文化等項目納入考量,這部分牽扯到文化部的工作,國發會除了提出相應建議外,也有居中協調並促成跨部會合作。
對於農地農用如何達成?曾旭正強調,會配合現有的《國土計畫法》,首要階段就是透過盤點來確認農地現況,並在確保糧食安全的基礎上,交由農委會的專業去訂定全國農地的最低總量,最後由地方政府去逐一劃定農地,有衝突就由中央協調。
此外,新政府上台後宣誓不再出現新違章,除了即報即拆的強力手段,國發會也在思考是否要讓廠商在變更土地的過程中,提高回饋金的繳交額度,且大幅度用來鼓勵農用,如此蘿蔔和棍子齊下,盼望問題得到解決,而中央最主要的任務就是將「原則訂清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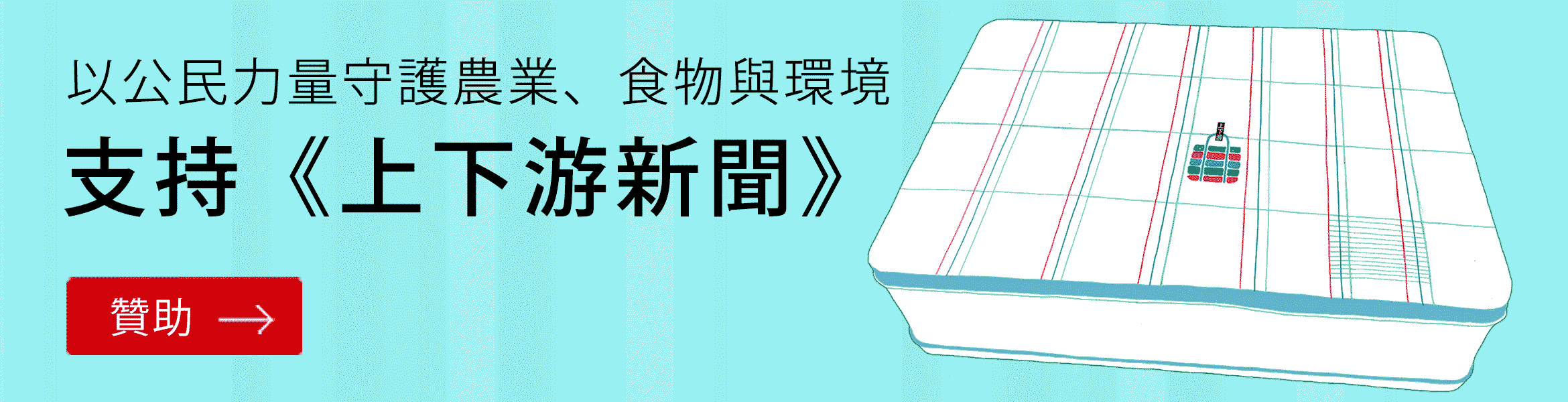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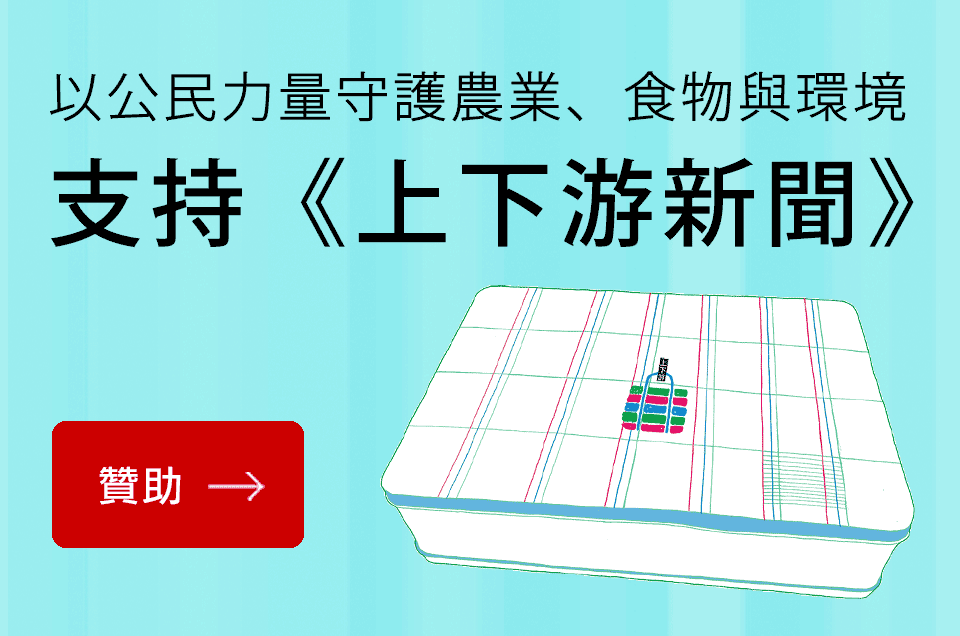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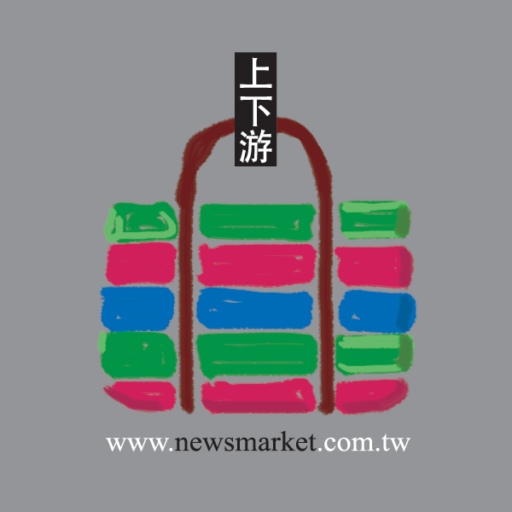


农村农民正义在哪里?
台湾农民就该被欺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