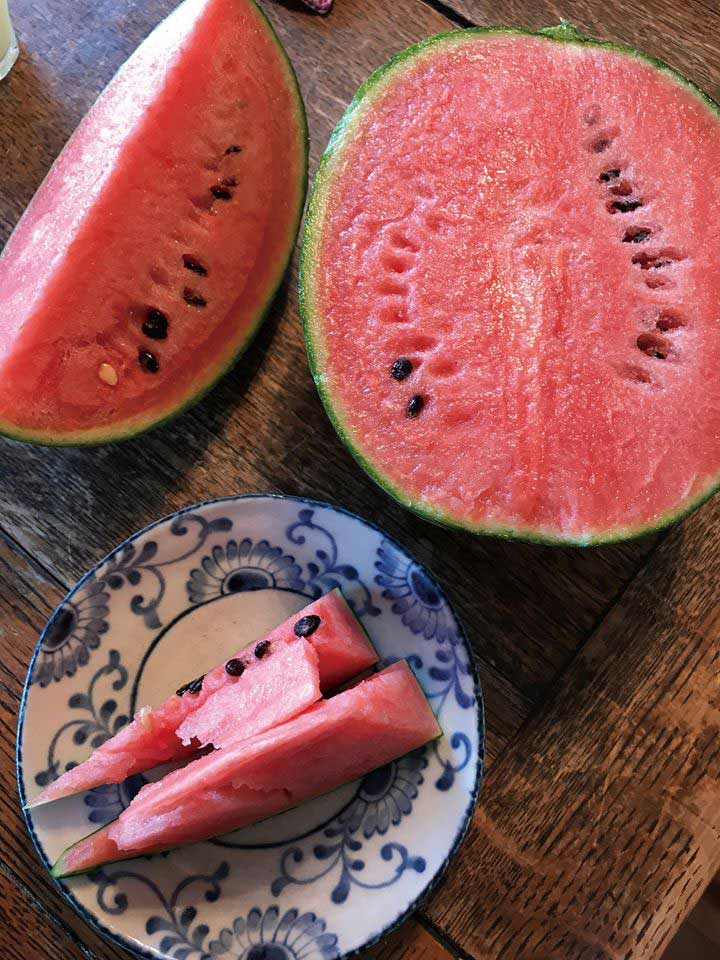熱的天,小孩子從外面流著大汗回到家,留守的姥姥或者母親,便端出冷麥茶和切好的西瓜片來。日本人吃西瓜,從來沒有砍成兩半,拿著湯匙一人吃一半的風俗;反而把大西瓜切成跟吐司差不多的片狀,邊擱鹽巴邊吃下,顯然要補充流大汗失去的鹽分礦物等。
[dropcap]記[/dropcap]得小時候夏天吃的西瓜很大很大。用雙手勉強能抱上來,而且是挺重的;倘若不小心掉下來,整個西瓜都喪命。切好後,撒了鹽巴,成功吃完紅色果肉,所剩下的白色內皮也夠厚,當年有些人還把它做成糠漬,算是「西瓜兩吃」了。
如今我常吃的西瓜是日本所謂的「小玉」。其實,用漢字該寫成「小球」才對。只是,日本人習慣用「玉」字來代替「球」字,不外是兩者諧音唸成「たま」。
早晨出現西瓜,晚上出現毛豆
「小玉」嘛,大小跟「小球」一般, 就是像排球﹑籃球﹑保齡球那樣的大小, 能夠直接放入冰箱裡的蔬果室冷卻,對生活空間並不寬裕的公寓居民來說,方便得很。至於皮呢,則薄到幾乎消失了內皮,只剩下跟一張紙一樣薄的綠色外皮而已。
今天日本商店賣的水果很多都有「糖度保證」的貼紙,買回家,吃起來一定甜蜜如點心,不必到時候要後悔自己當初沒買貴的,而是小氣鬼買了便宜的。日本有句俗話說:「安物買いの銭失い」(買便宜貨等於丟錢),就是這個意思。
五月下旬,我吃到了今年第一次的西瓜。夠甜,而且最近日本特別熱,吃了很有清熱的感覺。直到八月底以前,飯桌上,早晨出現西瓜,晚上出現毛豆,乃跟小時候一樣的夏天之味。
小時候吃西瓜,要麼在早飯和午飯之間,或者在午飯和晚飯之間,因為是當零食吃的。大熱的天,小孩子從外面流著大汗回到家,留守的姥姥或者母親,便端出冷麥茶和切好的西瓜片來。日本人吃西瓜,從來沒有砍成兩半,拿著湯匙一人吃一半的風俗;反而把大西瓜切成跟吐司差不多的片狀,邊擱鹽巴邊吃下,顯然要補充流大汗失去的鹽分礦物等。
我家老大小學一年級的暑假裡,每天上學校的游泳班,結束以後直接去校門對面的同學家,盡情吃同學母親給孩子們切的西瓜。我對那位母親心中滿是感恩,可是沒有機會見面直接表達謝意。未料不久後,他們家搬到不同的學區去了。九年以後,孩子都十五歲,要上高中了。在入學典禮上,我發現了一位面熟的新生家長。果然是那個同學的母親。我走上前開口要說的第一句話便是:謝謝您那年每天給我兒子吃西瓜。
圓圓的果實,皮兒的張力特別強
打開冰箱蔬果室,發現小玉西瓜旁邊有美如紅寶石的美國櫻桃。我至今記得高中第一次吃它時感到的震撼:多大﹑多甜﹑多紅!
太宰治有一部很有名的短篇小說叫《櫻桃》,乃在酒吧裡,媽媽桑端出來給顧客們下酒的。那是日本櫻桃,不僅很小,顏色在黃紅之間,而且吃起來味道很淡,主要是酸,幾乎嚐不到甜味的那種。儘管如此,櫻桃在日本歷來是高級的水果。小說家知道:在家餓著肚子等候的孩子們,恐怕沒吃過櫻桃,如果給他們帶回家的話,一定會很高興的。然而,他就是不肯拍屁股站起來走人,反而邊自己吃下櫻桃,邊為自己解圍說:寧願相信,大人比孩子重要。
日本人把櫻桃暱稱為「櫻坊」(さくらんぼう),好比它是個小男孩似的。小時候,我似乎沒吃過「櫻坊」,畢竟既貴又沒什麼吃頭,母親沒有理由買來叫孩子們吃。當年我唯一吃過的是,在冷飲店提供的飲料中,放著當裝飾品的瓶裝櫻桃。應該是在糖水裡煮過的吧,既軟又甜而且呈胭脂紅。
我念高中的時候,日本政府受到山姆叔叔的壓力,向美國開放了部分水果市場。市面上,忽然間既大又紅的美國櫻桃氾濫。忘了是母親買回來,還是我自己掏腰包買的,總之吃了第一口就驚呆了。圓圓的果實,皮兒的張力特別強,咬破後,滿嘴都是豐富的果汁,與其說是胭脂色,倒不如說是鮮血色。果然是肉食的美國人培植出來的水果。
後來,在美國櫻桃的壓力下,日本櫻桃也一步一步改良過來。如今,日本櫻桃的外表基本上消失了黃色,味道也不酸了。雖然還說不上胭脂紅或者特別甜,但是好歹活了過來,不至於絕滅。我覺得在那圓圓甜甜,吃了你我都變成吸血鬼的櫻桃威脅下,這已經稱得上是成就。
(本文轉載自《這一年吃些什麼好?東京家庭的四季飲食故事》,小標為本刊所加。)
【說說書】—說不定是最後一個平常年的紀錄了
文/新井一二三
[dropcap]我[/dropcap]發現,在日本人的飲食生活中,有幾個方面明確具有季節感:水果、海鮮、和菓子。
水果,我每天早晨一定吃的。海鮮,我也每週一定去中央線立川車站附設的魚力鮮魚店採購。
至於和菓子,就是因為有減肥之必要,所以平時得施行自我控制,可是到了節日就一定要嚐嚐對應的甜點,因為這屬於人文生活不可缺少而非得給下一代傳授下去的本國文化。
每月每月,我一邊寫文章,一邊叫家中老二幫我拍拍照。家人以及跟我共食午餐的同事都說過:給外國人看的書,妳選的題材都這麼平民化,可行嗎?
但是,我又不是幻想小說家,而是專門寫寫生活小事的散文家。且借用白話運動的推動者們所說的「我手寫我口」,本人都只能說「我手寫我口」了。
我本來認為:寫這時代日本人的日常飲食生活也可以。
畢竟,日常生活就是人生的主要內容。
其中,飲食的重要性,根本不需要由我這個化外之民去向華文讀者說明吧。
飲食是一種文化的具體表現。我的飲食習慣,不外是從小到現在,好幾十年來的生活經驗和思索、實踐的綜合。另一個因素就是時間,或說是生病老死。寫著關於飲食的回憶,我常常講到已故父親和姥姥,因為我喜歡吃的東西,往往是他們當初餵我的。
食物讓孩子長大。食物使生命前進持續。食物是物質,食物含營養的同時,食物也是傳達愛情的橋梁。
未料,原來以為再平常不過的一年,後來逐漸變為人類歷史上很不平常的一年了。
我二○一九年三月著手寫這本書,寫到最後一章是二○二○年二月。
在東京再相見面的時候,總編輯和我都戴著口罩了。那是在禁足令生效之前,我最後一次出外見人聚餐的一天。
後來,三月份預定的午餐會、歡送會、校友會、畢業典禮,通通都取消。
年年歲歲盛開的櫻花,今年也照樣開了,可是今年的「花見」遭禁止了。
老公當初還提議說:那麼改在家中陽台上舉行吧。
後來卻沒有,因為在這樣的全球環境裡,連愛享樂到底的老饕都不會有心思享樂的。
四月在日本是新年度的開始。可是,女兒新上的大學取消了入學典禮。等到五月,她和老大兒子都開始在家裡線上上課。
至於他們的母親,也得平生第一次從家中書房通過網路給總共兩百個學生授課。
防疫的日子裡,出外採購都受限制。可是,在這一段時間裡,家中每個成員都一定在家裡吃三頓飯,未料使伙食水平稍微提高。
對誰而言,一天三頓飯變得更加重要,這對廚子而言,算是鼓勵。無法出去跟朋友聊聊,結果家人之間說話都比平時多了。
我寫這本書的時候還以為,家庭生活嘛,一樣的故事每年都要重複下去的。然而,這一年果然變成很不平常的一年了。
我們吃的、喝的、想的、談的,雖然在一方面來說是去年的重複,可從另一方面來說,我們進入了根本沒想到的境界。
這場疫情結束以後,人類到底能回到跟原來一樣的世界嗎?
所以,我在這本書裡寫的東京家庭一年四季的飲食生活,說不定是最後一個平常年的紀錄了。明年、後年,世界到底會變得怎麼樣,真難預知。
既然如此,我們還是儘量珍惜每一天吃的每一頓飯吧。邊吃邊談已過世的長輩吧。也談談曾去過的外國城市,想再見的外國朋友吧。
記得食物不是單純的物質,食物也是愛情的化身,因為對人類來說,食物歷來都是跨越時間的橋梁。
- https://www.books.com.tw/products/E050070177?loc=P_0005_001
- 《這一年吃些什麼好?東京家庭的四季飲食故事》
- 作者:新井一二三
- 出版社:大田出版
- 出版日期:2020/07/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