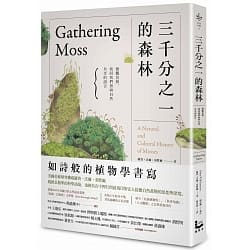一次次,植物都在被需要的時候來到。這個規律能否告訴我們苔蘚是如何被應用的呢?它們到處生長,成為日常景觀的一部分,小到讓我們渾然不覺。根據植物的語言,或許這說明了它們之於人類家戶的角色——微小而不張揚。一旦苔蘚消失不見,肯定是我們最懷念的微渺日常。
[dropcap]如[/dropcap]果每種植物都有一個角色關乎人類的生命,我們要怎麼辨別出那些角色呢?該如何讓它們發揮所長?前人留下的傳統生態知識和科學相輔相成,以口傳的方式代代相承,由一起在草地上採集的祖母傳給孫女、同在溪畔釣魚的叔叔傳給姪子、隔年會在大熊的學校裡傳給學生。但這些知識一開始怎麼出現的呢?前人怎麼知道生小孩的時候要用哪種植物?又該用哪種植物來遮蓋獵人的氣味呢?跟科學資訊一樣,必須細心又有系統的觀察自然,從無數親身經歷的實驗結果裡淬鍊出這些傳統知識。這些知識和地方環境密切相關,土地本身就是老師。植物的知識來自於觀察動物吃什麼,熊怎麼摘百合、松鼠如何輕叩楓樹。植物的知識也來自植物本身。對細心的觀察家來說,植物會自己顯露它們的天賦。
失去名字,就等同失去尊重
潔淨的郊區生活導致人們跟維繫我們生命的植物徹底割裂,植物的角色隱沒在層層行銷和科技的包裝之下,你不會聽到家樂氏麥片盒裡發出玉米葉的沙沙聲。大部分人失去了判讀環境中有哪種藥草的能力,只會讀紫錐花(Echinacea)密封瓶身上的「使用說明」。包裝成這樣,誰還認得出那些紫色花朵?甚至連它們的名字都不知道。一般人認識的植物名稱不到十二種,還包括像是「聖誕樹」這種類別。失去名字,就等同失去尊重。被記得名字,是重建連結的第一步。

我有幸能和植物一起長大,從小在野地裡打滾,手指總是沾染了小野莓的紅色。手上的籃子雖簡陋,但我喜歡收集柳枝的嫩芽,把它們浸入小溪。媽媽教我植物的名字,爸爸教我用哪種樹生火最好。當我離家上大學攻讀植物,學習的重點就改變了:植物生理學、解剖學、棲地分布、細胞生物學。我們仔細研究植物和昆蟲、真菌、野生動物的互動,但我不記得有一丁點提到人,尤其是原住民,即便我們學校就座落在奧農達加縣(Onondaga)易洛魁族聯盟(Iroquois Confederacy)的中心傳統領域。人類在這段故事裡被排除了,也許是巧合,也許是故意的,我不確定。我有個印象是,如果把人類互動也算進來的話,科學的聲望多少會受到影響。所以當吉妮找我一起策畫奧農達加部落的植物走讀,起初我不太願意,後來勉為其難承諾我只能提供生物的名字和介紹。後來我發現吉妮非常看重我帶到課堂上的科學認知方法,當然,最後我也因此教學相長。
我十分幸運,在學習路上都遇到好老師。我很感謝我的朋友兼老師,吉妮.仙納度(Jeannie Shenandoah),一位傳統的奧農達加草藥師和助產士。她總是帶著一份篤定,前進的姿態彷彿能夠覺知腳下的一切。我們因為教學成為很好的夥伴,無論我倆找到什麼植物,生物學的部分我一定知無不言,她則會跟我分享傳統草藥的用法。跟她一起散步,一邊修剪接生用的莢迷花樹皮嫩枝和要做藥膏的白楊樹芽,我開始用不同的方式認識這些樹林。求學的時候,我對植物跟其他生態系統之間的關係深深著迷,但這張連結的網從來不曾包括過我,我唯一的角色就是一個置身事外的旁觀者。我從吉妮那邊學到用山丘上的黑櫻桃榨出糖漿來治療女兒的感冒,還有用池塘旁邊蒐集的澤蘭屬植物來退燒。當我一邊採集晚餐要用的野菜食材,我又憶起兒時曾與森林建立的關係,一種有互動、互相照顧以及感恩的關係。當香氣四溢、熱騰騰又抹著奶油的野韭菜下肚之後,應該不會有人覺得學術可以跟土地脫節。
植物有自己的意志,會找到適合發揮長才的地方生存
我已經在苔蘚的世界裡打滾多年,但我明白我們之間仍然保持著一種距離:我們是在智性的層面上交集的,苔蘚教給我它們的生活,但我們的生活卻沒有讓它們參與其中。為了要真正認識,我得知道世界初始的時候,苔蘚被賦予的角色是什麼。造物主在它們耳邊說了什麼,要它們發揮什麼樣的天賦來照顧人類?我問吉妮她的族人怎麼利用苔蘚,但是她不曉得。他們不會把苔蘚當作藥草或食材。我相信苔蘚一定是這張互惠之網的一分子,但已經失去彼此間的連結好幾世代了,這樣我們該如何得知呢?吉妮告訴我,就算人們遺忘了,植物一定還記得。
傳統知識認為,一種學習植物特質的技巧是弄清楚它的來龍去脈,這跟原住民的世界觀若合符節,認為植物有自己的意志,會在需要它們的時機和場合出現,植物會自己找到適合發揮長才的地方生存。某年春天,吉妮告訴我有種新植物沿著她的樹籬石牆生長,原來毛茛和錦葵上方出現了一大叢藍色的馬鞭草,她從來不曾看過它們長在那裡。我試著解釋春天潮濕導致土壤變化,形成適合生長的環境。還記得她懷疑地揚起眉毛,但很客氣沒有糾正我。那年夏天,她的媳婦被診斷得了肝病,去向吉妮求救。馬鞭草是很好的養肝補品,且已經在樹籬上久候多時。一次次,植物都在被需要的時候來到。這個規律能否告訴我們苔蘚是如何被應用的呢?它們到處生長,成為日常景觀的一部分,小到讓我們渾然不覺。根據植物的語言,或許這說明了它們之於人類家戶的角色——微小而不張揚。一旦苔蘚消失不見,肯定是我們最懷念的微渺日常。
我問大熊和其他長輩是否知道哪些苔蘚的應用方法,結果什麼答案也沒有。現今的老人家和懂得運用苔蘚的先輩已經差了好幾代,而且受政府推動的同化運動影響太深。因為不再應用苔蘚,太多東西因此失落。身為專業的學者,我去圖書館翻遍人類學家的田野筆記想尋找古時和苔蘚的連結,閱讀陳舊的民族誌試圖拼拼湊湊,想知道我若發問,那些老人家會怎麼說。我好希望這些書頁可以像鼠尾草的煙一樣,裡面的意念可以讓人看得見。
人類學家的記錄裡 幾乎找不到一丁點苔癬的線索
我很享受採集植物的樂趣,喜歡籃子裡裝滿根葉。通常我會鎖定某一種植物為採集目標,比方接骨木的季節來臨或佛手柑因為油脂而沉甸甸。但其實閒逛本身才是最吸引人的,尤其是尋覓途中的意外發現。在圖書館裡也有類似的感覺,跟採野莓很像一書本形成的平靜原野、專注尋找的感覺,還有隱藏在灌木叢某處的知識,才是整個過程裡最珍貴的東西。
我翻遍各母語字典,想尋找是否有留下苔蘚的族語記錄。假設苔蘚是每天反覆出現的字詞,那麼它的日常應用應該也很普遍。在閱讀晦澀的學術資料時,我不只找到一個字,而是很多字來形容苔蘚,像是針對樹苔、莓蘚、岩石蘚、水裡的苔蘚、還有榿木上的苔蘚。我桌上的英文字典裡只找到一個,它把兩萬兩千個種類濃縮成唯一一類。
雖然苔蘚出現在各種棲地,不同族群賦予了它們不同名字,我卻幾乎沒有在人類學家的記錄裡找到一丁點線索。或許是角色太微渺,連存在都不值得一提。也或者,記錄報導的人對苔蘚認知不足,不知道可以問些什麼。比方說我找到蓋房子的記錄,從連排長屋到棚屋都詳盡說明建造細節,像是木板怎麼劈還有怎麼鋪設樹皮屋瓦,但幾乎沒提到用苔蘚填補木頭間的縫隙,只有在冬天的風灌進來的時候,人們才會注意到。果然,脖子後的冷風才能引起你我的關注。
苔蘚叢的隔絕功能也有助於阻擋冬天寒氣入侵。看過一份又一份的資料,我發現北邊的人以前會在冬天的靴子和連指手套裡墊一層柔軟的苔蘚作為隔絕層。當冰封了五千兩百年的「冰人」(Ice Man)在融化的蒂羅爾冰河(Tyrolean glacier)被發現時,他腳上的雪鞋裡還塞著苔蘚,包含扁枝平苔(Neckera complanata)。苔蘚為冰人的出身提供了很重要的線索,因為扁枝平蘚只會出現在低地河谷裡,位在南邊六十英里以外的距離。北方森林裡,羽苔(feather mosses)在雲杉下方長了厚厚一層,它們溫暖厚實,可以當作床鋪和枕頭。「當代植物分類學之父」林奈就提過他到芬蘭的拉普蘭地區拜訪原住民薩米人時,曾經睡在金髮苔做成的攜帶睡墊上。據說灰苔(Hypnum mosses)做成的枕頭會讓人做上特別的夢。其實Hypnum 這個屬的名稱就是在指稱這種令人出神的效果。
苔蘚用一種更直接、優雅的語言傳達它的角色
我慢慢爬梳資料,發現苔蘚被編織進籃子成為裝飾、做成燈芯還有用來刷洗碗盤。我很高興能挖掘到這些小註腳,表示人們並非對苔蘚毫無覺察,苔蘚確實在日常生活裡扮演著某些角色。但我也很失望,因為沒有一點談到造物者賜予苔蘚什麼樣的天賦,這個植物獨一無二的角色究竟是什麼。畢竟乾草也能夠當作靴子的隔絕層,松針也可以鋪成柔軟的床。我本來希望可以找到一種反應苔蘚精髓的使用方式,本來希望發現以前的人跟我一樣對苔蘚很有感覺。
泡圖書館讓我有了一點點進展,但直覺告訴我在那裡找到的故事還不夠,每種認知的方法都有它的優缺點。從書堆中喘口氣的當口,我憶起雪融時,新芽從冬天亂蓬蓬的落葉裡探出頭,跟著吉妮去找植物的經驗。我們找到的第一種開花植物是款冬(coltsfoot),長在奧農達加溪的礫石灘邊。植物學家可能會解釋它偏好三月的溪岸是因為生理機制或不耐競爭,這或許沒錯。不過,根據奧農達加族的理解,款冬長在這是因為接近能應用它的地點。哪裡有疾病,哪裡就有解方。長長的冬天冰融之後,孩子根本無法抗拒流水的魅力。他們踩水、潑水、比賽放流樹枝,把自己泡在溪流裡,渾然不覺那刺骨寒意,直到回家之後半夜咳醒。款冬茶對治療那種程度的咳嗽很夠用,那種小朋友把腳弄濕導致的咳嗽。另一個民俗植物知識的原則是我們可以藉由植物長在哪裡習得它的使用方法,比方說大家都知道哪裡有病因,附近就會有藥用植物。吉妮所言跟科學一點都不衝突。不只要問款冬如何長在溪邊,而是要問為什麼,這就跨到植物生理學無法解釋的境界。
植物的功能可以從所在的地方判讀出來。有一次我在林子裡前進時,為了爬上一個陡坡,不小心抓到有毒的長春藤,我立刻想辦法去找它的同伴。這招從不失手,鳳仙花跟毒藤一樣都長在潮濕的土裡。我用手掌壓碎它多汁的莖部,發出一聲悅耳的嘎吱聲,汁液噴濺,然後我把解藥塗了滿手。鳳仙花解了毒藤的毒,疹子也沒發作。
假設植物藉由長在哪裡來訴說它們的功用,那麼苔蘚要傳遞的訊息是什麼呢?想想它們生長的地方:沼澤、溪畔、有鮭魚跳躍的瀑布水霧區。如果這些還不足以構成清楚的信號,下雨就是嶄露天賦的時候了。苔蘚是跟著水而生的,看原本又乾又脆的苔蘚在一場雷雨之後變得飽滿盎然,它在用一種更直接、優雅的語言傳達它的角色,遠勝任何我在圖書館裡找到的資料。
苔蘚用作尿布和衛生巾,是女性手邊每天使用的工具
或許十九世紀的人類學記錄的苔蘚資訊很有限,是因為大部分觀察原住民族群的研究者都是貴族階級的男性,研究都聚焦在他們所看到的事物上,而這些人能看到什麼,則受限於他們的背景出身。他們的筆記本記錄了滿滿的男人嗜好:打獵、捕魚、製作工具。苔蘚曾經出現在武器裡頭作為魚叉頭後方的填充物,這一點就被鉅細靡遺地描述。就在我踏破鐵鞋無覓處打算放棄的時候,竟然就給我找到了!唯一一則記錄。這條敘述非常簡潔,彷彿可以看到記錄者當時臉紅了:「苔蘚普遍用作尿布和衛生巾。」
想像那一則記錄背後糾葛複雜的關係,被化約成一個簡單的句子。苔蘚最重要的使用方式,也就是反映苔蘚天賦的角色,是女性手邊每天使用的工具。這麼說,我就不驚訝為什麼這些男性民族誌學者不曾深入探究照顧嬰兒的細節,尤其是瑣碎無聊但無可避免的尿布大小事。但什麼能比寶寶的健康之於家庭的存續更重要呢?在拋棄式尿布和無菌濕紙巾當道的今日,很難想像沒有這些科技要怎麼照顧嬰兒。想像整天背著一個沒包尿布的嬰兒,那個畫面根本不忍卒睹。我很確定奶奶的奶奶一定會想出聰明的辦法,在家庭生活最根本、最重要的層面,苔蘚展現了它們的功能。這不是謙虛。寶寶被捆縛在搖籃板裡,裡頭塞滿舒適的乾苔蘚。我們知道泥炭苔(Sphagnum)可以吸收本身重量二十到四十倍之多的水分,跟幫寶適尿布的表現差不多。對當時的媽媽來說,塞滿苔蘚的育兒袋或許跟現在流行的尿布包一樣重要。乾燥泥炭苔裡頭的空氣可以吸走寶寶皮膚上的尿液,就像吸收沼澤裡的濕氣一般,它本身收斂酸性物質跟溫和殺菌的特性甚至可以預防尿布疹。像款冬一樣,濕軟的苔蘚就長在咫尺,剛好在媽媽蹲下來幫小寶寶洗澡的淺水塘邊,就出現在需要它們的地方。身為一個新千禧世代開頭的母親,我有點惋惜我的孩子從沒體驗過柔軟的苔蘚碰觸皮膚的感受,那份和世界的緊密連結,是幫寶適永遠辦不到的。
女性極擅於觀察各種苔蘚,對苔蘚質地知之甚詳
女人的生理期也跟苔蘚密不可分,很多傳統文化都把這段期間稱為「月事」。乾燥苔蘚被當作衛生巾。民族誌在這方面的描述也非常粗略,畢竟男性不太清楚經期女性在隔離小屋裡經驗到什麼。我想像這些小屋是月事同時來潮的女性聚會的地方,發生在夜空完全沒有光害的部落裡。人類學家的傳統觀念認為經期女性是不潔的,必須隔離。但這個解釋是基於人類學家對文化的臆測,而非來自部落婦女本身,她們的說法可完全不同。優克部落(Yurok)的女人形容這是一段能夠靜心冥想的時間,只有月事來潮的女性才能獲得恩准前去特別的山泉池沐浴。易洛魁族(Iroquois)的女性認為禁止女性在月事期間活動,是因為此時是女性的靈性高峰,太強的能量流動可能會影響整體能量的平衡。對某些部落來說,經期隔離是一段淨化和鍛鍊心靈的時間,跟男性在蒸汗屋的訓練有異曲同工之妙。她們的小屋裡一定塞著好幾籃精挑細選的苔蘚。必須要說,女性非常擅於觀察各種苔蘚,對苔蘚的質地知之甚詳,早在林奈之前就建構起貼身的植物分類學。虔誠的修女肯定會被這種作法給嚇得嘴歪臉斜,但我總覺得乾苔蘚變成煮過的白布,實在是少了點什麼。
我讀到另一篇民族誌記錄,是一位名叫歐娜.甘瑟(Erna Gunther)的女性寫的。裡頭充滿女性工作的觀察,尤其是準備食物。苔蘚本身不是食材,我嘗過,那種苦苦沙沙的口感會讓人打消所有讓苔蘚入菜的念頭。不過即使苔蘚不會直接被食用,也是準備食物時很重要的一部分,特別是在多雨的太平洋西北地區部落,那裡苔蘚長得特別好。哥倫比亞河(Columbia River)上游集水區的兩種主食是鮭魚和北美百合(camas, Camassia quamash)的根,兩者都因為它們餵養人類的天賦而備受尊崇,兩者也都跟苔蘚有關。
苔蘚被用以支持鮭魚和北美百合兩種主食的烹調
捕鮭魚通常需要整個家族一起協力。捕魚是男人的職責,女人負責準備用赤楊木生火來烤魚。煙燻鮭魚可以餵飽部落一整年,這個過程要小心進行以確保食物的品質跟安全。在烤魚之前,得先擦掉新鮮的魚身上一層黏黏的外皮,以除去可能的毒素,避免魚在烤乾的時候皺縮起來。古時都是用苔蘚來擦鮭魚。奇努克族(Chinook)的民族誌就曾形容女性儲放了大量的乾苔蘚在盒子和籃子裡,以確保鮭魚季來時手邊有充足的苔蘚可以用。
苔蘚也支持著西北部的另一種主食,北美百合。這是百合家族的成員之一,春天時會長出皇家藍(寶藍色)的小花,多半出現在部落精心照料的濕草地上,像是內茲珀斯部落(Nez Perce)、卡拉普亞部落(Calapooya)和尤馬蒂拉部落(Umatilla),他們燒草、除草、挖土,悉心養護成片的北美百合草原。路易斯與克拉克曾提過開花的北美百合廣袤的程度,從遠處看還以為是一片波光粼粼的藍色湖面。他們遠征通過比特魯特山(Bitterroot Mountains)時很驚險,幾乎要餓死。幸好內茲珀斯部落的原住民把冬季儲糧北美百合拿出來救濟他們,才挽回他們的性命。
北美百合的地下莖充滿澱粉也很脆口,吃起來有點像生馬鈴薯,不過通常不會生吃,而會費心製作成厚麵糊配上糖漿。它得用上烤爐來蒸烤,土窯由燒熱的岩石排成,北美百合的鱗莖被放在窯裡,上面會鋪一層濕苔蘚,讓苔蘚和北美百合層層疊疊。烤爐上鋪滿蕨類,爐子上方也有火源,可以整夜燜燒。濕苔蘚可以作為蒸氣的來源,滲入北美百合的鱗莖,把它們烤成深褐色。當烤爐打開、冷卻後,蒸熟的北美百合會被削成條狀或塊狀,方便存放。北美百合全年可食,在西部是常見的買賣,通常外層會包著苔蘚和蕨類。
北美百合在西部的部落裡依然是一種備受尊崇的儀式食物,今日還是如此。在紐約州北部的奧農達加縣,一年當中有幾個向植物表達感謝的儀典,各有其時,首先是楓樹,然後是草莓、豆類、玉米。每年十月在加州的大熊湖鎮(Big Bears)就有一場橡實的盛宴。據我所知,沒有一個特殊的儀式是獻給苔蘚的。或許禮敬這些不起眼的小小植物最好的方式,就是尋常的小小方法。溫柔盛托住小嬰兒、接住經血、為傷口止血、保暖─—我們不就是這樣在世界裡安身立命的嗎?
人們聚集起來向植物表達謝意,無論雄偉或卑微,它們都擔起了照顧人類的責任,於是我們燒菸草向植物致意。在我的文化裡,菸草是知識的傳遞者。我們要尊重通往知識的不同路徑,尊重以口頭言傳的老師、以書寫傳承的老師、藏身於植物裡的老師。是時候把念頭轉化成責任了。在這張互惠之網中,屬於我們的天賦是什麼?你我可以回報植物的又是什麼呢?
古有明訓,人類的角色是要尊重和管理。我們有責任關照植物和土地,向所有生命致敬。我們被教導過,運用植物就是在向它身處的自然表達敬意;我們使用它的方式要讓它的天賦能夠繼續滋長。神聖的鼠尾草所扮演的角色,就是讓心意能夠傳達給造物主。我們從這位老師身上學習,也要活出我們心中的敬意和感激,讓世界都看得到。
(本文轉載自《三千分之一的森林:微觀苔蘚,找回我們曾與自然共享的語言》,小標與照片為本刊編輯所加。)
- 作者:羅賓・沃爾・基默爾(Robin Wall Kimmerer)
- 譯者:賴彥如
- 出版社:漫遊者文化
- 出版日期:2020/07/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