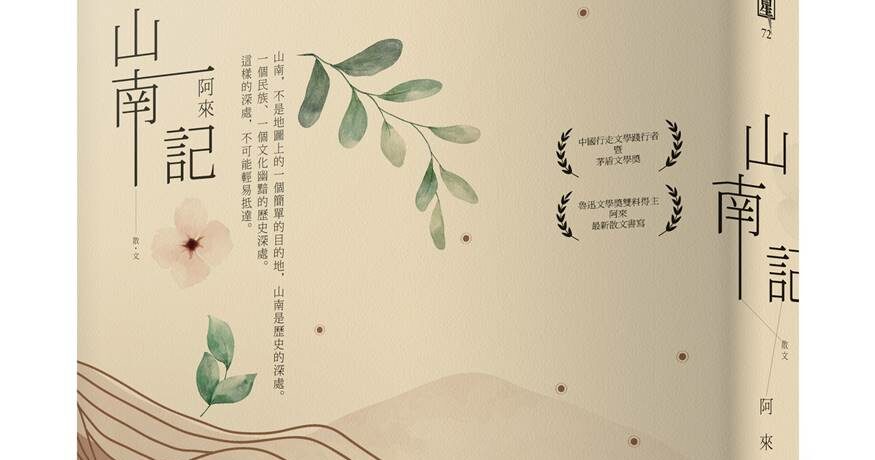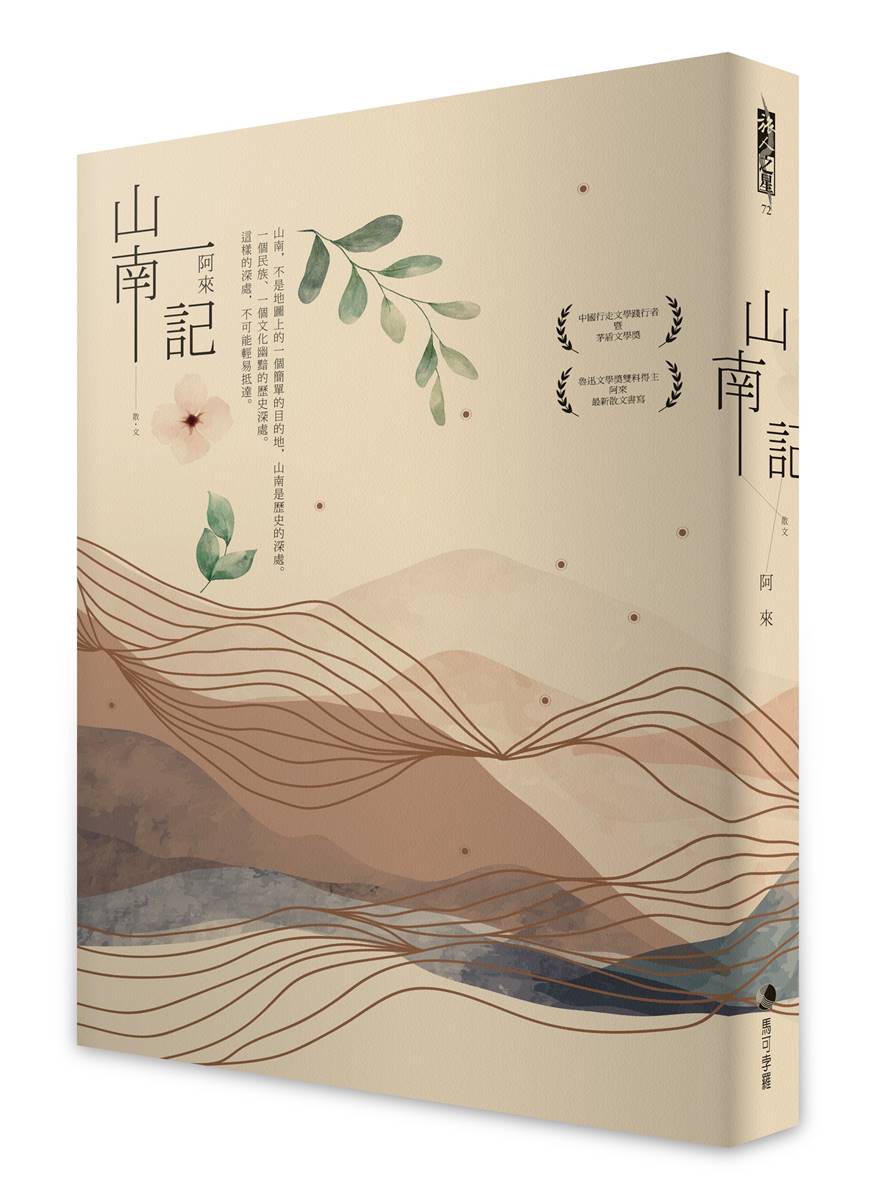1
從西寧起飛往玉樹。起得早,剛在座位上打了個盹,飛機著陸時猛一顛簸,我醒來,就聽廣播裡說:玉樹到了。
一出機艙門,就是晃得人睜不開眼的陽光。幾朵潔白得無以復加的雲團停在天邊,形狀奇異。雲後的天空比最淵闊的海還幽深蔚藍。幾列渾圓青碧的山脈逶迤著走向遼遠。這就是高曠遼遠的青藏。走遍世界,都是我最感親切與熟稔的鄉野。遼闊青藏,一年之中,即便能一百次地往返,我都永遠會感到新鮮。無論踏上高原的任何一處,無論曾多少次涉足,還是從未到過,心中都會湧起一股暖流。如果放任自己,可能會有淚水濕潤眼眶。我並不比任何人更多情,只緣這片大地於我就有這種神奇的力量。
一隻鷹在天際線上盤旋。
也許並沒有這隻鷹,我就是會「看見」。我抬頭,那隻鷹真的懸浮在天邊,隨著氣流上升或者下降,雙翅闊大,姿態舒緩。
大多數時候,我在內地別一族群的人們中生活與寫作。在他們中間,我是一個深膚色的人。從這種膚色,人們輕易地就能把我的出生地、我的族別指認出來。
現在,在機場出口,更多比我膚色還深的當地同胞手捧哈達迎了上來。我這個人,總是受不住過於直接而強烈的情感衝擊,於是迅速閃身躲到一邊,最終還是被推到迎客的酒碗面前。姑娘高亢的敬酒歌陡直而起。面前的三只小銀碗中,青稞酒晶瑩剔透,微微動盪,酒液下的銀子,折射光線,如那歌聲與情意,純淨、明亮。我深吸一口氣,讓自己平靜,同時感到,身體內部,某處,電閘合上了,情感的電流纏繞、翻捲、急速流淌,我端起酒碗的手止不住輕輕顫抖。
就這樣,我來到了玉樹。
我來到了這個在藏語的意義裡叫「遺址」的地方。
玉樹,和玉樹州府所在地結古鎮,因為一場慘烈的地震讓世界聽聞了它的名字。我也是第一次到達。我在一篇叫做〈遠望玉樹〉的小文裡寫過,「記得某個夜晚,好大的月亮,可能在幾十公里開外吧,我們乘夜趕路,從一個山口,在青藏,這通常就意謂著公路所到的最高處,遙遙看見遠處的谷地中,一個巨大的發光體,穹窿形的光往天空彌散,依我的經驗,知道那是一座城,有很多的燈光。我被告知,那就是玉樹州府結古鎮了。但我終究沒有到達那個地方。在青藏高原上,一座城鎮,就意謂著一張軟和乾淨的床、熱水澡、可口的熱飯菜,但對於一個寫作者,好多時候,這樣的城鎮恰恰是要時常規避的。因為這樣的地方常常會有與正在進行的工作無關的應酬,要進入與正在進行的工作相抵牾的話語系統。對我來講,這樣的旅行,是深入到民間,領受民間的教益,接受口傳文學豐富的滋養。但那時就想,終有一天,結束了手裡的工作,我會到達它、進入它。」
是的,我不止一次從遠處望見過這個鎮子的燈光。
從附近的稱多,從囊謙。
現在,在這個陽光強烈的早晨,我終於到達了。從機場到結古鎮的路上,一個深膚色高鼻梁的康巴漢子坐在了我身邊,我的手被有力地握住,「老師有什麼事情就告訴我們,要見什麼朋友也請告訴我們。」
這是個我不認識的人,但分明又十分熟悉。我們這個民族中的絕大多數人,僅憑身上那一點點相同的氣息,就能彼此相認相親。我說謝謝,但我不是老師。我開玩笑說,託時代進步之福,靠賣文為生,我還能養活自己,我不用兼職做家教,所以,請不要叫我老師。其實,我想說的是,當我面對自己堅韌的族群、自己的同胞,我從來都只感到自己是一個學生,雄渾廣闊的青藏高原,就是給我一千年時間來學習,也並不以為能將其精神內核洞穿。
我只說了一個名字,一個民間說唱藝人的名字。那是一個給過我幫助與教益的人,我說,我要去看望他。
2
路上,車裡,主人在介紹一些玉樹的基本資訊。提到結古鎮在藏語中的意思是「貨物集散地」。在一千多年的時光中,這個古鎮處於從甘青入藏的繁忙驛道上。這條古道有一個如今成為一個流行詞的名字——茶馬古道。也有一條漸漸被忘記的名字——麝香之路。這也是一條文化流淌與交會之路。所以,這個古鎮,曾經集散的豈止是物質形態上的商品。經過這個鎮子進入的,還有多少求法之人?經過這個鎮子走出的,還有多少渴望擴張自己視野與世界的人?
前面有著稀疏白楊樹夾峙著河岸的山谷中,一團塵霧升起來,我知道,結古鎮就要到了。真的,那些塵霧就是從正在重建的結古鎮、從整個變成了一個大工地的結古鎮升起來的。
我們就進入了那團塵煙。高原的空氣那麼透明,身在塵煙之中而塵煙竟消失不見。工地總是這樣,浮土深印滿車轍。各種機械轟鳴著來來往往。節節升高中的,已顯示出大致輪廓的半成的建築上人影錯動、旗幟飄揚。未來的學校,未來的醫院,未來的行政區,未來的商廈,未來的住宅,我們穿行其間。沒有地震廢墟,只有漸漸成形的建築在生長。這裡是青海,我想起了成就於青海也終了於青海的詩人昌耀的詩句:
鋼管。看到一個男子攀緣而上
將一根鋼管銜接在榫頭。看見一個女子
沿著鋼管攀緣而上,將一根鋼管銜接到另一根榫頭。
他們堅定地將大地的觸角一節一節引向高空。
高處是晴嵐。是白熾的雲朵。是飄搖的天。
那是詩人寫於二十世紀那令人鼓舞的八O年代的詩。現在,卻似乎正好描摹著眼前的情景。就是這樣,被強烈地震夷為平地的古鎮正在生長,飄搖的天讓人微微暈眩。
那個挖掘機手,輕輕一按手裡的操縱桿,巨大的挖斗就深掘地面。那個開混凝土罐車的司機,不耐路上車流的壅堵,按響了聲量巨大的喇叭。喇叭聲把路口那個疏導壅堵車流的年輕交警的呼喊聲淹沒了。
這樣的情形令我感動。
工地的間隙裡是板房中的小店、飯館。四川漢族人的飯館,青海藏族人的飯館,撒拉人的清真飯館。肉店、蔬菜店、電器店、旅館。生活還在繼續,熱氣騰騰。不像我去過的別的災區,浩劫之後有一種哭訴的情調。馳名整個藏區的嘉那石經城在地震中傾圮了,但虔城的信眾們並不以為那些刻在石頭上的六字真言、那些祈禱文、那些整部整部經卷的功德與法力會因此而稍有減損,人們依然手持念珠繞著石經城轉圈、祈禱,為自己,為他人,也為整個世界。
我也因這樣的情形而感動。
當然也聽到好多生命毀傷、家破人亡的故事。但人們只是平靜地述說,就像在述說遙遠的故事,就像這些故事不是親歷,而只是聽聞、是轉述。活脫脫就是流行在青藏高原上那些口傳故事的風格。講這些故事的,有失去了不止一位親人的人,有失去了自己剛建成不久的頗具規模酒店的人,有震中受重傷、身上的一些關節被替換成合金構件、回到工作崗位就服務於眾人的人。還有,一位一定要在震後的玉樹辦起一份文學雜誌的朋友。我沒有看見有人流下過半滴眼淚。反而,我看到很多的平靜與微笑。我喜歡這種平靜中的達觀。
高原上難得的溫暖季節依然如期而至,草地碧綠,百花盛開。我四處走動,看到人們依然按照習慣,在靠近漫漶流水的草地上搭起帳篷,外出野餐。當我在附近的小山上把鏡頭對準一叢叢點地梅細密的小花時,從河谷中的野餐地,有悠遠的歌聲傳來。歌聲在谷地中升上來,達到與我平齊的高度,稍作盤桓,又繼續上升、上升,升到了比後身側的岩石峰頂更高的天上。我趴在馨香的草叢中,用鏡頭對準細碎的花朵,取景框中,焦距始終模糊不清。扶搖而上的歌,調子與詞句我都非常熟悉,但那一刻,我卻因為心頭湧起的熱流而淚光閃爍。
一位年輕的活佛,定要請我到他家裡做客。他讓我坐在比他高的座位上,親手為我沏茶,然後,打開電腦聽他新寫的歌。他說,他要寫出一種歌,採用流行的方式,但不是一般的情愛表達,而是有宗教感的,要有對於生命和對宗教的本質感悟與思考。也許,他的歌與他的追求間尚有距離,但我想,催生他想法的這些因緣,同樣也將是我從這塊土地上領受的深厚教益。能有機會在這樣一塊土地上,沉潛於自己的族群和文化之中,做一個學生,並不斷收穫新知識新感受,是上天對我的厚愛。
3
就在那天上午,穿過喧騰的工地,穿過那些勞作的人群,穿過被陽光照得閃閃發光的塵土,一幢三層樓房出現在眼前。汶川地震後,我去過許多被瞬間的災變損毀的地方,因此熟悉建築物上那些猙獰的裂紋,知道是怎樣的力量使這座建築在一樓和三樓保持住基本輪廓的情況下,之間的二層如何幾乎消失不見。我們被告知,這是整個結古鎮將唯一保留的地震遺跡。我還進一步知道,震前,這座建築是一家以偉大的史詩主人公格薩爾命名的賓館。格薩爾史詩是屬於全體藏族人的偉大精神遺產,更是康巴人的英雄——他出生在康巴,建功立業也多在康巴大地。在康巴人的心中,英雄受到加倍的崇仰。所以,我推測,這座以格薩爾命名的建築做為紀念物得以保留,不僅僅是因為這座建築所留下的地震毀壞力的駭人印跡。
幾年前,我曾在這座城鎮四周的草原上搜集英雄的故事。就在那時,我就聽人們不止一次提起這個鎮子上的格薩爾廣場。不止一次,有人向我描述那個廣場中央塑造的威武的格薩爾塑像。我也在想像中不止一次來到那尊塑像面前。我甚至把這個廣場與塑像寫進了我的也叫《格薩爾王》的長篇小說。我尋訪英雄故事的時候,沒有到達結古鎮。但我小說中,那個追尋英雄足跡的說唱人晉美到達過這個廣場。
在這裡,說唱人晉美與要跟他學習民間音樂的年輕歌手分了手。
「他們又到達另一個號稱是曾經的嶺國的自治州了。
「他們從山坡上下來,貼地的風從背後推動著,使他們長途跋涉後依然腳步輕快。地上的風向北吹,天上的薄雲卻輕盈地向東飄動。這個城市的廣場很寬闊,兩個人坐在廣場上英雄塑像基座前的噴泉邊,看人來車往。年輕人說:老師,我們該分手了。他還要給他一些錢。晉美拒絕了。他的內心像廣場一樣空曠。身後,噴泉嘩然一聲升起來,又嘩然一聲落回去。他說:調子是為了配合故事的,為什麼你只要調子,不要故事……
「年輕人彈著琴歌唱。他唱的是愛情,他看見年輕人眼中有了憂鬱的色彩。開始他只是試著低聲吟唱,後來,琴聲激越起來,是他教給他的調子,又不是他教給的調子。這使他內心比廣場更加空曠。
「……晉美起身了,歌手一旦開始歌唱,就無法停止。歌手用眼光送著他,那眼光跟歌唱的愛情是一致的,無可如何,但又深情眷戀。當整個廣場和人群都在晉美背後的時候,他流淚了。」
在相當大的程度上,我也是一個說唱人。我不自視高貴。這個世界從來就是權力與物質財富至上,在當今時代,這一切更是變本加厲。但我堅持相信,無論是一個國,還是一個族,並不是權力與財富的延續與繼承,而是因為文化,那些真正做為人在生活的人,由他們所創造與文化所傳承的文化。我以為自己的肉身中,一定也寄居著說唱人的靈魂。我不自認高貴,但我認為可以因此從權力與財富那裡奪回一點驕傲。
現在,我來到了這個廣場。我早已從地震剛剛發生時那些關於玉樹的密集的電視新聞中,知道了所謂噴泉是出自我的想像。但那座英雄雕塑一如我的想像。這個形象在那些古老唐卡中我曾多次遇見。但在這裡,這個形象變得如此立體,堅實的基座上,那黝黑的金屬鑄成的人與馬,與兵器與盔甲如此渾然一體,威武莊嚴。
那麼猛烈的地震,沒有對這座塑像有絲毫的動搖與損傷。我當然要為此獻上一條哈達,和我內心一些沉默的祝禱。我當然很高興和當地的同胞一起在塑像前合影留念。格薩爾的英姿高高地矗立在我們身後,背後,是深遠的藍空和潔白的流雲。做過一個夢,在拜讀一位喇嘛詩人的詩句,驚奇他突然擺脫了那些陳腐的修辭,把流雲比作精神的遺韻與情感的馨香。(本文摘錄自《山南記》)
作者簡介:
阿來,中國當代藏族作家,一九五九年出生於四川西北部阿壩藏區的馬爾康縣,俗稱「四土」,即四個土司統轄之地。畢業於馬爾康師範學院。曾任成都《科幻世界》雜誌社社長、總編輯等。主要作品有詩集《棱磨河》,小說集《舊年的血跡》、《月光下的銀匠》,長篇散文《大地的階梯》、《就這樣目益豐盈》,長篇小說《塵埃落定》、《空山》、《格薩爾王》。第一部長篇小說《塵埃落定》獲第五屆茅盾文學獎,成為該獎項有史以來最年輕得獎者及首位得獎藏族作家;《蘑菇圈》獲得第七屆魯迅文學獎中篇小說獎,《空山》獲第七屆華語文學年度作家大獎等。多部作品在國外翻譯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