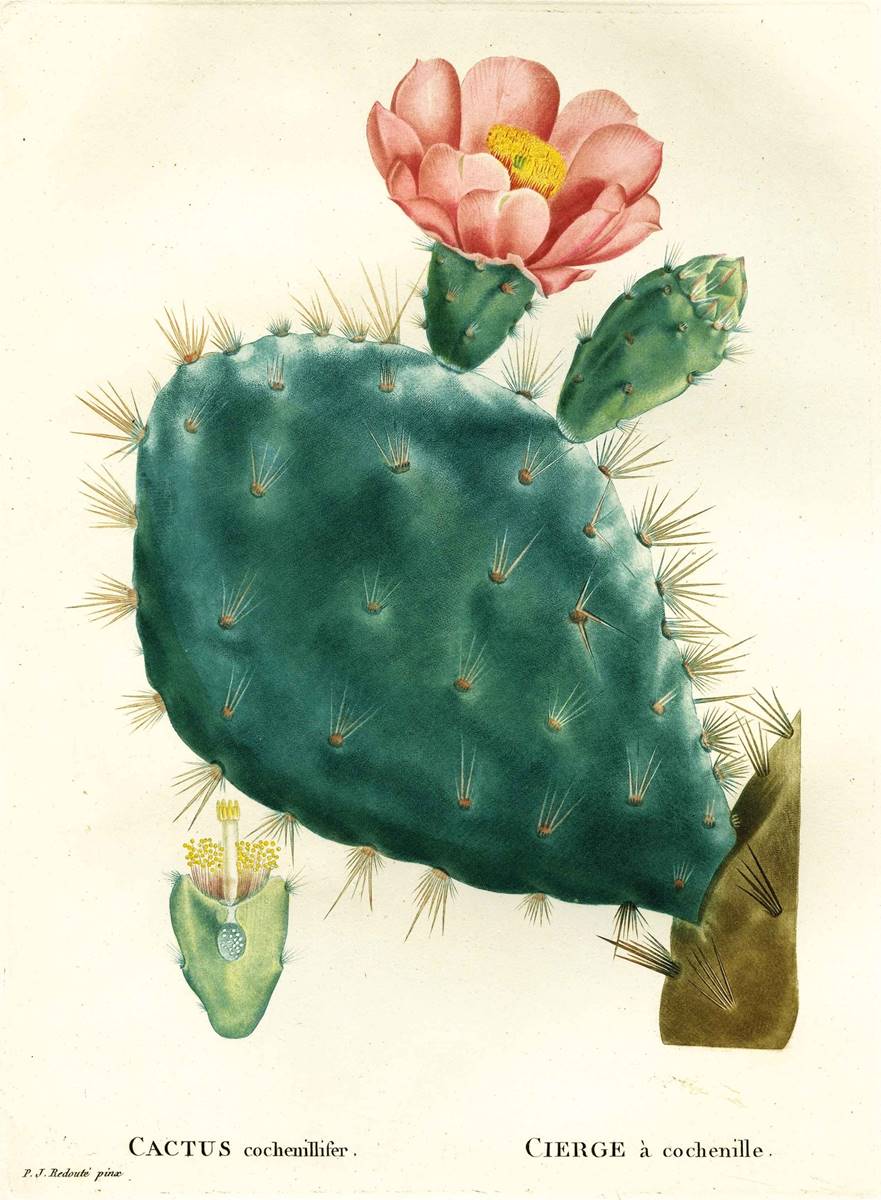「他竟然能夠登上喜馬拉雅山、發現一些植物,並且在不到十八個月的時間裡,以近乎舉世無雙的華麗插圖在英國發表這些植物,這真是這個時代的一大奇蹟。」
與貴族的關聯
到了十九世紀中葉,就如同歐洲的其他植物園,英國皇家植物園邱園已成為一個龐大網絡的中心,將英國在商業和科學上的期望跟殖民地的植物資源聯繫起來。邱園關注的一大重點是新物種的發掘,而這伴隨著學名的命名權——植物名稱可用來紀念、貶抑或奉承他人,儘管林奈曾發出警告:「不應濫用植物的命名來博取他人歡心、紀念聖徒或其他領域的名人。」
一七八八年,約瑟夫.班克斯(Joseph Banks)正式為天堂鳥取了學名「Strelitzia reginae」,以紀念身為邱園贊助人的英王喬治三世王后夏洛特(Charlotte of Mecklenburg-Strelitz),她出身自神聖羅馬帝國轄下的梅克倫堡─施特雷利茨公國。將近五十年後,負責管理加爾各答皇家植物園(Royal Botanic Garden, Calcutta)的丹麥植物學家納撒尼爾.沃爾夫.瓦利克(Nathaniel Wolff Wallich)將俗稱「緬甸之光」的瓔珞木命名為「Amherstia nobilis」,以「紀念尊貴的伯爵夫人阿默斯特(此指莎拉.阿默斯特〔Sarah Amherst〕)與她的女兒莎拉.阿默斯特(母女同名)。這兩位女性對於自然史學,尤其是植物學的各個領域都非常熱衷,亦長期推動相關發展。」
天堂鳥在獲得學名前就已經種植在邱園裡了,這種植物具有直立、類似香蕉的葉片,它的花序「有著六朵或八朵花,在綻放時朝上豎立,形成冠冕狀,呈現耀眼的橙色,蜜管則為純淨的湛藍色,令人驚豔」。這種稀有而引人注目的植物不僅與英國殖民地息息相關,也與王室有所關聯,成為了一種代表性植物,象徵著班克斯對植物園的雄心壯志。此外,栽培天堂鳥並不容易,因而為充滿抱負的眾多園藝家帶來挑戰。
一七九一年,柯蒂斯在《植物學雜誌》(Botanical Magazine)發表了第一幅手工上色的摺頁雕版畫,主角正是天堂鳥。對此,他如此解釋:「為了讓讀者有機會欣賞引入我國的這種難得一見、絢麗非凡的植物之彩色圖像,本期決定在插圖的相關設計上破例。」不過,他對讀者的反應仍有所顧慮: 「我們不免擔心,有讀者可能無法完全滿意。若真如此,我們希望這些讀者能夠放心,未來極少會出現這類破例,除非是遇到格外美麗或奇異的植物。」事實上,這種做法過了十三年才再次出現。
一九九〇年代,天堂鳥就像從前那樣,再度跟重要人士產生關係;當時,有人在非洲發現一個罕見的天堂鳥黃花變種,起初取名為「科斯滕布希黃金」(Kirstenbosch Gold)[1],後來更名為「曼德拉黃金」(Mandela Gold),以紀念南非政治家尼爾森.曼德拉(Nelson Mandela)。但出於「優先權原則」(Priority of Names),非洲以外的地區沿用了較早的名稱。
一八二六年,瓦利克收到一些「緬甸之光」瓔珞木的乾燥標本,這些植物來自一座緬甸寺廟的花園,採集者是一位姓克勞福德(Crawford)的先生,他形容這種樹木「實在太美,即使是那些對植物學一無所知也無法忽視」,這促使瓦利克進一步尋找更多樣本。一年後,瓦利克在另一座緬甸寺廟的花園裡發現了兩棵約十二公尺(四十英尺)高的瓔珞木,「樹上掛滿了下垂的總狀花序(raceme),開著朱紅色的大花,形成極為壯觀的景象,在東印度的植物中無與倫比。而且我認為,世界上任何一個地方都沒有植物能超越它的壯麗優雅。」印度藝術家維什努佩索(Vishnupersaud)是與瓦利克同行的「畫師」(draughtsman),瓦利克雇用他來「比對與修正」那些依照稍早收到的標本所繪製的畫作。維什努佩索的瓔珞木插圖出版後,激發了英國園藝人員的收集欲與競爭心。
瓦利克將瓔珞木引種到加爾各答,但未能將活體植株送回英國。一八三九年,第六代德文郡公爵威廉.喬治.斯賓塞.卡文迪什(William George Spencer Cavendish, 6th Duke of Devonshire)成為首位在英國成功栽培瓔珞木的人,而他與園藝師約瑟夫.帕克斯頓(Joseph Paxton)攜手合作,在德比郡的查茨沃斯莊園(Chatsworth House, Derbyshire)培育了各種稀有的異國植物,那裡是當時歐洲栽培這類植物最重要的其中一個據點。然而,英國園藝家路易莎.勞倫斯(Louisa Lawrence)在她丈夫於倫敦西部擁有的伊靈公園(Ealing Park)成功讓瓔珞木更早開花,搶先了卡文迪什一步。勞倫斯是在一八四七年從印度總督亨利.哈定(Henry Hardinge)那兒取得瓔珞木,兩年後就讓它開出花朵。勞倫斯更進一步,將一根生著花朵的瓔珞木總狀花序送給維多利亞女王,另一根則送給邱園園長威廉.傑克森.胡克,而一幅「地圖集大開本(atlas-folio)的畫作」也在邱園誕生:「唯有這種尺寸才能將這樣的主題表現得淋漓盡致」。一八四二年,已擔任邱園園長一年的胡克將《柯蒂斯植物學雜誌》(Curtis’s Botanical Magazine)的其中一卷獻給勞倫斯:「她的花園和遊賞區之美,以及她成功培育出的珍貴植物都令人驚嘆,更難得的是她的慷慨,將這一切開放給所有對植物學和園藝學感興趣的人參觀。」雖然一八六五年以來,就再也沒有瓔珞木在野外生長的相關記載,瓔珞木至今在潮溼的熱帶地區依然是一種園藝奇觀。
一八四九年,卡文迪什和帕克斯頓稍稍扳回一城,首度讓巨大的亞馬遜王蓮(Victoria amazonica;異名為Victoria regia)開出花朵,這又是一種為了討好英國君王而命名的壯麗植物。胡克一八四七年曾在《柯蒂斯植物學雜誌》(Curtis’s Botanical Magazine)上發表四幅手工上色的版畫,並詳述這種植物的發現過程來吸引讀者的注意。水晶宮(Crystal Palace)與邱園「棕櫚室」(Palm House)等溫室結構的設計靈感都來自亞馬遜王蓮的葉脈形式——水晶宮是為了一八五一年的萬國工業博覽會(The Great Exhibition)打造的溫室。
展望東方
幾千年來,貴重的香料、香水和紡織品紛紛從東方貿易路線輸入歐洲,地中海地區以外的風土人情和奇聞軼事也隨之傳入。然而,很少有活體植物從這些貿易路線進入歐洲,因此植物產品的來源有時籠罩在謎團之中。比方說,一直到十九世紀,有喝茶習慣的歐洲人都未意識到紅茶和綠茶其實來自同一種植物。
不過,原產於東亞的柑橘屬植物確實沿著貿易路線且隨著殖民活動慢慢傳播到世界各地。*59根據日本古墳時代(約西元三〇〇至五三八年)的傳說,垂仁天皇曾派遣一位叫田道間守的人去尋找長生不老的靈藥,那是一顆「永遠芳香的果實」,推測就是中國的橘子。到了十七世紀,柔軟的柑橘在歐洲非常流行,「我們因它美麗的常綠葉片和芬芳的花朵而受益;但在我們寒冷的國土上,它的果實始終不會成熟。」除了夏季的幾個月,柑橘幾乎全年都需要保護才不會死去。名為「橘園」(orangery)的建築物應運而生,專門用來培育這些嬌嫩的植物——由於君主擁有用之不竭的財富和人力,有些橘園的規模相當宏大,例如位於凡爾賽宮(Château de Versailles)的橘園。並不令人意外的是,柑橘屬植物也受到植物繪師的歡迎,其中有位繪師為義大利植物學家喬瓦尼.巴蒂斯塔.法拉利的《赫斯珀里得斯:金蘋果的栽培與用途》(Hesperides sive de malorum aureorum cultura et usu, 1646)製作了八十幅金屬版畫。
對於一些有錢有閒的歐洲園藝師來說,東亞在園藝領域提供了各種新奇的可能。那些由東方統治者栽培的華麗花園,相關的記述與插圖加深了西方人印象中的東方異國情調。來自西方的旅人雖然只能在中國和日本的沿海貿易據點採集植物,但他們仍面臨各種危險,甚至必須使出詭計來因應,這些故事卻反而助長了歐洲人對東方的強烈渴念。
中國北京的圓明園是東亞最壯觀的花園之一,它是清朝乾隆皇帝和後來歷任皇帝的主要居所,宛如一個鍍金的籠子。一七四三年,在圓明園開始動工的二十多年後,法國耶穌會傳教士王致誠(Jean Denis Attiret)熱情洋溢地描寫了圓明園的宮殿、花園與水源充足的樹林景觀。此外,中式風格和東亞的藝術傳統讓歐洲列強深深著迷。在英國,邱園的大寶塔(Great Pagoda)是現存最著名的人造中式花園,該塔建於一七六一年,由瑞典裔蘇格蘭建築師威廉.錢伯斯(William Chambers)設計。有趣的是,同樣是「中式風格的植物」成功在歐洲花園中保持地位,包括來自中國和日本的野生與栽培植物,有醉魚草、山茶花、栒子、連翹、波羅花 、茉莉、棣棠花、百合、木蘭花、楓樹、芍藥、杜鵑花、繡線菊、桂花、莢蒾、紫藤和金縷梅等。
有些植物對十八世紀晚期的園丁並不陌生,杜鵑花就是一例。然而,有些植物原本是從北美和歐洲大陸引進,十九世紀時卻被來自喜馬拉雅山脈和中國的物種大量取代。一八四九年十一月,以約瑟夫.道爾頓.胡克為首的團隊在尼泊爾東北部花了兩天採到「二十四種」杜鵑花的種子,這些種子隨後被引入英國的花園。一八四九至五一年,胡克的父親威廉.傑克森.胡克編輯了《錫金喜馬拉雅地區杜鵑花》(The Rhododendrons of Sikkim-Himalaya)一書,內容包括沃爾特.胡德.菲奇(Walter Hood Fitch)繪製的三十幅手工上色石版畫,以「帝國大開本」(imperial folio)[4]尺寸呈現。威廉.傑克森.胡克花了一些心思,確保讀者認知到「這些畫作和記述都是實地完成的」,出自他兒子約瑟夫.道爾頓.胡克之手。有人熱情洋溢地評論胡克父子的作品:「他竟然能夠登上喜馬拉雅山、發現一些植物,並且在不到十八個月的時間裡,以近乎舉世無雙的華麗插圖在英國發表這些植物,這真是這個時代的一大奇蹟。」
不過,許多在植物原產地工作的採集者不太關心如何在野外好好作畫,他們更在乎的是將活體植物帶回歐洲。因此,西方世界對於這些新奇的園藝植物,通常都是根據在歐洲栽培而非在棲地生長的植株來作畫。
其中一位最早前往東方的歐洲博物學家是耶穌會傳教士卜彌格(Michał Piotr Boym),他出身自波蘭富商家庭,一六四三年取道葡屬果阿(Portuguese Goa)前往中國西南部。他在一六五二年返回歐洲,從此捲入天主教會、歐洲君主與中國皇帝之間的複雜政治關係裡。一六五六年,卜彌格最後一次啟程前往中國,他的《中華植物誌》(Flora Sinensis)同年在維也納出版。該書收錄二十三幅品質粗糙、附有拉丁文和中文名稱的蝕刻版畫,而這部有著「誇大的書名」的作品,主要記述的是一些果樹——如巴西腰果、番石榴、鳳梨和印度芒果——它們可能來自十七世紀初的印度或中國的花園。沒有證據顯示卜彌格將中國植物引入歐洲,但一些十八世紀的耶穌會傳教士確實從中國的花園帶回了珍貴的植物。例如,湯執中(Pierre Nicolas Le Chéron d’Incarville)引進了大花紫薇和臭椿等為人熟知的樹種。
一八三九年,中英雙方爆發了鴉片戰爭,導火線是中國皇帝反對英國商人進口鴉片。中國在一九四二年戰敗後簽署《南京條約》,除了將香港島割讓給英國,也在原本的廣州口岸外再開放四個新的通商口岸。倫敦園藝學會認為這樣一來,便有望「採集尚未在英國栽培的觀賞性或實用植物的種子和植株」,於是雇用蘇格蘭植物學家羅伯特.福鈞(Robert Fortune)前往中國探險。學會成員希望為自己的花園蒐集一些植物,像是「栽培在御花園裡的北京桃子」、「能生產不同品質茶葉的植物」、「名為『香櫞』的佛手柑」、「正宗的中國橘子」與「木本與草本的牡丹」。由於「華德箱」(Wardian case)改良了活體植物的長途運輸技術,即使學會挹注的資金少得可憐,福鈞仍成功為英國引入一些如今大家已很熟悉的植物,例如冬季開花的金銀花、迎春花和綠梗連翹。在一八六一年以前,除了短暫返回英國幾次,福鈞幾乎一直都受雇在中國採集植物,同時也私自輸出茶樹,並將製茶工藝的知識傳播出去。
本身是傳教士的法國博物學家譚衛道(Armand David)曾率隊前往中國探險,最終發現數十種新的杜鵑花和報春花,很多後來都出現在歐洲的花園。其中,譚衛道跟兩種植物的關係最密切,它們是他一八六九年在中國西南部發現的大葉醉魚草(Buddleia davidii)和珙桐(Davidia involucrata),這兩種植物的學名正是以他命名。大葉醉魚草和珙桐被引進歐洲的過程,則牽涉到十九世紀末兩個知名園藝世家的競爭:法國的維爾莫漢家族(Vilmorin)與英國的維奇家族(Veitch)。維奇父子園藝公司(James Veitch & Sons)曾資助恩內斯特.亨利.威爾森(Ernest Henry Wilson)去中國採集植物——這位探險家有著「華人」(Chinese)的綽號——目標就是取得這些園藝珍品的種子。(本文轉載自《妝花:世界植物插畫演進史的藝術之美與科學思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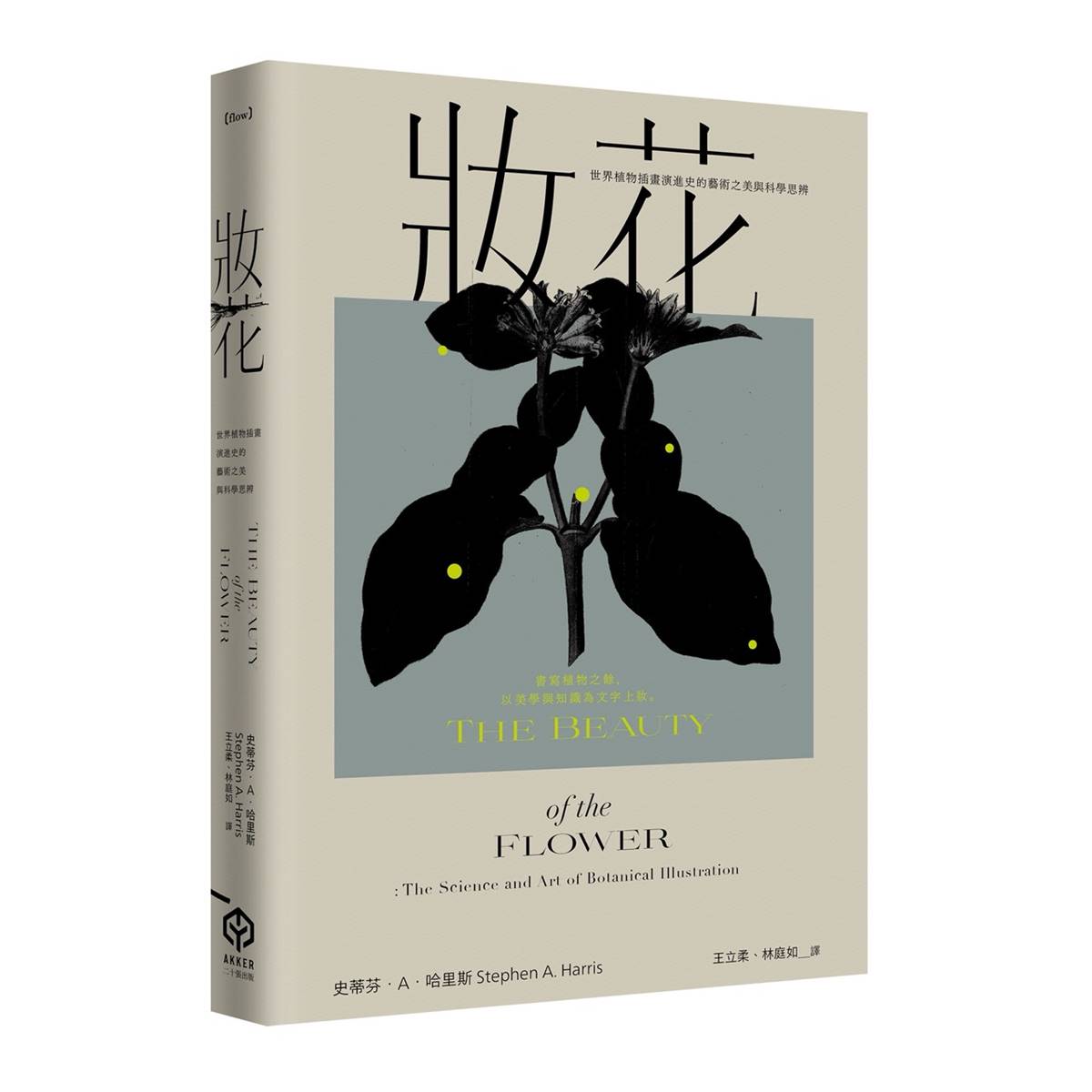
妝花:世界植物插畫演進史的藝術之美與科學思辨
作者: 史蒂芬.A.哈里斯(Stephen A. Harris)
譯者:王立柔、林庭如
出版社:二十張出版
出版日期:2025/05/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