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有人類的園子,或是路旁、垃圾堆,相形之下是「開放」的生存環境,新的雜交品種會有更好的機會;而且假如它湊巧符合人類所好,或滿足某種人類欲望,就能立穩腳跟,找到路進軍世界。
依我看來,大自然當中,少有景象能跟看到一畦畦蔬菜苗像綠色城市般由春天的土地冒出一樣令人激動的了。我鍾愛新綠植物與翻耕黑土彷彿數位訊號○與一那樣規律交替,以及田界分明的泥土所呈現的幾何秩序,那就是五月的菜園——在病蟲害出現之前、在過分繁茂之前、在夏日雜亂得叫人畏縮之前的菜地。曠野有其崇高性質,以及,歌頌田園的美國詩人軍團,天曉得有多少。但我在此打算為有序大地帶來的滿足感說些話。假如聽起來不會太像矛盾修辭,我想把這樣的土地稱作「農藝式崇高」。
但實際上,這個詞可能就是這麼矛盾。說到崇高的體驗,內容都是大自然對我們造成的影響,也就是我們對她的威力心生敬畏——覺得自己如此渺小。我要談的正好相反,我無法否認自己想談的主題有點啟人疑竇,那便是對大自然施力之後的滿足感,亦即瞧見自己投注在大地上的心血開花結果的快樂。正如尼加拉瓜大瀑布和聖母峰會激起第一種澎湃感受,農夫在山坡上修建的整齊農場,或是凡爾賽宮園林裡那種修剪得整整齊齊、排列成行的樹也會激起第二種澎湃感受,讓我們充滿力量感。
如今,崇高大多成了某種輕鬆寫意的「度假」,不論就字面意義或道德意義皆然。畢竟,誰還會說荒野的壞話?而相形之下,這另一種澎湃感受,即人類想控制大自然荒野的渴望,卻曖昧得叫人生氣。我們不確定自己在自然中有何等力量,也不知這力量是否正當、真實,而這種懷疑是應該的。或許農夫或園丁比大多數人更清楚自己的控制始終是種假象,端賴運氣、天氣等更多超出他掌控的事物。只有暫時擱下懷疑,農夫才能在每年春天再度耕種,在春季的一切不穩定性中跋涉。過不了多久,害蟲就來了,還有風暴、旱災和枯萎病,彷彿在提醒農人園丁,這些新種下的莊稼顯示出的人為力量,事實上是何等不完善。
一九九九年,一場怪物級十二月風暴,威力比任何歐洲人記憶所及的風暴還要強大,把凡爾賽宮園林裡那片由造園師安德烈.勒諾特爾(André Lenôtre)在數世紀前種下的樹木颳得一片狼藉,幾秒內就壓皺了這座園林完美的幾何圖形——那些圖形可能是我們曾有過最強力的人類宰制意象。當我看到那些殘破的林蔭道照片,筆直線條被亂扒、油畫般的景觀遭毀,不禁想到,園林若不是被精心修整得如此井然有序,或許更能好好承受風暴的狂怒,過後更能自我修補?所以,我們能由這樣的災難學到什麼教訓?要看情況而定,看看到底是像一般人那樣將這場特大風暴視為某種直接、簡單的證據,證明我們不知天高地厚,而大自然的威力無限優越,還是像某些科學家現在的看法,將之視為全球暖化的效應,大氣愈發不穩定。以這個角度看,這場風暴就跟風暴摧毀的林木秩序一樣,都是出於人造,是人類力量推翻另一種人類力量的體現。
這種令人哭笑不得的事,園丁習以為常,他們終究看出了,每當自己對園子的控制出現進展,就會同時邀來新的混亂無序。荒野可以減少,一畝接一畝,但野性卻是另一回事。新翻的泥土會讓新野草冒出,強力新殺蟲劑會讓害蟲產生新抵抗力,植栽愈朝簡化的方向跨一步,例如採用「單作栽培」(monoculture)或種植基因相同的植物,就愈容易導致料想不及的新複雜狀況。
只是簡化的威力之強,實在不容否認。這類做法「很管用」,能讓我們從自然取得想要的東西。農業就其特定本質而言,是殘酷地簡化,把自然界難以理解的複雜簡化成人類能夠管理的東西。畢竟,農業始於一個簡單行為——驅逐一切,只留一小撮中意的物種。把作物種成清晰明瞭的一列列,不僅可以滿足我們的秩序感,而且很明智,接下來的除草及收成就簡單多了。所以儘管大自然本身從不把植物種成一排排,或種成花壇、林蔭道,但當我們這麼做,她也不見得會抱怨。
事實上,很多新事件都發生在園子裡。在人類意圖控制自然之後,大自然原本未曾有的新多新奇事物出現了,包括可食的馬鈴薯(野生馬鈴薯又苦又有毒性,無法下嚥)、重瓣鬱金香、精育無籽大麻、油桃等,不一而足。每一案例中,大自然都提供必要的基因或突變,但是,若是沒有園子和園丁來開闢空間,這些新奇事物永遠也不見天日。
對於大自然及人類而言,園子向來是實驗室,可在裡面嘗試新的雜交與突變。野生狀態中絕不會交配的物種,在人類清空的土地卻能自由雜交。在發展完整的草原或森林生態系交織嚴密的脈絡中,新奇的雜交品種很難找到立足之地,可能每個棲位都被占滿了。唯有人類的園子,或是路旁、垃圾堆,相形之下是「開放」的生存環境,新的雜交品種會有更好的機會;而且假如它湊巧符合人類所好,或滿足某種人類欲望,就能立穩腳跟,找到路進軍世界。關於農業的起源,有種理論認為,馴化植物首度出現的地點就在垃圾堆,人們採集、吃掉野生植物,將種子扔在那裡,之後種子生根發芽、生長,最後雜交。人們採集這些植物時,無意中已根據甘甜、大小和效力進行篩選。隨著時間過去,人們將最優良的雜交品種引入園子,在那裡,人類和馴化植物展開一系列共演化實驗,永遠改變了彼此。
現今園子仍是實驗室,是嘗試新作物、新技術,又不必賭上農場的好地方。今日有機農場使用的方法,有許多就是在園子裡初次發掘。拿整座農場來實驗下一代「新東西」,代價太高,風險過大,正因如此,農人向來很保守,出了名的不愛改變。但是,對於我輩園丁而言,下賭注的風險相形較小,嘗試新的馬鈴薯變種或新的害蟲控制法算不上大事,每一季我都會做。
我得承認自己在園子裡的實驗很不科學,更談不上萬無一失或從中得到結論。今年種馬鈴薯,甲蟲蟲害控制得當,這究竟是我新噴的印度苦楝籽油奏效,還是由於我在附近種了兩棵粘果酸漿樹,而甲蟲似乎愛吃那樹的葉子更甚馬鈴薯?(於是我稱之為代罪羔羊。)理想中,我該控制一切,只留一項變數,但在園子裡不易辦到,這地方跟大自然其他地方類似,充滿了變數。用「一切環環相扣」來形容園裡的情況,或者說任何生態系的情況,似乎相當貼切。
儘管這麼複雜,我的園子也只能靠著試錯法來改良,所以我就繼續試驗下去。(本文轉載自《欲望植物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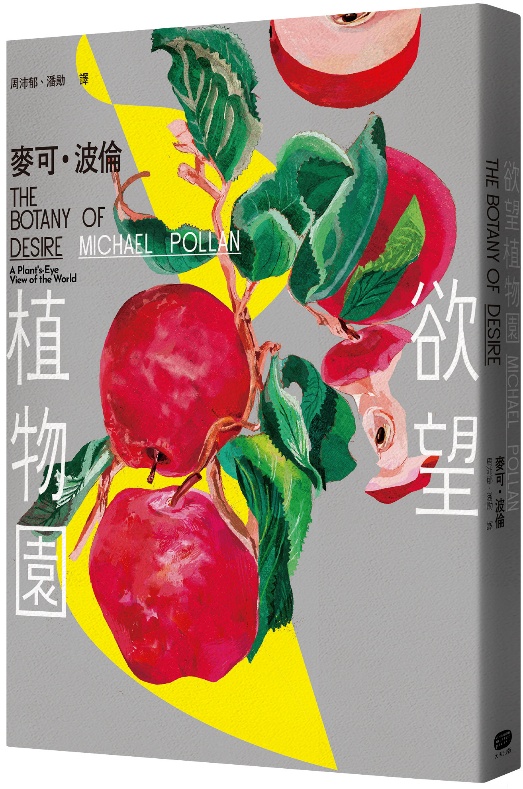
書名:欲望植物園
作者:麥可.波倫 (𝙈𝙞𝙘𝙝𝙖𝙚𝙡 𝙋𝙤𝙡𝙡𝙖𝙣)
翻譯:周沛郁、潘勛
出版:大家出版
出版日期:2025/06/2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