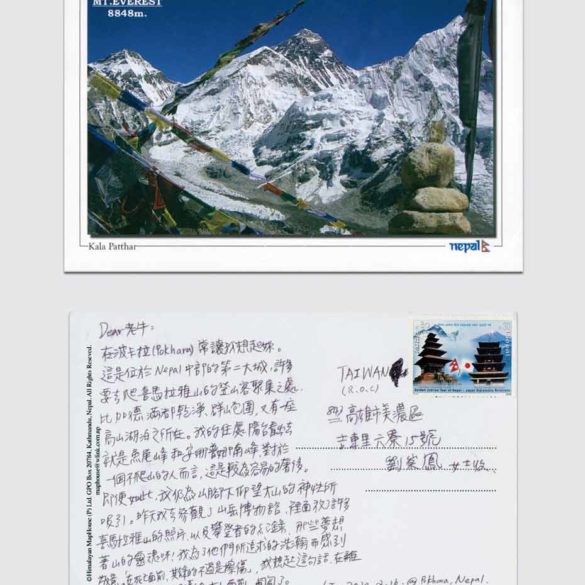溪流在水泥化與環境保護的兩種思考間擺盪,記憶、情感、混雜著經濟與身家性命安危的考量,村民與知識分子的意見水流般沖激著這片翠谷。我尊重這樣的激盪,見證人與自然的相親與相離,並學會把握當今所見溪谷面容的每一刻,去創造、去孕生更多無形的流動,這一刻逝去就不會重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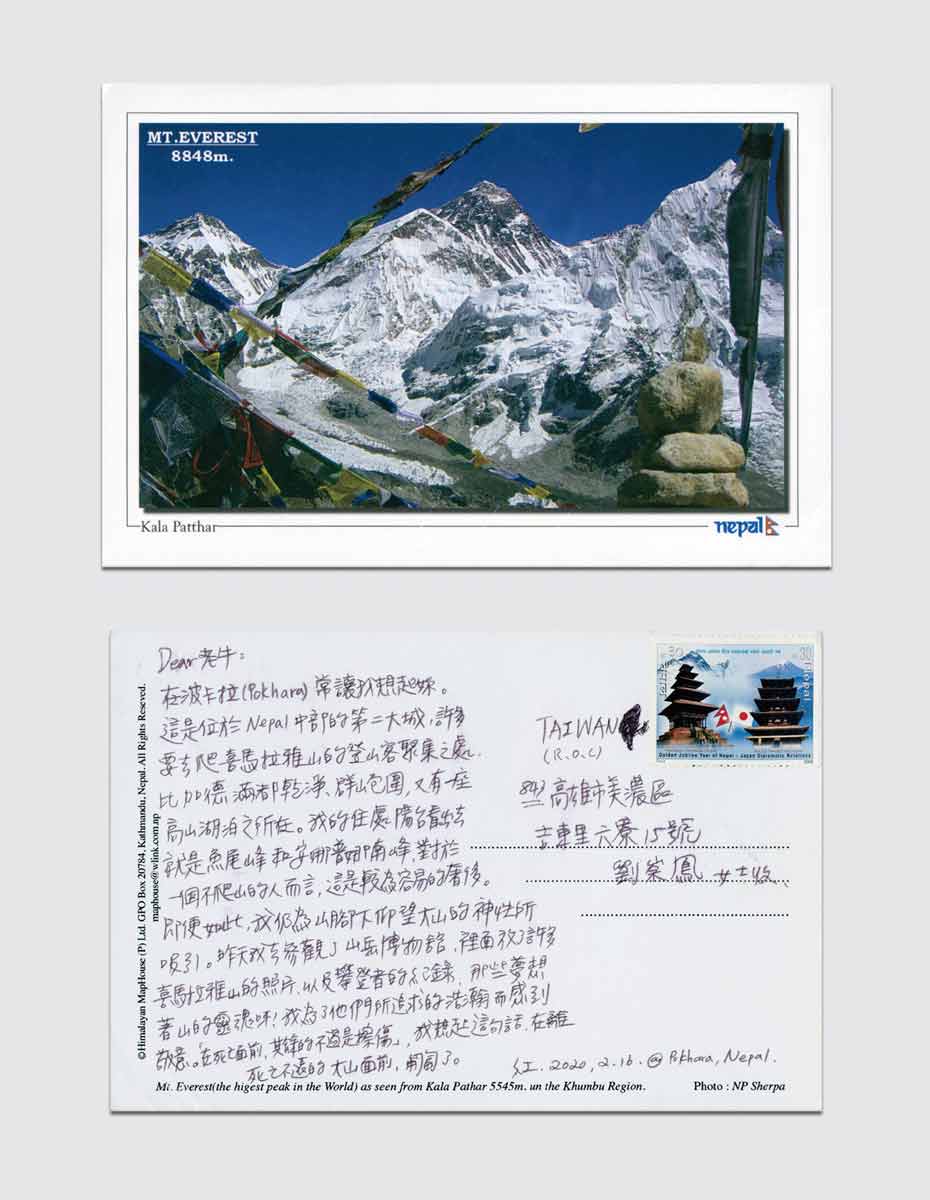
那一片防風林,我記得。林子裡的陸岸,會從泥土慢慢轉成沙灘,沙灘連接著海,往往走著走著,我會坐在林外的沙灘上吹風,看海,一迴身,便是成排的山。無論白天黑夜,山的靜定都帶來心安。
而我也記得在山裡眺望海的樣子。三千公尺的海拔之上,朗朗清空下能清晰看見海洋,蔚藍的海岸線和天空相連,每當在那麼高的地方遇見海,「海!海!海耶!」總像孩子一樣興奮。
海邊回望著山,山裡眺望著海。而溪流,是山林與大海的橋梁,如母親一雙溫柔的手,安穩的搖籃會接起漂流的孩子,水自山裡,刷出溪谷,從涓涓細流到泱泱大澤,向下行旅,愈走愈是開闊,毫不遲疑奔向人間,交融出那我們一點都不陌生的,匯流如花的出海口。
我曾被溪流救贖過,在一個暗潮洶湧孤魂也似的臨暗時刻。
1.
那個傍晚,思緒混亂,得費很大的力氣不停拉自己回當下,才能打理細瑣的行囊。溯溪鞋帶不帶?早餐吃什麼?鋸子放哪去了?刀、我的刀呢……我東抓一個頭燈、西拎一個水瓶,一邊打包一邊渙散地想到底要不要去溪邊過夜?一整天在家掙扎與拖延,在太陽下山以前,終究是逼自己跨上機車,狼狽地離開了家。
即使出發了,還是渾渾噩噩,不知該怎麼辦,要去向何方?留丈夫一個人在家裡,晚上還要獨自吃飯……心裡糾結,美濃水橋旁停車,蹲在水圳邊撥電話:「我去溪邊過夜……你、你還好嗎?你會不會很無奈?」其實我根本不知道自己這通電話有什麼用,就像我懷疑溪邊露宿有什麼用,走投無路之時,只能把自己流放到山水間。
「沒關係,妳去吧。」丈夫的聲音低沉,卻很平靜,莫名穩定了我。在掛斷電話以後,神智終於清楚了些,驅車往山谷裡騎去,即便黃昏轉瞬即逝。
淺山的溪流不深,將車停放在林子間,穿過一小段芒草路,將拖鞋藏在岸邊的石頭下,換上溯溪鞋,水流漫上腳踝之時,我感到沁涼。中背包負在肩上,潺潺水聲相伴,山谷曲折的走勢收攝我散亂的心神,只是專心走著,向晚時分,蟲鳥齊鳴,水的深度在膝蓋上下起伏波動,走到營地之時,天幾乎要黑了。
不行,我需要火。
戴起頭燈,掏出刀鋸,砍下山壁旁的竹子,爬上山坡上鋸木頭,鋸子的聲音在山谷間響起,我感到明晰的存在感,能自主供應自己所需,而不及細想傳統農村的客庄山谷,一個女人在這裡做什麼?專注地蒐集木柴,拖著一根粗大的枯木幹自山坡走下溪岸,汗水自顏面滑落,感覺自己的呼吸、天地的存有。身體愈是濕黏,我就愈發清醒。
火柴擦出火光,點燃細枝落葉,金色火苗竄起,連忙添柴,看火慢慢長大。火光閃動間,攤開地布與睡墊,為自己鋪張床,抬頭看看天空,星星出來了,今晚就偎在火邊,不搭天幕了吧。
夜裡,我獨自在溪畔的石頭跳上爬下,水聲清明,山谷好安靜。滑入水中游泳,任水流包覆,舒展四肢……依稀看到另一頭有激盪的流水,嘩啦啦啦刷洗著石頭,我划水過去,變成其中一顆石頭,嘩啦啦啦任其刷洗── 嘩啦啦啦、嘩啦啦啦,白天的淤塞與疼痛,盡數放水流去。
嘩啦啦啦、嘩啦啦啦,夜裡的水不冷,只要全心收受。我趴在溪水中,將身體的重量交付,層層疊疊的圓石成為按摩床墊,這麼被水沖著、洗著,一陣舒暢,身上有什麼正緩緩剝落、解離?
水是母親。
迴身向岸,床邊有火。
火是父親。
我在父親與母親的懷抱中睡去,清晨醒來,神采奕奕。脫了衣服又去水裡,邊划邊玩,仰漂以及翻滾,聽見自己發出歡快的笑聲,爬上石頭曬太陽,藍天底下感受胸口明顯的起伏……起身,望見水中自己的倒影:高束的髮髻、瘦削的肩、細窄的腰、寬胖的臀,女人的身形,落在水中央。
一個念頭閃進腦海中。被水喚醒的感覺真好。
深呼吸一口氣,我知道我要做什麼了。「請多多指教。」彎腰,向這片溪谷致敬。
水流潺潺,千古不息。
2.
一個月後,在當地組織和長者的支持下,我邀請夥伴到美濃,一起開辦「溪女」工作坊。二十個來自島嶼四面八方的女人,來到這傳統客庄農村,匯集在翠谷的山腳下一幢新式樓房中,圍坐成一個圓。都是為了水而來的。
一個三十歲的女生背著吉他而來,一個四十歲的女子騎著機車抵達,一個五十歲的女人預計搭便車而走。
幾個夜晚,我們圍著生命低低絮語,女人的故事很長,如河流一般,有時說著說著,不知怎麼眼淚就流出來,哽咽地吸吸鼻子要吞回去,「流下來吧,沒關係。」另一個女人拍拍她的肩。
那是一種怎樣的理解?無須多說,我們懂得。阻斷的是情感、淤塞的是記憶,砌起硬邦邦的水壩,我們不允許氾濫。
連續幾天,想到就去溪裡、想到就去溪裡。無須引導、沒有目的,一群女人在水邊各做各的。有人在石頭上發呆、有人在溪裡游泳、有人在滑瀑間做S P A、有人爬上巨岩跳舞、有人漂在水中央、有人在岸邊睡著了……一個女人抬著大鍋子前來,鍋裡是熱騰騰的炒河粉,那是自越南嫁過來的新住民媽媽準備的。女人們就聚集到飯鍋旁,溪畔野餐。
僅僅如此,便聽見了喟嘆。我會恍惚,懷疑這裡不是美濃,不是家鄉,而只是電影中哪個不知名的山村。
一個女人沒來吃飯,在溪的另一側,她將自己身上的披肩披在兩個大石之上,在裡頭創造一個空間,穿來鑽去,很開心的樣子。發現她一瞬,我以為她是七歲的小女孩,臉上的笑容不為誰而生,單純為她自己與水、與石頭的互動而綻放,深深地快樂著。
沒人想打擾她。大家不約而同記起昨夜她訴說母親死亡的眼淚。
即便不是高山清澈的溪澗,農村業已水泥化的河流,也能洗去我們的憂傷、撫慰我們的失落。慢慢明白了,在我們為野溪水泥化爭論不休的同時,並未意識到,水泥化的溪流,就是我們自身。
於是有一天,我們攀下一座橫跨整條溪流的攔水壩,扶著高高的水泥立面而行,用身體去經驗經過壩體沖刷下來的水流,其上綠色青苔濕濕滑滑,生命從不放過任何縫隙生長。我們故意的,就是要走這條路,依著壩體過水,與壩體親密無間,從中理解它為什麼會在,人們為何如此選擇?
如我們內建的堤防。
「真的,就是要築這麼高。」一個女人這麼說,臉上帶著理解的微笑。似乎唯有如此,我才能原諒水泥化的自身,看清自己,毫無罣礙地投入溪水的懷抱裡。
3.
午後,甦醒時,身側還有女人在睡,揉揉惺忪的眼,手抓著被單一角,望著窗外的天空。烏雲密布,陰沉的天空讓室內跟著昏暗,一種朦朧的心慌感浮現,記起幼年不太喜歡這樣陰暗的光線……忽然一片銀光乍現,閃電!而後出現悶沉的雷聲。
走下樓,大廳上安安靜靜,一個女人在翻書、一個女人坐在藤椅上納涼,還有一個女人乾脆搬了椅子到外面屋簷下,看天。她如貓一般蜷曲在椅子上,看天的神情專注,惹得我也搬了一張椅子出去,一起看天。
一推開門,一股涼爽的風襲來,灰暗的天空似乎不那麼叫人心慌了。
蜻蜓滿天飛舞,山雨欲來。我們坐在那裡仰望,看風、看雲、看深處的閃電如何閃耀烏黑厚重的天空。安安靜靜的午後,又有兩個女人走了出來。一個靠在機車邊側,一個直接躺在水泥地上。
大家都在看天。
「好希望下雨喔。」開始期盼雨的到來。
天空一直閃著白光和打悶雷,還在憋啊?趕快放水下來啊。
等久了,我進門上二樓,才上去不久,就聽見下面傳來興奮而壓抑的喊聲:「崇 鳳,下雨了!」
真的?跑下樓的同時,依稀聽見淅淅瀝瀝的雨……可不是嗎?柏油路面被一顆一顆的小黑點沾濕了,細細的雨絲落了下來,像溫柔的白色棉紗。
下雨了、真下雨了!我跑進雨中,開心地轉圈圈。彩色的世界在旋轉中糊成一片,我是我自己穩定的軸心。
一個個女人陸陸續續跑了進來,她們在雨中跳起舞來,渾然不管身體是否會濕透,每個人都享受雨水。
啦啦啦,啦啦啦,我們在,天空落下來的溪流裡飛翔,以及旋轉。
大概是笑聲太鮮明,一旁住家突然拉起了鐵捲門,一位老阿嬤探頭出來,一臉驚愕,下一秒眼睛就笑彎了,眼角的皺紋壓得密密深深,好可愛。
雨水是水,潤濕我們的肌膚;血水是水,周轉在我們的身體裡;眼淚是水,流出了我們的眼睛── 我們就是水,就是溪流,就是海洋。
雨水成河,歡笑一片,戲耍一片,我們如此匯聚成海。
4.
最後一個晚上,收拾行囊,決定去溪邊過夜。
「想要火。」一個女人說。
又是臨暗時刻,戴起頭燈,四散撿柴,手鋸木頭的聲響在暗夜中明晰地響起,這場景似曾相識……而我不再是一個人,一群人有明晰的意念與方向。
火苗在她手中擦撞出來,翻轉童話,賣火柴的小女孩不再孤苦無依,冬日會遠去,春天還會再來,如同黑夜的存在是為了迎接白日到來。每一個女人拾一根柴薪添入,火壯大了,輝映著彼此的臉。
是夜,圍著火的女人們不知怎麼了,沒有酒卻像醉了一樣,一一脫口而出心裡深處不輕言的故事。像深埋在水底的石頭終於鬆動、又或是存放太久的木頭突然起火燃燒,那些痛苦煎熬的情感或戲劇化的人生遭逢,都在這一夜獲得釋放。
明明是悲慘人生,卻只聽聞女人不停不停大笑,張狂放肆。幽默如海岸成片的鵝卵石,在洶湧的情感大漲潮之後,嘩啦啦啦退去時我聽見石頭與石頭間清靈細碎的聲響,滌洗過去每個倉皇失措的暗夜。
沒有評價,無條件接納,我擁抱我潰堤的水壩。
入睡前,唱一首搖籃曲給火聽,謝謝這片山谷,承載了我們似水的年華與星星般閃爍的祕密。然後一起走到溪畔,面朝閃著月光黑得發亮的溪面,要唱一曲耳熟能詳的兒歌。
一群三十到五十歲的女人,慎重其事站直身體,像回到童年的美聲合唱團。從沒這麼專心唱歌給河流聽過,唱得那麼深情那麼投入,歌聲裡溯源,身體深處傳來陌生的震動,無可抑止,我不知道那是什麼,好像河流為我們唱了這麼久的歌,我們卻從未唱給河流聽過,而現在我們要告訴她,無論她如何變換容顏如何蒼老甚至死去,都不會改變的── 「母親像月亮一樣,照耀我家門窗,聖潔多麼慈祥,發出愛的光芒……」
夜半微冷,露水深重沾濕了臉,大量的訊息來到夢裡,迷幻深奧,我睡不好,醒來多次,溪邊散步,直至晨霧降臨。
5.
從不知道原來可以這樣做,從不知道這樣做能帶來多少溫潤可親的力量。山與水、水與人、人與土、土與天。
走過許多地方,當年帶著大山大海、森林野地的氣息回到農村生活。歸來初期,時刻懷疑自己身上所帶有的這些東西,在客庄裡有什麼用?
而今一群女人在溪裡盡興地游,在山腳下的房子裡唱歌跳舞,對面的阿婆拄著拐杖站起來張望,放養的山雞翹著屁股大搖大擺走過家門前。
工作坊結束,心裡甜滋滋的好滿足,將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拉著丈夫上館子吃飯,哇啦哇啦跟他分享一切。原來不一定要東奔西跑遠登高山才會遭逢原始而美好的發生,淺山小溪也可以,而且更接近人間。我知曉我是誰,歸來是為了什麼。擁抱家鄉的全部,保守與創新都是養分。
我庄還是一樣,自反水庫運動成功後,在地鄉親持續為開發與不開發的爭議,耗心費神溝通至今,溪流在水泥化與環境保護的兩種思考間擺盪,記憶、情感、混雜著經濟與身家性命安危的考量,村民與知識分子的意見水流般沖激著這片翠谷。我尊重這樣的激盪,見證人與自然的相親與相離,並學會把握當今所見溪谷面容的每一刻,去創造、去孕生更多無形的流動,這一刻逝去就不會重來。
山是搖籃,水是搖籃裡的軟布巾,我們是軟布巾上的孩子,用母親給我們的身體和聲音,揮灑出生之榮耀。
「褪去固化的身影
朗讀覺醒的書籍
傾聽內在的聲音
耕耘本質的事情
平穩與安定
並非一成不變的寂靜
碎裂光影的風景
此起彼落的蟬鳴
攀爬石頭的小溪
鳥兒編織的天際
萬千變化的聲音裡
需要的是流動的生命」
那位背著吉他來的女子,回家後為溪流寫下新歌。弦被彈撥,應聲流動,水是這片山谷的祕密。如妳告訴過我的,若森林是海洋的戀人,那麼河流就是森林與海洋的媒人。一路順行而下,滋養萬物,勇於沖激,無畏撞擊,轉彎再轉彎,曲曲折折,最終總會穿出山谷,一望無際的湛藍大海,就在不遠的前方。
每一個孩子,都曾這樣沉睡而甦醒、遠行而回歸吧。
(本文摘錄自《女子山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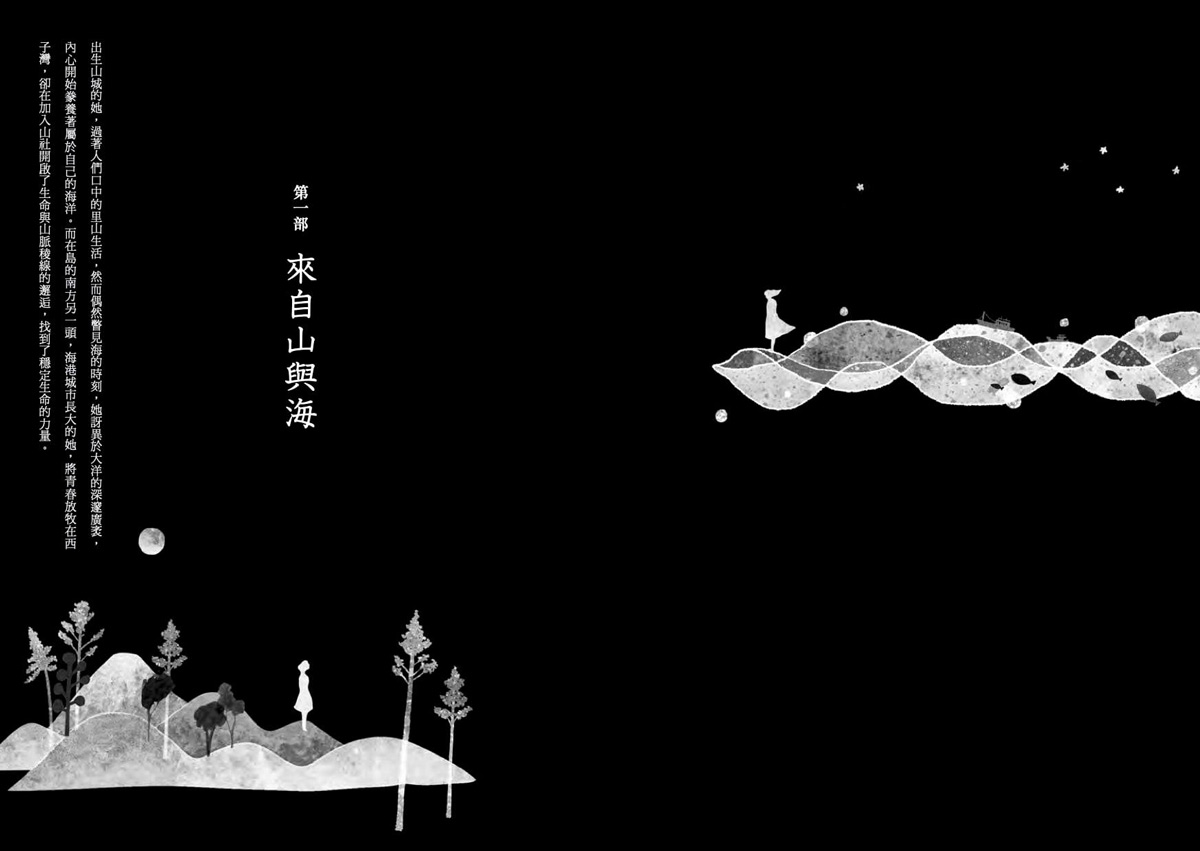
- 作者:張卉君•劉崇鳳
- 繪者:薛慧瑩
- 發行:大塊文化
- 出版時間:2020/12/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