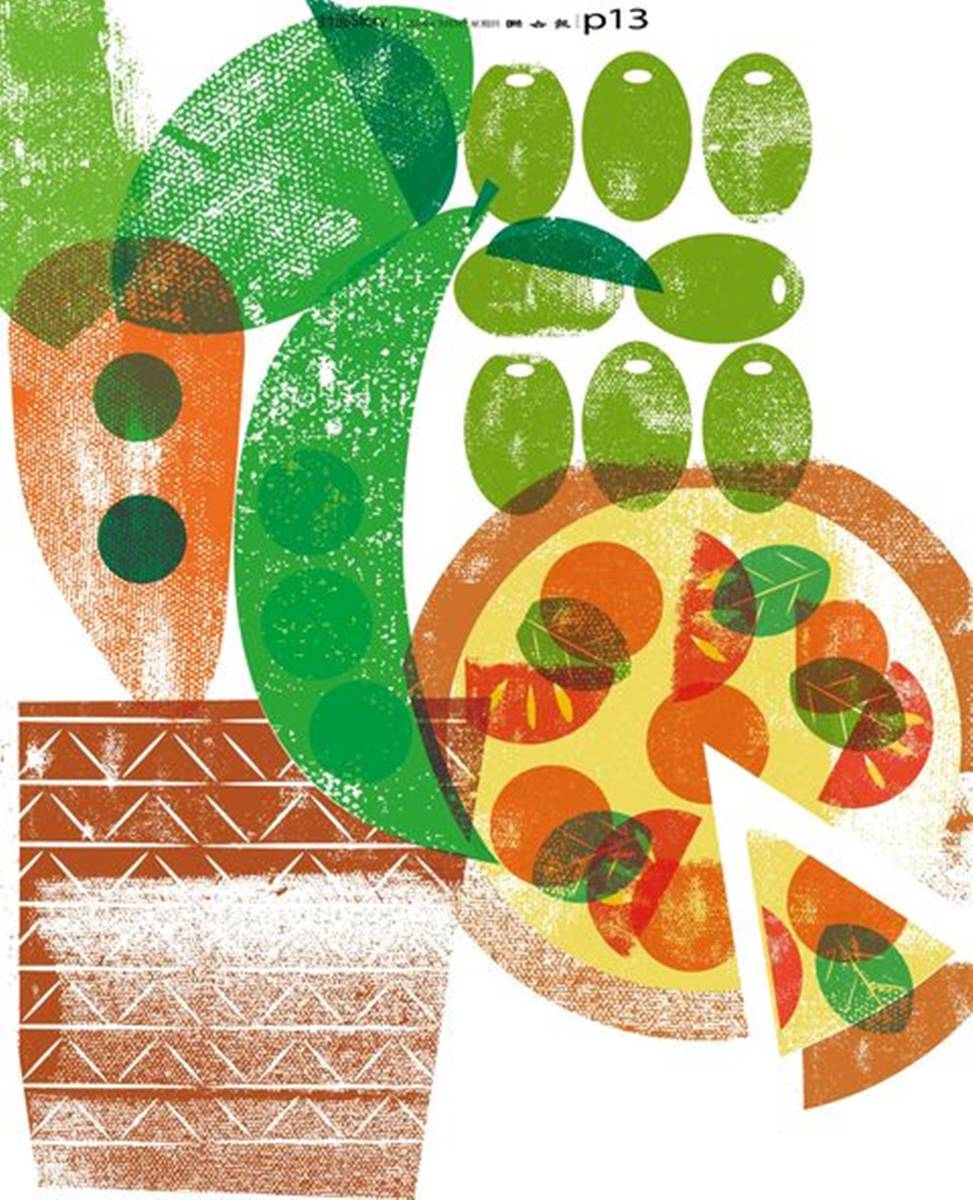冰箱有絕對的領域性,它帶有主人的氣味,像一棵經常被同一隻熊摩擦背部的樹。我的母親偶然來到我家送魚,拉開冷凍櫃並且評論了一句:「你要記得清冰箱啊!我都會清冰箱欸!」不知怎麼的我感覺有點火大,就好像在我最喜歡的樹上聞到另一隻熊摩擦後留下的毛。
同樣是在應付「時間」這個奧客,如果說按部就班的鐘錶做的是預示未來的工作,性格凜冽的冰箱顯然走的是反方向,它負責蹲點按下暫停鍵。由於冰箱在本質上就是負責應援的後勤部隊,無法隨行在側﹝除非搬家的時候﹞,一個人的冰箱,永遠比外露的錶更私人,它具體而微體現了一個人的各個面向,好比一個人的房間,向來比帶出門的行李箱更全面,更難以矯飾。
一座冰箱也容不下兩個主廚,意見太擠
冰箱有絕對的領域性,它帶有主人的氣味,像一棵經常被同一隻熊摩擦背部的樹。好比說我的母親大人,其冷凍庫永遠是一個宇宙大爆炸的狀態,塞滿了她家宇宙運行的道理,我閉著眼睛都能看到裡面有超過兩打以上戰糧般的自製五穀雜糧饅頭﹝早餐﹞,幾包美濃帶上來的冷凍波羅蜜肉﹝甜點﹞,以及來自大溪漁港的分裝鮮魚﹝晚餐與便當﹞,這幾個基本元素日昇月落不斷循環出現在餐桌,確保家的運作如常。
至於冷凍庫其餘品項我不太清楚,主要是因為所有的內容物幾乎都分門別類用只有她認得的塑膠袋層層密封,冷凍櫃一打開一般人只會看到一球一球看起來像鵝卵石的塑膠袋,除非眼睛內建X光,內容物無可辨別。
常言道,一個廚房容不下兩人,一座冰箱也容不下兩個主廚,意見太擠。我認識自己的親生母親數十年,從來沒有好好認識過她的冰箱,是因為我知道她也不太想知道我的看法,我們兩人對於醬油品牌都無法獲得共識,她經常毫不矯飾地對我的烹調建議嗤之以鼻,更別說是如何安排冰箱的布局。一般狀況下,我們應該彼此看不順眼彼此的冰箱,但是無論怎麼無法忍受對方的廚房習慣,我都選擇自掃﹝冰箱﹞門前雪,這是能夠快樂活下去的首要基本心理素質。
豪雨過後的土石流VS.設計過的花圃
因此當我的母親偶然來到我家送魚,拉開冷凍櫃並且評論了一句:「你要記得清冰箱啊!我都會清冰箱欸!」不知怎麼的我感覺有點火大,就好像在我最喜歡的樹上聞到另一隻熊摩擦後留下的毛。我試圖想釐清她到底看到的是什麼,到底是她餘光掃到了先前送我的一小罐炒花生﹝剩下十來粒 ,我以為我很快會把它變成木瓜涼拌的一部份﹞?還是不小心知道角落那包大紅辣椒已經閒置太久?
總之聽到她越界的評論時我馬上起立答辯,用儘可能自信的語氣跟她強調我會清冰箱,而且我的冷凍庫可是有分門別類的,我很早便弄來了幾個客製的L型透明壓克力板,把冷凍庫區隔成三大區:肉類、海鮮、配料與雜貨,要拿獅子頭就往左伸手,要拿馬頭魚就往中間翻尋,充滿了科學精神。我希望她能聽得出我的暗箭,因為她的冷凍庫在外人面前看起來就像豪雨過後的土石流,我的像設計過的花圃。
我家冰箱剛來的拓荒時期,冷凍庫並沒有分隔板,但是很快我就厭倦了大海撈針的挖掘工作,因為每次伸手進去找一樣食材,都會不小心翻攪到其他,使得冷凍庫就像旋轉中的洗衣機一樣,把不同屬性的食材翻到雲深不知處。
對我來說,食材的曝光度能有效爭取它受到處理的速率,一個人平常要同時處理三百六十五件凡塵瑣事已經讓人身心俱疲,根本不要期待自己能夠深刻記得冰箱某個離奇的小角落夾藏了一小袋待處理的蓮子──我們都忙到連昔日戀人的長相都已記憶模糊,怎麼還會記得那不到半公分厚的澎湖扁魚乾放在哪個隨機的角落。
我的訴求很清楚,我需要冰箱內部建檔,最好不要浪費太多時間在無謂的尋找,最好是肉啊魚啊都像站在高原上大喊「快來吃我!」那樣,擺在沒有太多雜訊的正確地理位置,這個原理和Tinder相去不遠。人類確實是視覺性的動物,看不到的食材就像網戀一樣飄渺,冰箱裡的東西你必須清楚看到,才會感覺需要,才會把它挪出來變成盤子裡可夾食的美味,這是一個簡單而殘忍的事實。

不知心的話 你可以去開一下他的冰箱啊
然而即便我已努力科學性處置我的冰箱,依然還是有讓人迷惑的片刻。那天在雜貨區翻找干貝的時候,突然從深淵一樣的底部掏出了一包……到底是多久以前冰進去的香茅?啊是的,應該是當時買來準備做越式嫩雞時提味用的,這麼一想,幾乎可以想像手上的香茅被敲裂時迸發出來的檸檬甜香。
可惜當天我要做的是西式料理,於是我把它慎重放回座標位置。此後這包不顯眼的香茅三擒三縱被我驚詫地從底部捧出來三回,那道料理依然被無限期擱置。我默哀,到底是它的存在感低落,還是自己的記憶力頹危?我漸漸覺得是後者,想到前陣子整理在雲端的「幾百種網頁登入密碼之自製提示一覽表」突然人間蒸發,我簡直如喪考妣。
比起打開一個人的衣櫥、一個人的臉書、通訊紀錄或垃圾桶,打開一個人的冰箱可以揭露的訊息永遠比自己想像的更多。過剩的、空洞的、重複的,只有冰面膜或冰啤酒的,或者一打開便山崩的。
不都說冰箱具體展現了一個人的方方面面嗎?這個頓悟是從與人合租宿舍的時期開始的。常常聽人老派地手背拍手心說:「知人知面不知心啊!」我都很想講講幹話,說,不知心的話你可以去開一下他的冰箱啊。
共享冰箱簡直是一座四方體的濃縮星際大戰
此生我搬家的次數不多,曾經擁有過的室友﹝扣除家人不算﹞卻過剩。只要開過社區管理委員會的人大概都知道,即便是沒有住在同一個屋簷下的鄰居都很容易讓人忍不住按摩太陽穴,直接在居住空間內部遊走的室友加倍容易觸動情緒火災警報。分享其實是痛苦的事,尤其是相互傾軋的那種。
經常開伙﹝我指的是計劃性烹調,而不是大鍋菜吃一個禮拜﹞的人可以告訴你,如果一個人的時間有限、經費有限,又不像澎湖或馬祖離島的民眾那樣在家擺了巨無霸冷凍庫,隨時可以冰進一整隻海運來的豬──在家煮飯這件事其實需要有點基本的邏輯與評估能力,它需要釐清先後順序,計算平衡與速率,並且能夠設想大局。使用冰箱,人必須誠實。
比起浴室排水孔誰的陰毛沒有撿乾淨,或者誰偷用了我的洗碗精這種小型的零星內戰,共享冰箱簡直是一座四方體的濃縮星際大戰,一次出現四個黑武士的那種。可以撿起來、可以洗乾淨的東西只是點到點的代辦事項,雖然偶爾牽涉到一個人的品格,但不論怎麼心不甘情不願,還算是可以剷除的障礙。
共用冰箱不一樣,它很容易就發生侵門踏戶的事件,但很不幸地冰箱最曼妙的作用就在於擱置,無論好的壞的,它是一個延緩劣退的原件,以至於如果有什麼讓人看不慣的事件點起了狼煙,也是以樹懶般的消極節奏,反正,「一切都冰起來了」。
永遠會出現類似史前遺跡的化石,無人招領
我如果有任何基本的做菜能力,基本上都是租屋在外催逼出來的求生本能,尤其租屋處不像台灣一樣,隨便下樓就能吃到便宜又大碗的東西。在這種處境之下,冰箱就像野外求生的火種一樣重要。對於許多室友來說,把東西冰進冰箱這件事,類似於把長毛象封入永凍層的概念,冰箱本身是一座史詩級的博物館,這都必須感謝「冰起來就不會壞」這個恆古以來的謠言。
如果有新的室友要加入我們的小型聯合公寓,導覽守則第一條就是介紹冰箱的分層,一般來說,長老級的室友會告訴新來的室友每一個人大概可以盤據的冰箱位置。冷藏空間比較寬裕,除了有人經常像老鼠一樣偷吃別人東西的禍害,沒有什麼太大問題,但是缺乏隔層的冷凍庫就像阿里巴巴與四十大盜的賊窩一樣,它的問題不在於無端消失,而在於死不消失,永遠會出現一些類似於史前遺跡的化石,無人招領。
我曾經有過一位研究癌細胞治療的室友愛蓮娜,她應該比誰都還要清楚細胞膜與細胞核,以及正常的生物細胞放在冰箱冷凍庫不等於永生那一類的事。如果僅靠著一些社會性的頭銜判斷而不夠認識她的話,也許會以為愛蓮娜數學很好、邏輯甚佳,並且行事作風小心翼翼。
實際情況是,愛蓮娜開車的技術讓她經常差點輾過路上行走、時速1公里的雁鴨,而且她不拘小節的生活習慣讓我懷疑這才是人類到目前真正無法破解癌症的根本原因。這個風格也許不能從她這個人的形象、交友關係與房間的陳設看得出來,但是完全可以從她與冰箱束手無策的失憶關係彰顯出來。
曾經的冰箱作為 讓我很精準地憶起他們的性格
租屋在外賦予我的第二項能力,就是有話直說。要練習這個能力最好的練習,就是從共享冰箱的冷凍庫拿出一塊礦石般滯留太久的食材,走到每一位室友的房門面前,面不改色地敲門,開門見山問對方:「請問一下這個是你的嗎?」當你要爭取冰箱空間﹝或者其他本來就該屬於自己的東西﹞的時候,你就應該這麼直接,而不是忍受別人的忽視,或者冰箱內部無謂的擺爛。
「愛蓮娜,這玩意兒是你的嗎?」愛蓮娜注視著我從冰箱裡拿出來的即期品,經常歉然地表示她忘了。後來我們發展出一種若即若離的新室友模式,在她丟棄的過期食材已經累積到不可原諒的時候,我們開始一起吃飯,她提供食材,我提供烹調技術。再後來她拿到了癌細胞治療領域的最高學位,但是她決定離開這個科學領域,我們雖不夠親密,但某種程度上我能理解。她從來不是能夠從重複規矩的實驗中獲得快樂的人。
後來我又遇到了號稱養生但冰箱裡除了補品就是零嘴的人、重複買青蔥但不斷不斷讓青蔥爛掉的人、總是一次煮好一個禮拜份白米分裝成小磚存入冷凍庫的人⋯⋯我可能已經不記得這些人偏好的服裝款式,但是這些人曾經的冰箱作為卻很精準地讓我憶起關於他們的性格。
我的母親大人總是喜歡耳提面命,到菜市場買菜要跟著季節走,如果不是當季的食物,它太貴,而且不好吃。在某種程度上,冰箱是旬味追尋的調節器,比如說,我家常備冷凍澎湖日曬小管一夜乾,寒流的時候一邊翹腿看著電影,一邊烤幾片小管下酒,也能感受到夏季暖呼呼的陽光與海味。既人性又科技。

我和時間本身到底還是相安無事
安頓一個人生活裡的時間感,首先要有耐跑的鐘錶,其次要有座不錯的冰箱,最好是自己的。安頓,多麼慈祥的狀態,可惜無論是鐘錶或者冰箱,都各自有各自的極限,時間自有安排。
我喜歡戴錶,甚至睡覺的時候也喜歡戴著,因為醒來的時候睜開眼睛就知道時間,有種寒流中受到棉被簇擁的安全感。
這並不表示我是個非常有時間觀念的人,實情完全相反,且這劣根性從小時就表露無遺,印象裡面我總是那個升旗典禮都已經進展到一半,才匆忙從校門口跑進來,小偷一樣跑到排尾去站好的人。小學時早上練跆拳道,原本是想逃離升旗典禮,結果連練拳也遲到,一遲到就被教練往腦殼上賞好幾個爆栗子,拳法我都忘了,教練敲頭的指節手感倒是很深刻。
我的時間觀念終究在社會化之後稍微被制約了一點,畢竟無情冰冷的打卡鐘不像朋友,只要遲到就會被扣錢,非常讓人心寒。經過長期飆摩托車飛躍大台北、極速趕打卡的終極訓練之後,久而久之我還是不免俗地變成了體制的動物,大幅度矯正了遲到的謬誤。﹝催稿的編輯可能在這邊要舉牌表示不同意﹞
不過呢,雖然這一輩子都在截止日和遲到線前奔波,我和時間本身到底還是相安無事,我喜歡手上有時間,看得到時間,就好像我喜歡檢查冰箱裡面的有效日期那樣,防堵任何腐爛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