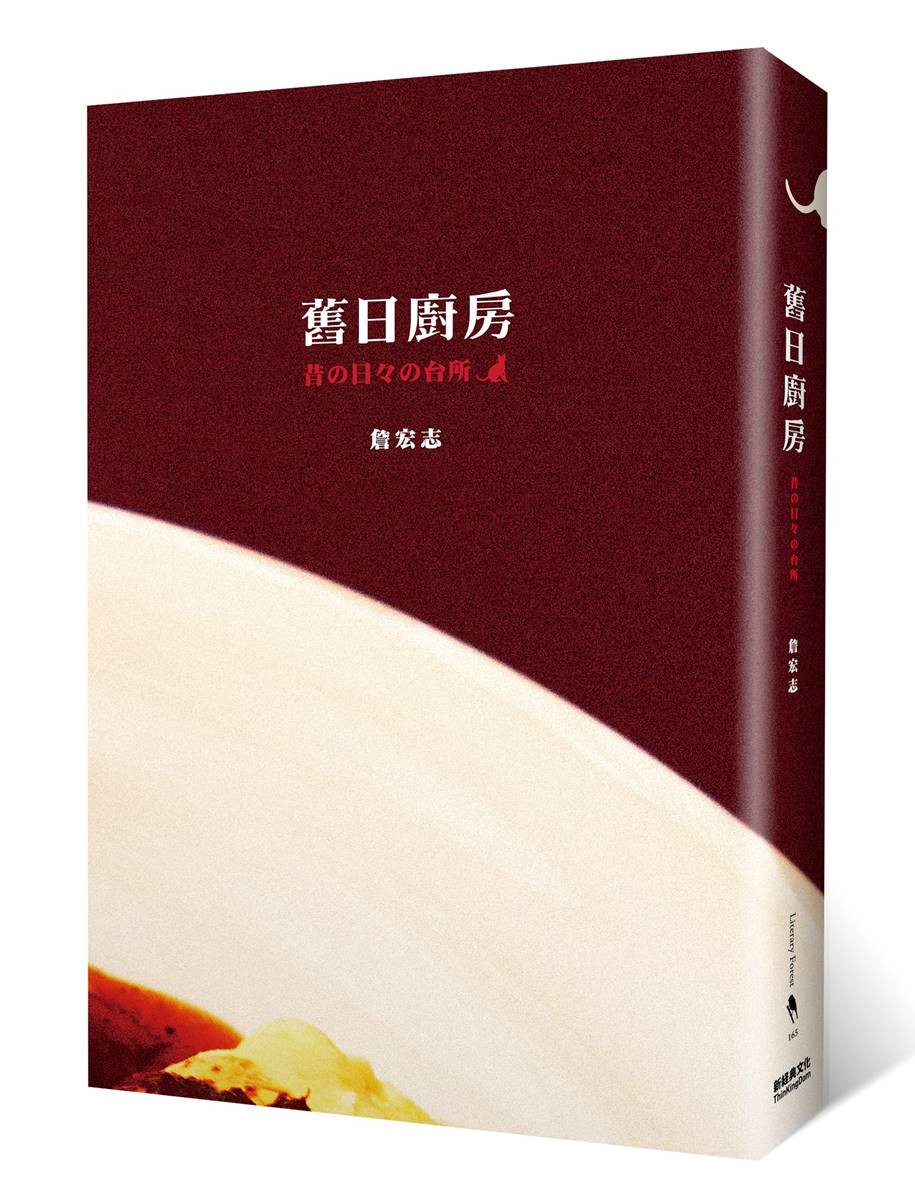她拿鐵鏟在爐火裡攪一攪,火光熾烈起來,映得她滿臉通紅,她下了一勺油,油上冒出煙,她下了蒜與辣椒,又下了一點紅色的肉絲,肉絲一下子變成了白色,她再把切好成段的韭菜花下了鍋,翻炒幾下又下點米酒,火焰衝出來,媽媽再把豆干都撥入炒鍋裡,又翻炒了幾下,她再從湯鍋裡舀小半勺湯加入鍋中,把鍋蓋蓋上燜煮一下,再開鍋,白煙竄出來,她快速起鍋……
四十歲以前的我,還是一個連燒開水都不會的無用男子,這當然是媽寶之屬;小時候父母顯然有點重男輕女,女孩功課再忙,也被要求做點家事,但男孩子遠庖廚,好像就被認為無所謂了。
不過這樣斬釘截鐵的話,常常會被人生真相打臉。我母親要姐姐們做家事似乎出於好意,總覺得女孩家如果不學會做點家事,將來嫁人恐怕要吃到苦頭。但我的二姐初中聯考就考了個中部聯招的狀元,震動鄉里,報紙電台都來採訪,老師也帶著她到處去露臉領獎,出了鄉下人少見的風頭,從那之後,二姐似乎有了「家事豁免權」,媽媽也不太叫她做家事了;可憐我另一位頗有文學才氣的大姐,就淪為家中唯一必須幫忙做家事的女兒。
人生之事是福是禍或許不能太早下定論,後來我大姐燒得一手好菜,頗得朋友與家人稱許;我二姐卻許多家事都不擅長,自己頗為懊惱,這件事她一直要等到擔任大學教授接近退休之際,才發奮圖強,力求在廚房當中能尋回自信。現在手藝愈來愈好,但錯過少年時期的學習,今天她的廚藝完全和母親的菜色毫無關聯,成了一個沒有家傳來歷的自學廚娘,不能不說也有點遺憾了。
要說男孩子沒有被要求做家事,好像也不完全對,至少我從小就是家中的「小跑腿」,臨時家中少了什麼柴米油鹽,媽媽幾乎都是派我出去採買,「小弟,去買一斤雞蛋。」
「小弟,去買一塊錢味噌。」
媽媽一面交代,一面把錢交給我,我一溜煙就跑到菜市場去了,雜貨店就在菜市場口,我向老闆說要買味噌,老闆馬上拿起一張粽葉,從木桶中用飯匙舀出一勺土黃色的味噌來,把粽葉包好,用繩子繫好,笑盈盈交給我,一面還交代:「路上拿好,不要打翻了。」
雞蛋則要到另一家店去買,店就在市場裡面,那是一家賣麵條的小店,門口則擺著整箱的雞蛋,放在防止磨擦的米糠上,白白的雞蛋沾滿了黃色的米糠,乾乾爽爽的,拿起來很舒服,我小心翼翼一顆一顆撿著。媽媽很早就在菜市場教過我怎麼挑雞蛋,要看雞蛋外殼有沒有破損,要純白近乎透明,要拿在手上有沉甸甸的扎實感……。
為什麼買東西都是我的差事?家中有哥哥、弟弟,但他們都只是母親不得已的「第二選擇」,只有我才是正選。原因可能是媽媽看我不愛讀書,最愛往外跑,叫我出門算是「投其所好」,不覺得是苦差事,而叫我哥哥出門買東西,他就苦著一張臉,好像是接到什麼痛苦的任務一樣。另一個原因可能是我比較大膽靈光,絕對不會容許賣東西的攤商找錯錢或開出離譜價錢來。如果老闆找我短少的錢,我就直挺挺站在那裡,一臉嚴正說:「昨天我媽媽來不是這個價錢。」我堅持說這和媽媽買的價錢不一樣,老闆在別的客人面前掛不住面子,一面補給我錢,一面嘟嚷地說:「昨天是特別算你媽媽便宜。」幾次之後,媽媽知道我是使命必達小跑腿的最佳人選。
等到我四十歲以後,失業在家,突然有了學做菜的念頭。我一開始進廚房,水深火熱,手忙腳亂,壓根兒沒有想過做家庭主婦們做的菜,或者說我一點也沒有勇氣做「家常菜」;對我來說,那些家庭主婦每天做的菜是最難的,因為她們那麼駕輕就熟,我如果冒失闖進去,我的笨拙一定落得個人人嘲笑的下場,這絕對不是初學者最想見到的場面。事實上,我一開始嘗試的料理,是從一道義大利的「蔬菜湯」(minestrone)做起的,學習的方式是來自食譜書的「西洋料理」;我先學北義菜,再學南義菜,然後學習南法的鄉村家庭菜,之後又學西班牙菜、希臘菜。等幾年過去,我在廚房裡已經不怕刀不畏火,家中的主廚老婆大人看我逐漸有點樣子,開始也願意讓我在廚房裡擔任助手,交代我一兩個簡單的任務:「你把空心菜炒一炒。」或者:「你把湯熱一下。」
即使只是「把空心菜炒一炒」,我還是做得「戒慎恐懼」。這麼簡單的東西,就是半路出家的自學者最容易露出馬腳的地方。我開始回想小時候在廚房裡觀看媽媽做菜的樣子。媽媽隨手炒一盤空心菜,也要加上一句名言:「寧可人等菜,莫要菜等人。」她要等全家人都坐定了,大火把鍋子燒得火熱,半勺沙拉油下去,爆香拍扁的大蒜和辣椒,油燒熱了,切段的空心菜嘩啦一聲下了鍋,三下兩下翻炒,下點米酒,火焰竄起半天高,再滴兩滴麻油就起鍋,熱騰騰端上桌時,菜梗脆爽,芳香撲鼻,酒香麻油香大蒜香,加上菜葉中刺激的辣椒味,那麼平凡的一道家庭料理,卻永遠百吃不厭。
我卻一開始總做不好,鍋子不夠熱,油不夠熱,炒菜的動作不夠俐落,更糟的是,我不太會用中華炒菜鍋,我總是拿了西式平底鍋來炒菜,等到吃來覺得鑊氣不足,卻已經後悔莫及。
等我睡覺時閉上眼睛,試著回想母親做這些菜的模樣,我驚訝地發現中年後的我什麼都記得。我閉上眼,有著兩口大灶的廚房浮現眼前,爐火正旺紅紅地燒著,那已經是民國五十年以前的事,我才五歲或者未滿,我們還住在基隆的七堵。房子是日式陳設,榻榻米和紙門,後方的廚房卻是傳統台式,磚砌大灶在角落,灶的前方有四方桌充當料理檯,牆邊還有紗窗櫥櫃。媽媽似乎是在煮一道「韭菜花炒豆干」,年輕美麗的三阿姨在旁邊幫忙,我看見三阿姨把菜刀打橫,把棕色的大豆干橫向片下薄片,一片兩片三片,她把一塊豆干橫向片成六片,再把菜刀打直,直向往下切,切了八刀十刀,豆干變成工工整整的豆干絲,媽媽在一旁起大油鍋,她拿鐵鏟在爐火裡攪一攪,火光熾烈起來,映得她滿臉通紅,她下了一勺油,油上冒出煙,她下了蒜與辣椒,又下了一點紅色的肉絲,肉絲一下子變成了白色,她再把切好成段的韭菜花下了鍋,翻炒幾下又下點米酒,火焰衝出來,媽媽再把豆干都撥入炒鍋裡,又翻炒了幾下,她再從湯鍋裡舀小半勺湯加入鍋中,把鍋蓋蓋上燜煮一下,再開鍋,白煙竄出來,她快速起鍋,把整盤菜放入大盤中,韭菜花與豆干綠黃相間,加上紅辣椒和灰白肉絲點綴,很漂亮的一盤菜。
我繼續回想媽媽做大黃瓜鑲肉的模樣,她拌肉餡,有絞肉、有香菇、有蛋清、有切碎的胡蘿蔔,用醬油和糖調味,然後塞入挖空的大黃瓜中,她把黃瓜塞肉放入骨頭高湯中,才煮滾一下下,她就用湯匙去試味道,點點頭,她很滿意地加上一句名言:「四腳走過的就好吃。」原來,透過一個小孩天真的眼睛,那些遙遠的廚房舊事,我一切都記得……(本文轉載自《舊日廚房》,刊頭照片為版刊所配)
【說說書】試圖留下家庭的滋味,從認真宴客找到力量
文:新經典文化
從「40歲前對烹調一竅不通」,到積極做菜、認真請客、書寫飲食。
詹宏志追溯自己「食的經驗」,發現味覺記憶主要受母親、岳母和妻子等三個女性的影響。他親自下廚、試圖留下記憶中家庭的味道;他由菜憶人,讓平常化為最恆久的思念,也在中年之後自辦一場又一場的家宴中,見證宴客原來是如此凝聚親朋好友的力量……
「這三個女人的料理實際上構成了我一生飲食的主軸,我總把這些菜色的出現和存在視為理所當然;等到她們都離我而去,我才警覺,所有的味道都要靠人的不斷實踐才能維持。」
每一個母親的拿手菜,都來自家庭的薰陶與傳承。詹宏志的母親、岳母、太太,各有一手好廚藝。母親為傳統台菜料理、岳母為典型江浙菜,太太承襲岳母的廚藝與天賦,嫁入台灣人家裡,接觸不同的飲食文化,學習台菜並加以改良變化,後期出國旅行日多,接觸了更廣的「美食地平線」,餐桌上多了更多異國的風景。
詹宏志有感於每個家庭的滋味都應該珍惜,而珍惜的方法就是不斷有「傳承」,也就是要有晚一輩做上一輩的菜,每個家庭必須都有新一代的下廚者,而他也必須有興趣保存家中某些獨有菜色。這一次,他時而回憶過往,決定為這些菜「補課」,追尋故人的味道。他從這三位女性的菜色出發,發展出自己的詮釋,完成了這本集合眾人味道想像的真情散文集。
讓每個味覺記憶,藉由一次一次的試做與校正,慢慢摸索出相似味道
本書共分四輯,詹宏志娓娓道來38個廚房裡的飲食往事與豐富滋味。
詹宏志做菜「富實驗精神」,在他心中「媽媽的味道」,不一定是最高明的宴席,卻常常是一個人味覺的原點,我們會在後來人生的每個階段卻一再發現,母親的飯菜總有療癒之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