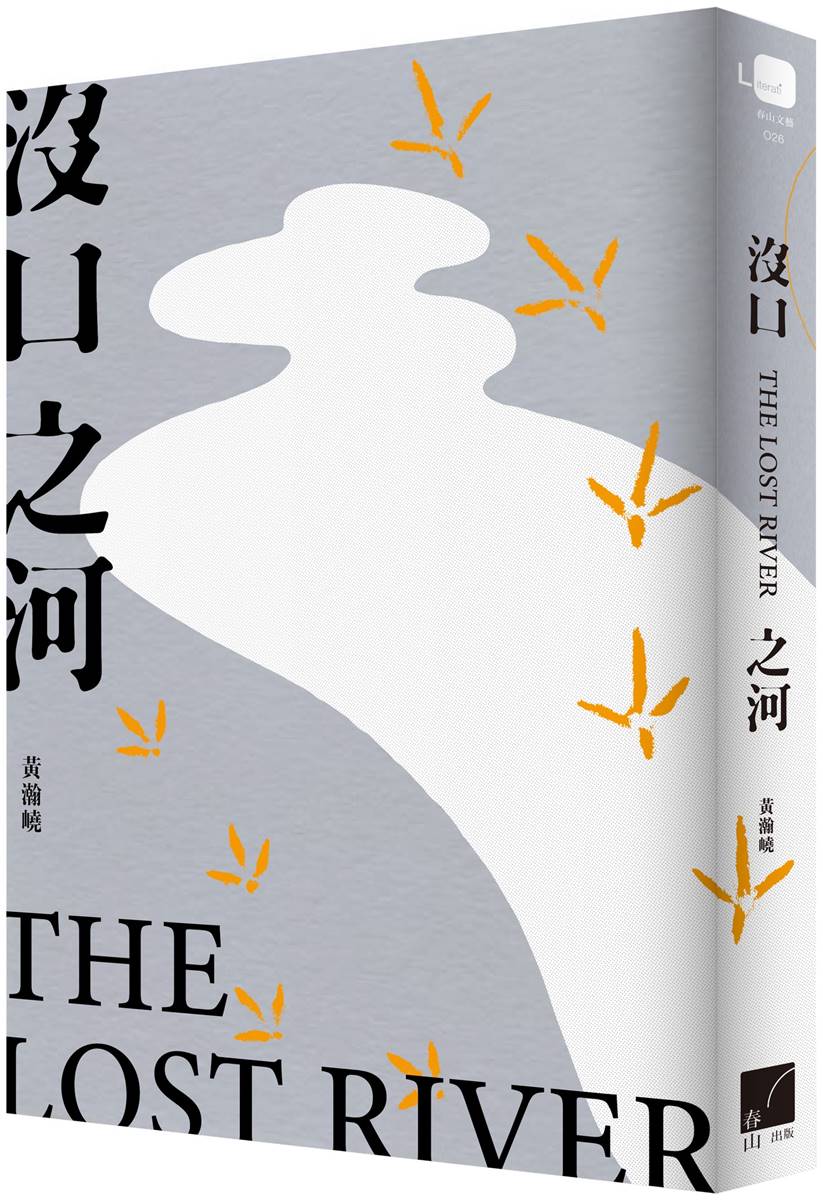藉由《沒口之河》試圖將人類重新放回自然之網中。他花了大量章節寫下卑南族部落人民自古至今,和其他民族、部落間的交流,以及他們創造、維持與利用知本溼地的形式。
也因此,讀《沒口之河》的時候,我常有一種感覺,瀚嶢似乎把人也當成了一種生物來觀察、描述並且記錄。
那天午後,讀完《沒口之河》後記的最後一個字,心中激動的情緒戛然而止。我像是突然失去重心,墜入到意識的深處,如沒口河般,隱沒到地表之下。
在意識的深處,一組朦朧的聲響此起彼落。裡頭混雜著水鳥鳴聲、爭論的人聲,以及植物彼此摩擦發出的婆娑之聲。我想到,如今生活的這座城市,在約一小時車程外的山間,也有一座巨大的高山湖,湖邊據說在上個世紀初,被無垠的溼地圍繞著。但在我漫步湖畔的回憶裡,我似乎不曾聽過這些聲響。經濟掛帥的這座城市悄悄地與湖爭地,不僅驅逐了鳥聲與草響,也許也掩蓋了抗議的話語。
這座城市是否有人能夠創作得出《沒口之河》這樣的作品?是否有一個人,他願意花六年的時間去記錄湖泊失去溼地的過程,就像瀚嶢一樣。
「對我而言,只要這裡仍是流路,就算只是暫時性的水體,但那個嚮往水,記憶水,那個信念流淌之處,就是實實在在的一片溼地。」

前往人群之中溝通自然
《沒口之河》是二○二二年底春山出版社出版的一本自然書寫作品。
作者瀚嶢與我曾在同一間研究室求學,他當時研究的課題圍繞在中國石灰岩植物多樣性的起源。長久以來,中國南方的石灰岩地貌就被認為是東亞特有植物的搖籃,許多植物學者致力在探索此地區植物多樣性特別高的原因,而瀚嶢的研究亦然。
瀚嶢以一種廣泛分布在廣西石灰岩地貌的秋海棠──鹿寨秋海棠為材料,探討了鹿寨秋海棠的物種形成歷史以及遺傳多樣性的起源。他發現,鹿寨秋海棠各地的族群大多具有地方性的獨特基因型,這種現象意味著,任何一地族群的滅絕,均可能導致鹿寨秋海棠某個獨一無二的基因型的消逝,進而對整體遺傳多樣性造成傷害。也因此,瀚嶢針對像鹿寨秋海棠這樣的石灰岩特有植物的保育,給予了他的建議,他認為保育必須盡量涵蓋各地區的族群,才能有效地防止物種遺傳多樣性的喪失。
瀚嶢的論文邏輯嚴謹,筆觸隱然已有學者的氣息。但我依稀知道,做研究之餘,瀚嶢還熱中於解說、教學和社會運動,他是優秀的生態解說者,受歡迎的樹木學助教,也是環境保育的行動者。如今回想起,這似乎隱約透露出他對自然的態度,不甘於學術象牙塔內研究自然,而是前往人群之中溝通自然。
畢業後,瀚嶢沒有繼續攻讀博士學位,但開始進行文學創作,並成立了一間藝術工作室。他雖然暫時不寫論文了,但改用畫筆與小說和散文來轉譯眼中的自然萬象。他的創作,不論是繪圖還是文學作品,都適切地揉合了科學的細節與細膩的情感,頗有自己的風格。也因此,在尚未閱讀之前,我對《沒口之河》十分期待。因為對於溼地生態系十分陌生的我,這次真的很想靠著瀚嶢的文字來好好認識臺灣的溼地,關於它的生態與原生動植物之美。
殊不知,第一次看到《沒口之河》的目錄,我心裡便有些意外。沒料到瀚嶢竟然大剌剌地用木麻黃、巴拉草等外來物種作為章節的主題。甚而,當我從第一章開始逐步認識起知本溼地,我赫然發現它並不是一個嚴格定義的天然溼地,而是一個位於知本溪舊河道上,由水圳排放之水所灌溉而成的季節性沼地。
瀚嶢怎麼會放棄那個,在我心中他最拿手的題材──臺灣自然生態,轉而去書寫一個,連是否能被定義為自然都不太清楚,還被外來物種大肆入侵的溼地?
作為研究植物多樣性的研究人員,我從這個驚訝中想到一件事,究竟什麼是自然?
以往,在向國家申請科學計畫資助時,我們不帶疑問地將自己的研究歸類為自然科學。我們默認的研究對象,以研究高山植物的我自己為例,可能是中央山脈深處的一個新物種,或是喜馬拉雅山大峽谷裡的某種稀有植物,那是一個原始大自然,裡頭鮮少有人類出沒,充滿著原生的生物相。許多自然科學的研究,彷彿主觀選擇一個沒有人為干擾的視角,在所謂無人的荒野中,研究純粹的自然的奧祕。
但瀚嶢似乎不同,《沒口之河》裡的知本溼地,是一處充滿人的自然環境。

自然現代性的回顧
「或許在現當代意義上的環境生態書寫,已從曾經名為自然,對荒野的無盡追尋,逐漸轉向如今被稱為後自然,現代性荒原的持續性解構。」
儘管受過同樣的科學訓練,瀚嶢顯然比我花了更多心力去探索自然在科學視角外的可能面貌。完全不同於我對溼地生態預設的想像,瀚嶢介紹的知本溼地是一個「河流的溼地,部落的溼地,產業政策的溼地,更是一個想像的溼地」。當知本溪改變了河道,卑南族人在舊河道開始野耕,當外來的荷蘭人獵捕著草叢裡的鹿,知本溪第一次響起槍聲,如今,當候鳥來訪,來自臺灣各地的旅人與訪客帶著望遠鏡來到知本溼地。人們就像知本溼地的一部分,在此地生活,或遷徙或經過。
瀚嶢致力於描寫一個有人的自然,並且試圖解構當代社會中自然一詞的現代性。
自工業革命以來,對於自然的詮釋,現代人類社會與傳統社會或遠古人類十分不同。人們與自然的相對位置從早期受制於自然,內含於自然,到征服自然,用獨立於自然的第三者觀點去分析自然的構成與運行。甚而,隨著現代環境主義興起,自然被部分人士視為保護的對象,心靈寄託的純然荒野。保護自然是人類的一種道德義務。
我們是從什麼時候開始忘記了自己也是自然的一分子?我在心裡問著自己。
在類似日記式文體的絮語裡,瀚嶢藉由《沒口之河》試圖將人類重新放回自然之網中。他花了大量章節寫下卑南族部落人民自古至今,和其他民族、部落間的交流,以及他們創造、維持與利用知本溼地的形式。
也因此,讀《沒口之河》的時候,我常有一種感覺,瀚嶢似乎把人也當成了一種生物來觀察、描述並且記錄。藉由回溯在地居民繁殖、遷入遷出的歷史,瀚嶢彷彿再次使用了撰寫碩士論文的技巧,推論出知本溼地環境的動態變化,前世今生。
人類似乎都忽略了自己是自然的一分子
有意思的是,藉由梳理這些人與人,人與動植物間的相互關係,一個鮮活的溼地生態系誕生了。所謂生態系,係指一個由生物群落及其環境間交互作用所構成的自然系統。生態系的特色是具有自我運行的功能性,其某種程度上是靠著系統內各類生物間競爭的交互作用所維繫。生態系靠著生物間對資源的競爭來確保平衡,最終幾乎可以自給自足,使得大部分的物質在內部循環使用。
一個生態系一旦失去自我運行的功能,也就宣告滅亡。在《沒口之河》中,我辨識出許多人類與生物間的競逐,譬如人們跟象草爭地,跟火刺木爭奪河岸的使用,雖然彼此各有勝負,但正是這些交互作用,構成了知本溼地以及生態系自我運行的機制。然而,度假園區或是光電園區的構建卻不是。這些建設都是人類再次選擇將己身視為自然之外的異物的一種宣告 (雖然這在現代人類社會裡並不是什麼新鮮事)。因為,當人類不再同溼地生物競爭,而是選擇獨占當下所有的資源,知本溼地便不再是一個生態系,而是一處人類盤據的新領地。
我們得明白,至今,歷史上從未出現任何永久存在的人類領地。這意味著,人類一旦驅逐其他物種,事實上也等於驅逐了自己。於是,現代人只能不斷地向著荒野尋找新的領地,抑或向荒野尋求心靈的庇護。不論哪種方式,人類似乎都忽略了自己是自然的一分子。
「有時我覺得,如果真還有所謂的自然,外於文化的自然,其實也就只存在我們的視野,與陌生他者的交界之處,只存在於那一薄膜,那一瞬間,突破未知的一瞬間。在那瞬間之後,他者就成為自己,自然就成為文化。」
《沒口之河》對我來說是一個意外之外的自然書寫作品。如果說,生命科學的論文定位了人類在地球億萬物種中的位置,那麼自然書寫則試圖記錄了人與環境和其他物種間的關係。回顧我回憶中瀚嶢對自然的探索,他在專注觀察其他物種的同時,也花費同樣的專注在人類這個物種。在碩士論文中,他提到保育,而在《沒口之河》這本書裡,他也許想說的是,一個充滿人的自然,原本就是一件再自然不過的事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