搬家前一年,我種活了絲絨般的特殊種玫瑰,花瓣厚實、深紅近黑,盛開有整個手掌大小,每隔幾天要替它沖洗枝葉上攀著的汙塵、蟲卵甚至蛛絲,那些混著塵垢的游移份子貼著嫩葉掐著花蒂,使許多花苞來不及長大盛放,不知是從大肚山電廠那頭隨我下班來的,或是附近忽然暴增、過分喧擾的工地裡隨風輕浮而來。
人在時空中行旅一生,心會選擇適合它棲息的地方,不完美,卻填補了生活,想時光慢慢沉澱它為懷鄉之境,像白水煮茶潤過舌尖的一抹輕鬆。選個地點釀造歲月的氣息,比如劉書甫逛遍台中舊城的老滋味、焦桐吃出台北人的牛肉麵街、韓良露字留大稻埕的盛世繁華,記憶終成好味,勾引心頭念念不忘的少時澀戀,便是文字長養於時代的苗,一眼驚鴻寫盡參天。如果可以,我也想帶寡母住在一個這樣的地方,歷史記憶融入舌尖,精神足跡藏在筆下,實現那句「境隨心轉」──我棲息,在我默許的城境,我構建的心象網絡。
38歲第三次搬遷,從台中大里搬到市中心北區,想為「家」多添些想像,放下清末水路商榮一時的大里杙,選個把生活場域概念化的地方。「現在我家是植物園和博物館」,其實是指植物園後面安靜的忠太園道往忠明路、太原櫻花道方向,短短一公里看進文化與親子,循路蔓延的綠意穿過城區,像平地森林覆蓋一時頹落的印象。這隅城區有最熱鬧的一中、中國醫商圈,也有無盡蕭條的天津商圈,無論它曾經是怎樣意氣風發,如今都受疫病肆虐,只能星光四散在巷弄中的網路名店。
…………………………………………………………………………………………………………
剛搬來時,我透過網路側記和google散步走訪鄰里風景,陌生中解消了以往座標日常的方式,改隨喜好、聚落、社群這些抽象的概念,繪出屬於自己的尋寶圖。在舊中區地方創生,社團選了鈴蘭花為街道的重生命名,說是因為日治時「鈴蘭」那條街代表最熱鬧的地方,花語也有幸福的意思。在北區有植物園,偌大的蝴蝶雕像乘載整個園區的繁盛扶疏,熱帶植林和比鄰而居的科博館恐龍、化石守著一方綠野。我的google散步以植物園為核心,除了畫上路徑經緯幫助認知,小圖示則串起區域中的陶藝、茶舍、畫室、藝術拍賣、音樂教室、手作花店…,自得其樂建構藝文小眾「書同文、車同軌」的網頻,略過與鬧市相比簡直像Android和Apple大相逕庭的細節,以便能智慧生活──自以為smart的整合融入、連結藝術語言,把鄰居濃淡皆宜的送作堆、堆在一張圖上。這個世代數位環境能預先查知你要去的地方、想見的人、有興趣的故事,我輩習以為常,事先放大它的歷史脈絡與相關性,在微觀的世界透視一切穿越古今,網民和而不同、世界大同。
搬家就是行旅,換了生活場域,那種呼吸膚觸往來慣習都微微改變的新,給了舊日子不一樣的趣味。原有的日常習慣都得先斷片、再重拍,樓上種龜背芋熱情的小蔡換成養二層樓高琴葉榕的老范,巷口的蛋餅阿姨換成留英歸來創業的連鎖早餐。年份足夠的市中心除了高密度人口,往往小巷弄與三線道並存,街廓彎度變大,偶遇不知來人,步行直徑變長,點到點漫遊的空間增多,耽留發酵人情的時間卻愈短。城市的節奏本來就和外緣區不同,當街坊從熱炒小吃變成了個性店、藝品店,向小販討教菜色鹹香時大火歡快的高度音聲,自然而然就變成揉進白牆美玉、墨色生暖的觀展模式。搬遷以後,當期藝品拍賣價格,或今日店鋪使了哪家的陶壺映襯這季清冽好茶,不疾不徐地浸潤了生活另一面,即便我和母親兩人都有急性子、熱愛飲食酣暢之樂,城市自帶禮貌距離與保持依時處順的彈性,也有不衝突、不狎膩,剛好的舒服。
白日裡,人群依相似的節奏與車流上班、下班,疫情後我們在網路一起上班、下班,要不是冷氣吹頹了桌上的瑪格麗特盆花、長出白菌,電費帳單提醒溫室效應與大肚山外的發電廠之爭,日子幾乎完全忘記了環境限制,斗室裡人人都活成一個IP,後頭跟一串數據,紀錄著開機、打卡、電郵、通訊、社交軟體上業務問好的足跡。進階版的智慧IP可能是位AI同事,由遠端科技作業員操持智慧手臂,或記憶著作業員一切模式的仿生機器人執行公務,他們活脫脫就是你,深植生活的虛擬神經使你也能變成虛擬辦公室裡任何一個想成為的角色、機器人、貓狗或女神,一邊工作,苦中作樂或享受返老還童!

………………………………………………………………………………………………………………
疫情年代搬家竟然能這麼超現實,生活像電腦組件改版升級,環境記憶體得格式化,「從前」只剩一小部分收藏,而為了防疫的遠端職場實驗在每個角落發生。如果我想論證虛擬世界中「區隔」的概念是實際存在的,就像在同個網域中說每個人對同一區地理所講述的風貌不同,對同一份資料解讀的重點不同,對同一JPG檔能接收到的感性不同,但我們完全能夠在Android和Apple上不同的系統往一致的結果,或是從一樣的生活需求衍生不一樣的選擇。只是,Android和Apple都不支援自家上一代系統產品,消費文化的代代更新就是為了取代,對上一代來說,它(他)的世界就運轉到硬體完全無法支援系統運轉、壞了為止。母親對於生活的變化也只有接球的份,她的世代長養自稻田與河渠,金黃色的浪裹住米白色的豐足,數十年間從操煩一家溫飽的勞苦迎向製造為王的狂潮,從未想過多年後生產線金雞母會被扣上汙染、耗能、金屬霸權的帽子,而設計創價、產業轉型、虛實融合這些新詞會如潮水淹過了她們「台灣錢淹腳目」的世代。
環境變了,日子也得變,不光是母親這樣感受。小時候都市與農村的界限不明顯,從家到學校一路就能經過牛隻悠閒散步的水圳、公車路牌旁的麥當勞與外資工業大廠,青年時我對「自己的家」滿是嚮往,有一處自由配置的屋宇、滿牆滿廳的讀冊,放置人生尚未發生的美夢、荒謬、理型、慾望,放滿屋子裡存在主義構成的「我在」,或貸款棲身形制勞苦的「不在」。20來歲用青年貸款磨了16年,看周邊良田成鐵皮,鐵皮成工地,深掘地基的機具震動窗櫺取代鳥鳴,路旁空地劃上了白線、再轉為紅,最終一位難求無車可棲。16年也是在數百人社區耕耘的日子,從鄰居小妹長成社區委員,才熬出熟悉和安穩,城市發展和生涯突破的鳴聲又催促起來。好不容易啊!亭臺換下幾棵破壞地表的樹種,雞蛋花漸漸長成人高,我種得一畦各有名號的花藥蟲魚以為要安居終老,卻得捨下炒作跌宕的數字和建商工誤的塵囂而去。去哪裡?
…………………………………………………………………………………………………………

搬家前一年,我種活了絲絨般的特殊種玫瑰,花瓣厚實、深紅近黑,盛開有整個手掌大小,每隔幾天要替它沖洗枝葉上攀著的汙塵、蟲卵甚至蛛絲,那些混著塵垢的游移份子貼著嫩葉掐著花蒂,使許多花苞來不及長大盛放,不知是從大肚山電廠那頭隨我下班來的,或是附近忽然暴增、過分喧擾的工地裡隨風輕浮而來。短短一年時間,同一條街開出三個工地、無數張買賣廣告上了牆板,房屋價格飆漲雙倍,一路蔓延到舊工業區、軟體園區附近,本來失修空屋、凶宅的拋售價竟也逼近1.5倍。某個清晨,地方媒體用極小篇幅揭示道路盡頭工地忽然拉起整片封鎖條的原因:地層下陷、鄰居抗議,責任正在釐清。那路段臨溪、靠橋頭,工地兩邊高低差目測近二百多公尺,我記得研究生時期熱愛田調的同學說橋下有活冷泉,古早時期很多浣衣婦、戲水民眾活動,還能想像水鳥飛來澗上,婦人濯足童稚踢水。
多年後冷泉雖然湮於荒煙蔓草,但橋上還有一座石獅像,註記著清末霧峰林朝棟奉命修城牆、包工程,其後不得已率精兵北漂參與戰事,使城牆未果的遺跡。從橋頭石像起數百公尺遠是指定文化資產菸葉廠,不定時噴黑煙通通氣,氣氣大樓曬衣被的住民,菸葉廠斜對面是人稱活菩薩雪盧老人李炳楠行醫施教的遺址菩提醫院,再往南是林爽文逃亡足跡,然後靠近霧峰林家周邊的幾個特色地點。就這麼一段距離、兩年時間,房市忽然鶻起,地表增建圓塔停車場,遺跡毀滅於翻修陸橋,菸葉廠改建提案也擱置,當年意氣風發開樟撫藩的棟軍,甚至橋下浣衣戲水的俗民歌謠,均已無人記識,我決定搬出住了多年、處在預備工地群中的大樓,捨得盛開的玫瑰都被母親零星分送,只剩下扣除房貸與通膨後所剩無幾的餘款,往市中心第三個定居地點而來。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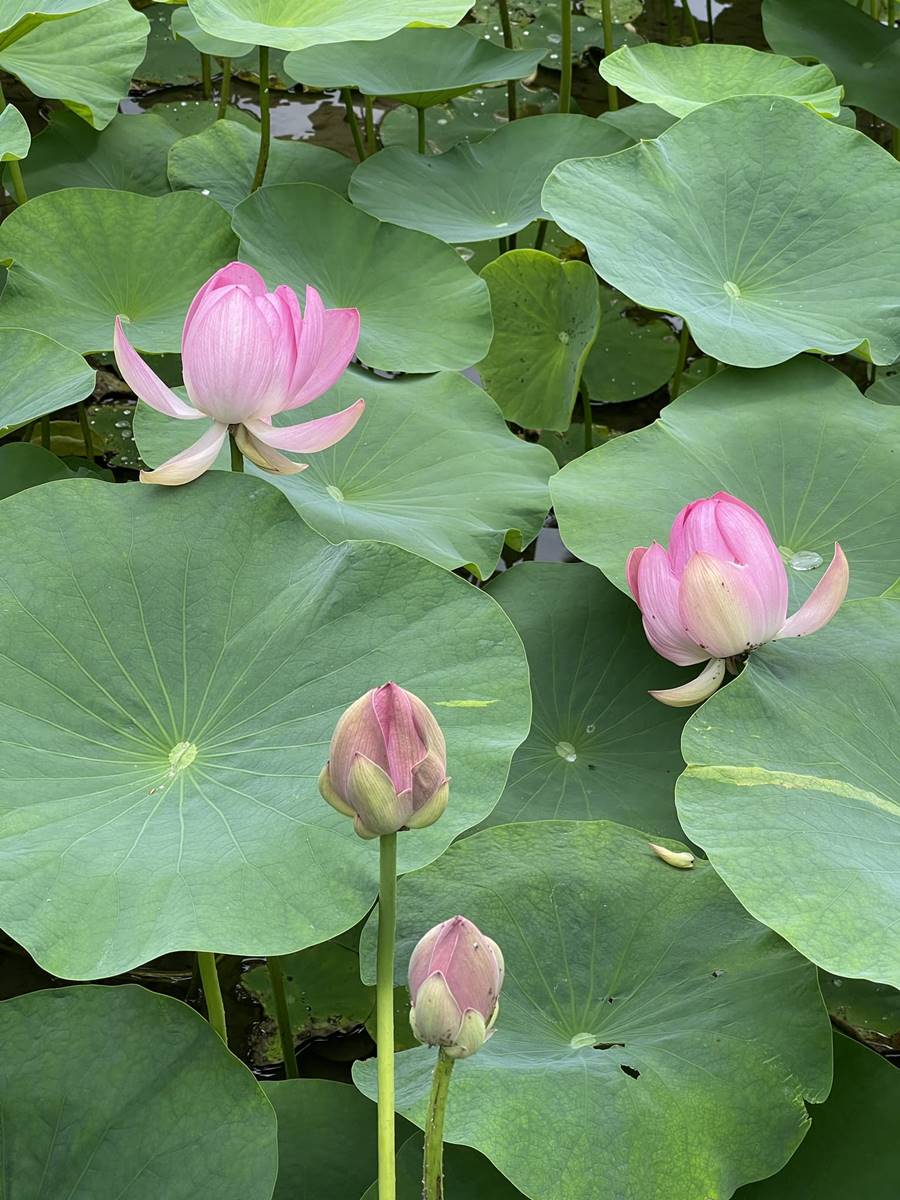
38歲中年,浪潮下捨了第一棟自己買的屋子,擱下整個陽台的蓮花與玫瑰,告別被歷史覆寫的大里搬到博物館和植物園附近,卻覺得城市經緯生動起來,彷彿沿著植物園道路發散出的路徑是佈滿氧氣的筋血紋理,我來,便急著想多看它孵育出的街廓,能不能以藝術在巷弄間牽起新線索,妝點餘存風韻。少年時許願要跨出再跨出這世界,如今在老邁城區被歲月和網際網絡撐架、模擬的神經元構成另一番視野:無論個體「我」在哪,都是連結世界的其中一個端點,無論我們看向何處,以google散步或進資料庫點讀文獻,所在環境的縱深不只是歷史或地貌、住民與商店,對於環境的真實感受,不等同對於真實環境的感受,我們共同居住在一個可以關機的世界,所以有無限擴張的土地、任何想要的臉孔、隨時增減的評價足跡;我們也共同居住,在一個已經無法重新開機的世界,呼吸以落塵和病毒不知所從來,觀看著別人購買無限擴張的土地,不敢問新的機會在哪裡,卻幻想星際殖民。
欸!未來我們都是童話裡的小王子,玫瑰在外星球上等的太久,傑克都已除掉巨人的看守,伺服器還擺著一隻齧齒羊守候你的旅行。青年時想奔逃的那個擁有綠野河堤的城市,老人拿起花鋤勞動,或大肚山紅土夕日襯臨海用愛發電的場景,或地圖上還堪百年的榮家棲族之處,終究千金難買了,剩心象城境,點擊連結展開史地;有花鳥蟲魚,轉生應猶在,在我存檔地圖上的經緯、資料庫裡的JPG、牆上掛軸未拍賣的風景。植物園是我所能移居的雨林,想像枝葉過風喃喃囈語,攀天的寂寞登樹冠之上,為王子守著玻璃城、替歷史記著起落,陪伴城間的人們呼吸、幻化,於網域相連之無涯。(本文為2022建蓁環境文學獎入圍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