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們眼中的「洪水」,其實是河流正在呼吸。當洪水週期性地淹沒整個泛濫平原時,猶如河流舒張肺部。一呼一吸之間,大量有機質和微生物隨著河水漫延,孵育植物、吸引魚群、繼而招來鳥類和哺乳動物,最後才有智人的身影。洪水因此不是毀滅,而是生態繁盛的前提。
當我們談論河流時,我們在討論什麼呢?
歷史課本常告訴我們,人類文明的誕生總與大河相依:埃及文明與尼羅河、兩河流域文明與底格里斯、幼發拉底河,當然,還有我們耳熟能詳的黃河文明。然而,河流帶來的不僅是穩定水源與肥沃土壤,也帶來突如其來的洪患。於是,人們觀察、記錄、乃至於企圖治理河流。當環境史在一九七○年代興起時,河流毫不意外地成為研究焦點。以中國為例,黃河相關的研究成果豐碩,[1]臺灣則有《濁水溪三百年:歷史.社會.環境》、《尋溯:與曾文溪的百年對話》、《島都之河:匯流與共生,淡水河與臺北的百年互動》等奠基之作。
但是,這些作品,幾乎都從人類視角出發,訴說人與河流的長期互動,卻少有真正關於「河流自身」的故事。
究竟,什麼是「河流」呢?
或許有人會回答:不就是水嗎?如果有人提到具體的河流名字,例如淡水河,我們腦中浮現的,往往是一條地圖上的實線:有確切的起點、有粗壯的主幹、有細密的支流,然後一切終歸入海。
但是,斯科特搖搖頭。他指出,河流遠比我們想像得更加複雜,包含流水、淤泥、黏土和砂礫,以及所有依附這些元素而生的生命形式群聚。正如一棵大樹不只是樹幹,還有枝葉、根系、果實等等,每個部分匯聚起來,才會形成一個整體——「樹」。河流亦然。於是,為了回答「什麼是『河流』」這個看似簡單卻關鍵的問題,他在生命最後幾年寫下了《讚美洪水》。
三種河流敘事
熟悉斯科特過往研究的人,或許會對他的新嘗試感到意外。畢竟他長期關注的是東南亞農民如何抵抗國家權力,以「人」為核心。但在這裡,主角換成了「河流」,人類反而退居其次。只是,那條潛伏的主旋律——弱者如何與強權抗衡——依舊流動其間。
在《讚美洪水》中,他提出三種河流敘事。我們可以想像自己正乘著船,自上游而下,依次經過不同河段。每一段皆展現特殊風景。
第一種是非人類中心的河流敘事。斯科特要求我們,重新調整觀察的時間尺度,不再以人類的一生為單位,而是拉長至千年、萬年。如此一來,方能清楚看見每一條如今貌似穩定的河流,可能因地震、火山爆發、氣候變遷等外在因素而改道,但更多時候,是憑自己力量前行,從山上到山下,沖刷出新河道,開闢新的泛濫平原,無數次地重塑自己。移動,才是河流的本質。
其中最關鍵的移動,就是洪水脈動。在人們眼中的「洪水」,其實是河流正在呼吸。當洪水週期性地淹沒整個泛濫平原時,猶如河流舒張肺部。一呼一吸之間,大量有機質和微生物隨著河水漫延,孵育植物、吸引魚群、繼而招來鳥類和哺乳動物,最後才有智人的身影。洪水因此不是毀滅,而是生態繁盛的前提。
為了使讀者一窺河流的生物多樣性,斯科特甚至在第五章中,讓緬甸伊洛瓦底江的眾多非人物種發聲,抗議人類的過度活動使其生存日益艱難。我讀到這一章時,不禁莞爾,覺得他以帶有玩心的方式,與近年「more-than-human(不只是人)」的環境人文思潮相呼應:既打破物種位階的迷思,也提醒我們,人類絕非唯一的行動者。不過,斯科特在此仍集中於動植物,尚未觸及水與石等非生命物質。若納入它們,將能看見更複雜的多物種權力關係。[2]
第二種是「納」的敘事。藉由緬甸在地協同研究者的田調成果,斯科特介紹了伊洛瓦底江流域各種尊稱為「納」的河靈。這些「納」生前是凡人,有男有女,死後以「納」之姿施展不同能力,或造成山崩與洪水,或庇佑信徒捕魚和航行。可惜的是,因政治與疫情的限制,他無法親自深入調查「納」,使這段極具在地特色的河流敘事草草收尾。
第三種是以人類為中心的河流敘事。在《國家的視角》中,他曾批判國家如何透過「標準化」與「可辨識度」的手段,將原本複雜多樣的社會與自然,壓縮成便於統治的樣態。於是,農業推行單一作物,林業專注培育標準樹。但在國家眼中,最難以馴服、最需要嚴加管束的,其實是放蕩不羈的河流。自十八世紀以降,政府倚仗土木工程科技,大刀闊斧地將河川改造為筆直的輸送帶。為了維持水流暢行,他們截彎取直河道、疏浚河床至整齊一致的高度,再築起一道道堤防,使河水奔流更快、流量更大,以避免淤積。
然而,這樣的治理,反而累積沉積物、抬升河床,也大幅加速水流。一旦雨量超標,或者水利設施失靈,就會催生更致命的洪患。他稱此為「醫源效應」——原本意在治療,卻讓病情惡化。換言之,治水之初已經同時埋下了致災的種子。
也正因如此,斯科特提醒我們,當今的水危機若真能稱之為「危機」,根源不在洪水,而在於獨尊以人為本位的單一敘事,抹消了原有的多元敘事。

與斯科特的相遇
讀完全書,我不禁回想起,自己第一次聽斯科特親口講述這些想法的場景。
那是二○一九年三月,我在哈佛大學擔任博士後研究員,剛剛展開我的中國河流環境史研究,桌上堆滿了從燕京圖書館借來的水利史著作。某日,主持哈佛亞洲環境史工作坊的張玲博士告訴我,斯科特要在波士頓學院演講,題目是「讚美洪水:河流與文明的研究」。於是,我興沖沖揣著《反穀》,一路搭地鐵從紅線到綠線終點的波士頓學院站。因為人生地不熟,我繞了好一陣子才找到講堂,最終仍遲到了幾分鐘。入場時,座無虛席,我只能靦腆地坐在第一排,卻因此與他面對面。
坦白說,我最初滿心疑惑:洪水有什麼值得「讚美」?在中國史書裡,洪水幾乎總是災厄的化身。可是,不到十分鐘,他讓我看見一幅生機勃勃的生態系景象。更重要的是,演講最後,他問了一句:「當一條河失去幾乎所有賦予它『河流之所以為河流』的特徵時,我們還能說它依舊是一條河嗎?」
那一刻,我彷彿遭到雷擊。

複數的人;異質的環境
回去後,我推倒既有認知,重新出發。返臺後,我甚至走入山林,並在因緣際會之下,與一群臺東Pasikau部落布農族人相識,隨他們上山、返回祖居地,學習與自然共處的智慧。這經驗徹底改變我的人生和研究方向。
其中之一,是我對「自然觀」的理解。雖然我是個駑鈍的學生,但慢慢地我也領會到,由於漢字沒有複數的表達方式,很容易讓人誤以為,彷彿只存在一種「自然」、一種「人」、一種「人與自然的關係」。但現實遠非如此。尤其原住民族(若暫且視為整體)的自然觀,便與非原民人群的看法天差地別;而在「原住民族」這個統稱下,各族群也因地域、氣候、歷史背景等差異,孕育出異質的環境經驗與觀念。
然而,自日治以降,臺灣逐步以西方科學知識為尊,相對地卻邊緣化「原住民族知識」。因為這些知識常被視為「傳統」知識的同義詞,而「傳統」意味著「靜態」與「過去」,遂被對立於「進步」、「現代」科學。而且,西方科學知識自認其原則放諸四海皆準,因而漠視在地知識的產生脈絡與價值。這種偏見,甚至長期主導公部門的政策制定。
幸好,近年來,由於學者和在地族人的努力,致力於洗清「原住民生態知識」的污名,推動原住民知識與現代科學的對話和合作,並進一步引入政策實踐。
例如,泰雅族出身的地理學者官大偉,透過口述歷史、地名採集與地圖建置等方法,展現河流對馬里光(Mrqwang)流域泰雅族人的多重意義:它是部落間共享的語言之流、血緣之流、資源之流,也是族人遊戲、學習與回憶的場所。[3]這些豐富的河流知識,提醒我們:臺灣的河流史,不該只有一種聲音。
我們必須納入更多元的河流敘事,無論是原住民族的經驗,還是非人生物的聲音。唯有如此,臺灣的河流史才能如同河流本身——不斷流動,承載眾多生命,展現豐富而異質的面貌。這也正是《讚美洪水》帶給我們最深的啟發:當我們失去了對河流的想像,我們同時失去了真正理解河流的可能。(本文轉載自《讚美洪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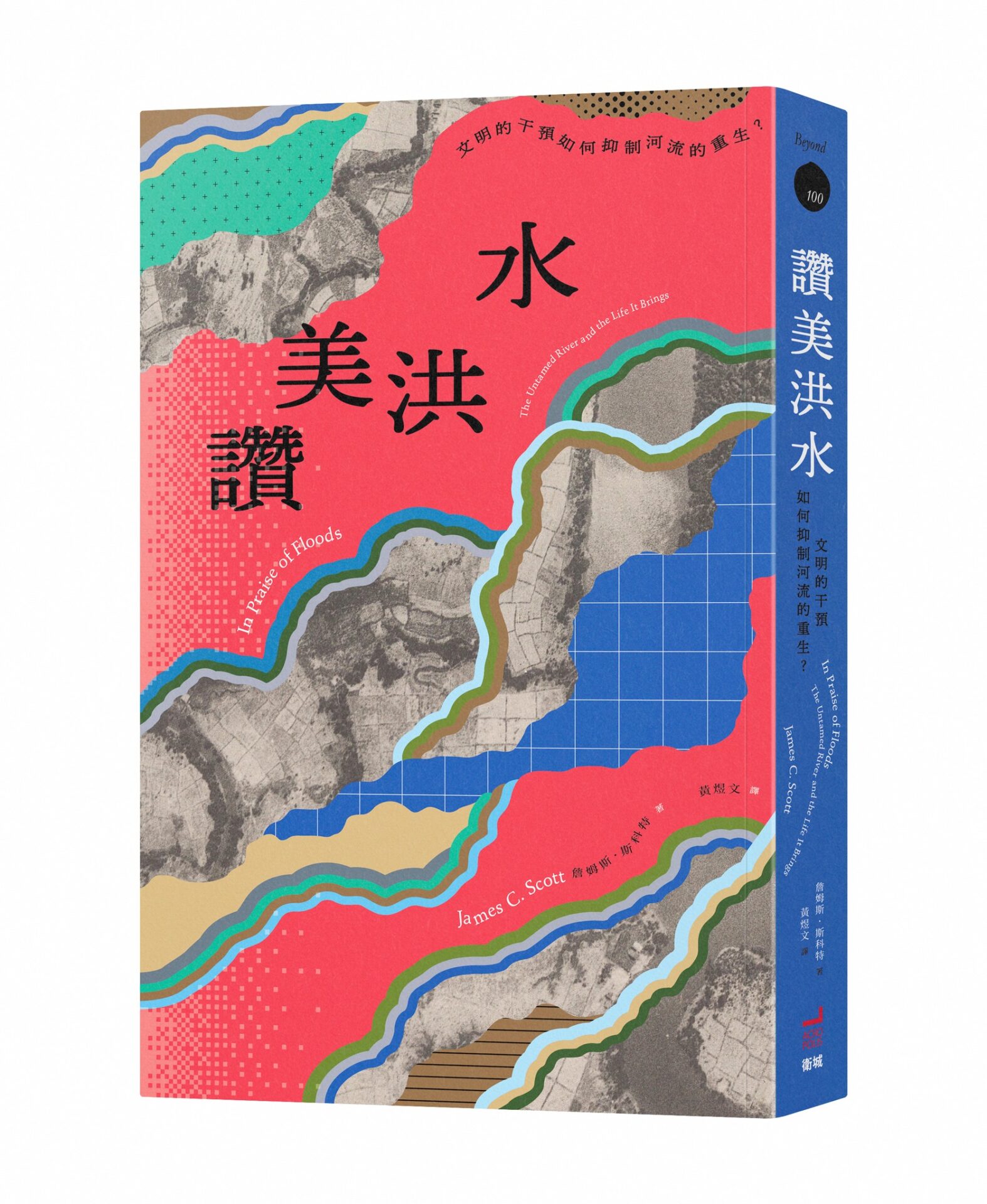
書名:《讚美洪水》
作者:詹姆斯.斯科特( James C. Scott)
出版社:衛城出版
出版日期:2025/09/24
[1] 有興趣的讀者,可以參考以下書目: Hsu, Hui-Lin. When the Yellow River Floods: Water, Technology, and Nation-Building in Early Twentieth-Century Chinese Literature.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24. Mostern, Ruth. The Yellow River: A Natural and Unnatural History.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21. Muscolino, Micah S. The Ecology of War in China: Henan Province, the Yellow River, and Beyond, 1938–195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4. Pietz, David A. The Yellow River: The Problem of Water in Modern China.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5. Zhang, Ling. The River, the Plain, and the State: An Environmental Drama in Northern Song China, 1048–1128.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6. Dodgen, Randall A. Controlling the Dragon: Confucian Engineers and the Yellow River in the Late Imperial China.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01.
[2] 蔡晏霖,〈動保vs.野保?淺談多物種研究〉,收入王麒愷編,《流動的界域:從在地、跨域到多物種》,新竹:國立陽明交通大學出版社,2024,頁74。
[3] 官大偉,〈原住民生態知識與流域治理-以泰雅族Mrqwang群之人河關係為例〉,《地理學報》,70(2013),頁69-1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