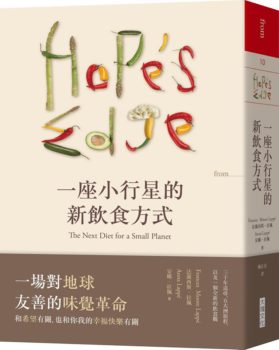當我發現肉食以外的豐富及多樣性以後,我為五花八門的蔬果與有機食品著迷,有些食物的名稱我連聽都沒聽過,更別說是曉得如何烹煮。儘管如此,我愛上了這些新朋友,並沉浸在 令人驚喜的滋味中。
[dropcap]穿[/dropcap]過帕尼同家的廚房進入用餐大廳,撲鼻而來的是打清早便開始準備的餐食,金黃色的洋 蔥、捲葉菊苣和紫蘆筍映入眼簾。不一會兒的功夫,我就被迷得團團轉。
我不由想起第一次被食物「誘惑」的情形,那次經驗喚醒了我的感官。當時是六O年代末 (別忘了以前和現在是天壤之別),除了我媽以外,家庭主婦只有在端得出肉時才敢稱之為「正 餐」。不過在我家只要有鬆餅粉、果凍粉和大鍋菜,就算是一頓不折不扣的大餐了。

當我發現肉食以外的豐富及多樣性以後,我為五花八門的蔬果與有機食品著迷,有些食物的名稱我連聽都沒聽過,更別說是曉得如何烹煮。儘管如此,我愛上了這些新朋友,並沉浸在 令人驚喜的滋味中。我發現紅色與黃色扁豆、紅豆、稷和大麥、布格麥和蕎麥等。以前我老是 把種子看成鳥飼料,現在我會將各類種子烘烤後,灑在每一道鍾愛的菜餚上。
我將食譜當做小說來閱讀,想像將大麥、蘑菇和詩蘿組合起來,會迸出什麼驚人的美味; 才一晃眼的功夫,肉和馬鈴薯不再讓人食指大動,它們和蔬果比起來,反倒成了單調又死氣沉沉的東西。我發現蔬果不但美味,而且對地球與人體健康最有益處,真可說是「集三千好處於一身」呀!
要從雜草叢生、貧瘠的都市惡土中把菜園建起來
一九九三年,當地報紙上登載一篇報導,艾麗斯用不以為然的語氣,批評馬丁路德國王二世中學的校地使用情形;國王中學距離帕尼斯家餐廰僅幾街之遙,該校校長尼爾.史密斯(Neil Smith)看到這篇報導時相當不悅。「於是我寫了一張短箋給艾麗斯,她回電邀請我前去午餐, 」在和艾麗斯碰面幾天以後,我們和尼爾在他的辦公室外頭閒聊,他回想當時情形:「在用餐中, 她提出了『食用校園』的概念。」
真是個偉大的主意:「學生先建座菜園,在茶園種些食材,收成後洗洗切切,最後煮成一 道道菜給彼此享用。」艾麗斯解釋給我們聽。「無論是數學、科學還是英文課,學童將園子裡的 工作和正課結合在一起。」
「艾麗斯的步調太快了,」尼爾把先前和艾麗斯的談話內容轉述給我們聽。「她一下就跳到第十步;她希望說到做到,只不過…」他逕自說著,搖了搖頭:「我跟她說我們得從第一步開 始,首先要從雜草叢生、貧瘠的都市惡土中把菜園建起來。」
我們在冷冽刺骨的早春來到國王中學,學校正巧在放學,這時我們逮到一位小男生,便趁 機會問道:「你們今天煮什麼菜呀?」食用校園的總管米得蕾.霍華(Mildred Howard)大刺刺地笑著,讓我們感覺她對自己和學童的傑作相當得意。
「做餡餅,」他解釋道:「我擀麵團,其他人把胡蘿蔔、馬鈴薯和洋蔥塞進去。」我們問他餡餅好不好吃,他齜牙咧嘴的笑著,用力地點了點頭。
米得蕾陪同我們走過鋪著柏油、黑壓壓的運動場,有群學生正在打籃球。我們聽見叫嚷聲和遠方的號笛,還有正在鳴響的學校鐘聲。擁擠的速簡餐廳,此刻正趕著在上課前賣出最後一口食物。
接著一行人來到菜園。進入這裡的感覺像是到了不同時區,或者說是不同緯度,由於這裡被茂密的樹木和玉米莖部遮蔽,因此比較涼爽,空氣中夾雜一股不同的氣味。鳥兒的鳴唱就像繭殼般將園子團團包圍,隔絕了都市的喧囂。
菜園確實改變了孩子在世界上的存在方式
這裡見不到排列整齊的作物。玉米和莧菜、胡蘿蔔和萵苣相互交錯,大小樹枝捲曲纏繞成 林蔭和圍籬,間或穿插著藤蔓,更添神奇特質。我每踏出一步,就越來越難以相信,不過是幾年前,這裡不但是塊荒地,也是街坊鄰居的眼中釘。
手繪的木製告示牌告訴我們,什麼東西種在哪兒。其中一塊牌子上寫著:「Mashua」,當我 露出困惑不知所措的神情時,才曉得原來這是一種瀕臨絕種、古印加帝國的塊莖植物。這時米得蕾在一株與我下巴同高的朝鮮薊前停下,切了三片朝鮮薊拿來做晚餐。「今天晚上我打算用帕瑪森起司和奶油來烹煮這些朝鮮薊。」在她誘惑我的同時,我努力回想是否曾品嘗過剛摘下的朝鮮薊。

早春時刻結實緊繫,說明了土壤肥沃的程度,因此當米得蕾說,學童會定期在園子施放有機堆肥時,我們一點也不意外。從園子誕生以來,孩子們在五年內已經用掉兩百公噸的有機肥了。
顯然這些年來,艾麗斯和 國王中學早已跨越「第一步」的階段。
有位男士興高采烈地正在講話,被太陽曬成棕色的皮膚再加上太陽眼鏡,使他看起來比較 像一位救生員,而不是老師兼菜園管理者。我們猶豫著要不要打斷他的談話。
「我不會給學生很多指導,」當我們問到大衛·霍金斯(David Hawkins)的角色時,他用
濃重的英國腔解釋。「我讓孩子自己玩,自己試驗,從觀察中學習。比方說,我不教他們如何使用鋤頭,我先示範一遍以後,再讓他們嘗試,直到技巧純熟為止。」
「我們讓孩子勝任每一件工作。我們不用木材,只用樹枝和藤蔓,這樣學生就能把每件事情做好。」當我們環視四周用樹枝纏繞而成的拱門和圍籬,發現只要運用大自然的創造物,似乎不太可能做出醜陋的東西來。
大衛和米得蕾均澄清,茶園經驗對學童的影響可能不是立即性,甚至是無法明確衡量,不 過影響力卻真實存在。
「世事難料,」大衛說,他曾在倫敦和一群被普通學校拒收的孩子相處過好幾年。「去年, 有個小傢伙讓我束手無策;我想,與其讓他推著手推車穿過園子,又惹了一堆麻煩,還是不要也罷。可是這個禮拜,他母親到學校來,跟我說菜園改變了她兒子。」
「我當然沒有和她爭辯,」大衛笑著說,「於是她又說:『以前他一放學回家就打電動,現在他會告訴我菜園裡發生的事,像是種什麼植物啦,等等之類的。』」
「我本來不相信,」大衛強調,「菜園會影響孩子的內心世界,因為沒有人能針對這一點做測試。可是菜園確實改變了孩子在世界上的存在方式,因為他們知道自己建造了這裡。這類體 驗真是打著燈籠也找不到。」
他們在這裡可以做自己。他們可以發出噪音
我們在閒逛之餘,心情逐漸豁然開朗;的確這不只是座茶園,還兼具更深的意義,這也是孩子的想像世界。我們身後的教室,是用茉莉花纏繞著樹枝建造而成,座椅則是用一捆捆乾草紮的;我們面前有個用乾泥巴堆成的小山,靠近底部還有一些細枝從土堆裡凸出來。一經解釋 我們才恍然大悟,原來孩子蓋了一間大到可以鑽進去的鳥巢。
「從情感上來說,許多孩子的內心是相當封閉的,」大衛說,「不過,他們在這裡可以做自己。他們可以發出噪音。你們應該聽聽其中一個女孩子,她模仿的鴿子叫聲真是維妙維肖!」
幾天後我們又回來參觀烹飪課,這次負責接待的是伊恩·奧斯特拉斯—康斯特保 (Ene
Osterraas-Constable),他是「食用校園」的十項全能,身兼對外與媒體聯繫、攝影、專案經理以及啦啦隊等職。此刻孩子們正在廚房,忙著把看似蕃茄,小小的綠色墨西哥酸漿 (tomatillo)(譯 註:和蕃茄同科,又稱為粘果酸漿,原產墨西哥,以食用未成熟的酸果為主,多半用來製 作莎莎醬)裝進大碗,再過一下子,這些酸漿會被製成莎莎醬 (譯註:用來沾玉米片的醬汁)。
我想起美國人消耗的蔬果,有超過半數是三樣東西冰山高、馬鈴薯和蕃茄罐頭;這時伊恩笑著說:「孩子們用園裡的蔬菜做的第一道食物是燉甘藍菜;有幾位老師把我們拉到一 邊,輕聲問道:『我們都同意菜園的構想很棒,可是真的不能不吃嗎?』」我和安娜也笑了,心想燉甘藍菜肯定不能拿來作為「誘餌」,讓孩子喜歡菜園裡的新鮮食物。
「老師都好緊張,可是小傢伙卻愛死了,」伊恩說。「甘藍菜是現摘的,所以吃起來不會苦。 事實上,我還看見有個小男生,把五片葉子藏在餐巾下,以便稍後享用。」
「最重大的成就,是每天讓不同的孩子明白,我們辦到了,而且不但做得很好,心裡也充滿喜樂。我們現在在談論食物,這一點真是可喜可賀。」伊恩愉快地解釋。
『文化』是藉由餐桌傳給下一代
對艾麗斯和伊恩來說,料理、將食物盛入陶土盤再一同享用的過程,和栽培、除草與收成同樣具有教育意義。艾麗斯曾提醒我們:「『文化』是藉由餐桌傳給下一代,如果不能透過餐桌傳遞文化,或許文化將無從傳遞。如今大多數孩子很少有機會和家人同桌吃飯。」
「當然囉,我們會希望孩子利用用餐時間,說一些平時沒有機會說的話,」伊恩說。「有一 次我在午餐時經過一張餐桌,聽見一群男生正在說某人的頭被剁下來,流了很多血;當時我真的好失望,我以為他們在描述哪部恐怖電影的情節呢。後來又路過那裡的時候,才知道他們正在討論功課,那段時間他們正好讀到希臘神話。」
「『食用校園』讓我明白孩子才是主人翁;事實上,大人的成見,諸如孩子會做哪些事,以及願意做哪些事等,才是真正的障礙所在。」
從一通電話和一所學校裡的菜園開始,加上各路人馬合力發揚光大,終於贏得全社區的迴響。到一九九九年為止,當地的教育委員會表決通過,每所市立學校都要設置學生菜園;此外學校必須向當地農民採購食材並供應有機餐點。再過不久,學校課程就會納入整個食物生態學, 而且是由淺入深有計畫地進行。
安娜驚訝萬分。不到十五年前,她在附近的某公立學校就讀,回想當年「美好的一天」,就是當薯條沒有被炸得直滴油的時候。
學童正目睹園子裡每天、每季的生滅變化
我們不久後發現,「食用校園」是校區菜園的再現,而校區菜園正是一世紀前的校園基本配備。目前加州有五分之一的學校,將菜園作為教學場所,近年來全國則有數以千計的校區菜園, 如雨後春筍般地崛起。
我和安娜對「食用校園」的瞭解越深入,就越常回歸到一個老問題:什麼阻礙改變?為什麼「每校一茶園」不被認為和體育一樣重要?事實上,校區菜園也曾一度被認為與教育無關。
「什麼使人裹足不前?」我拋出這問題後,艾麗斯連一秒鐘也沒猶豫。
「是害怕改變,」她說。「長久以來,教育灌輸我們,世界與生命具有某種恆常性,我們甚至不承認自己隨時會死。其它地方的文化,讓孩子從小就將改變視為人生的常態,」艾麗斯接著說。「他們在十幾歲的時候,就知道自己一定會經歷重大轉變,而且不同的生命階段有不同的變化,因為這就是人生。沒有一件事是固定不變的,如果試圖保持現狀,你只會感到震驚與失 望而已。因此人一定要懂得放下堅持。」
她說話的時候,我想像學童正目睹園子裡每天、每季的生滅變化。即使我一直鼓勵自己不斷改變,卻仍舊發現我對改變的恐懼,有部分是出自對永恆的迷思,而且我也已經被這種迷思同化,我以為一旦真正瞭解生命本質,我就會是穩定的,也就是不改變。可是艾麗斯提醒我們,問題不在如何戰勝改變,而是讓自己有信心面對改變,甚至是接受改變的到來。
聽來挺好的,可是迎接改變卻極富挑戰性,尤其是橫亙在眼前的,盡是地球面臨的巨大問題,從全球暖化到全球飢荒。這些問題讓人無力招架,因為實在是太沉重了。那麼,我們從何處尋找改變的原動力呢?
想也知道,我們很想一點一點解決,將問題切割成容易控制的小片段,再循序漸進。第一 章將這種企圖命名為「見樹不見林」;可是如果將問題拆解得支離破碎,並且忽略彼此間的相關性,那麼這種策略就不再管用,因為問題從一開始就是從片段與片段之間的相關性中製造出來的。
三十年前,先拆開來、再裝回去的模式,束縛了文化予人的想像空間,如今依舊如此,只不過正逐漸被新的世界觀所取代。
(本文轉載自《一座小行星的飲食方式》,小標為版刊編輯所加,照片亦為本刊所配。)
- 作者:法蘭西斯.拉佩,安娜.拉佩
- 原文作者:Frances Moore Lappé;Anna Lappé
- 譯者:陳正芬
- 出版社:大塊文化
- 出版日期:2020/02/27
- https://www.books.com.tw/products/0010850071?sloc=ma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