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本不吃牛的臺灣人,今日牛肉卻成為肉類消費的大宗,在飲食變遷的過程中,「沙茶菜餚」是否扮演關鍵的推手呢?從戰後初期到今天,歷經七十年左右的時間,為何沙茶醬成為臺灣人吃火鍋不可或缺的沾醬呢?又為何沙茶炒牛肉與牛肉爐受到許多臺灣人的青睞呢?
本書討論的「沙茶醬」是二次戰後,來自廣東地區的潮汕移民將「沙茶菜餚」(沙茶粉、沙茶醬及沙茶牛肉爐)帶到臺灣的產物。沙茶醬在今日臺灣社會相當普遍,但實際上「沙茶」其實是個「舶來品」,其身世可追溯至南洋的「沙嗲醬」(satay or sate)。
在南洋地區,居民習慣將醃漬過的烤肉串在一起,沾沙嗲醬食用,是一種常民小吃,其醬料成分包括研磨成粉的烤花生、薑黃、椰奶、棕櫚糖、南薑、小茴香、胡荽子、羅望子、檸檬汁、香茅、蔥、蒜與花椒等香料,慢火熬煮而成。
沙茶原來系出沙嗲
南洋「沙嗲」如何轉變為「沙茶」?關鍵在於潮汕移民,閩粵地區素有「僑鄉」之稱,耕地狹小且人口稠密,居民為了追尋更好的生活條件,離鄉背井乘船出洋,大多前往東南亞。根據《海外潮人的移民經驗》一書,潮人下南洋的首次高峰在清乾隆與嘉慶年間,第二次高峰在十九世紀中期,汕頭開港後興起「豬仔貿易」(契約華工),人口販子拐買潮汕華工至南洋等地。([1])當潮汕移民來到東南亞後,嚐到了當地的「沙嗲」飲食,濃厚香氣特別對味,當他們返回家鄉時,亦將「沙嗲」醬料帶回了潮汕地區並進行改良。
首先,考量乘船遠行,潮汕人以油炒方式延長醬料保存期限。其次,潮汕人擅長處理水產海鮮,因此烹製過程添加了蝦米和扁魚等魚貨乾品,並加上華人喜愛的五香、果粉、薑黃與陳皮等中藥。因此,沙茶醬的顏色偏深褐且海味重。([2])潮汕地區以沙茶入菜甚為普遍,例如沙茶牛肉粿(河粉)是潮汕人最喜愛的小吃,潮式撈麵也以沙茶醬調味。此外,潮汕當地盛產牛肉,牛肉丸與牛肉鍋也十分普遍,皆以沙茶佐味。([3])在此脈絡下,沙茶菜餚在潮汕地區逐漸成形。

潮汕地區的「沙茶」又如何傳入臺灣呢?其實潮汕人素有「東方猶太人」之稱,多數移居海外且善於經商,東南亞的暹羅(泰國)、安南(越南)與新加坡等地皆有潮汕人建立的會館公所,透過綿密的商業與社會網絡,潮汕人將中國的瓷器和藥材賣到海外,再將暹羅與安南的米、糖與香料進口至中國。([4])
在近代臺灣歷史脈絡,明清之際已有潮汕人來到臺灣,清代臺南建有「潮汕會館」,正殿供奉三山國王。([5])此外,清領時期福建巡撫丁日昌奏請朝廷在香港、汕頭、廈門等地設立招墾局,招募移民來臺開墾,當時在汕頭曾招募潮民兩千多人,以官輪船載至臺灣。([6])日治時期亦有不少「華僑」從中國來臺經商,當中不乏潮汕人士。([7])
臺灣從南到北 有潮汕人即有沙茶菜餚
然而,真正大批潮汕人移居臺灣的時間是二次戰後,他們跟隨國民黨軍隊來臺,面對新的生活環境,不少潮汕人選擇販賣原鄉熟悉的沙茶菜餚,畢竟華人著名的「三把刀」(剪刀、菜刀與剃頭刀)是在異鄉最容易生存的方式。爾後臺灣從北到南,只要有潮汕人聚集之處,多出現沙茶菜餚,包括沙茶麵、炒沙茶牛肉和沙茶牛肉爐,較著名的地區包括臺北的西門町與建成圓環一帶,高雄的哈瑪星和鹽埕區,此時沙茶醬的香味逐漸在寶島各地飄散開來。
今天大家對於「沙茶菜餚」(shacha cuisine)相當熟悉,但若回到戰後一九五○年代的臺灣社會,當時臺灣人對於沙茶醬不僅十分陌生,而且牛肉消費比例也甚低。從戰後初期到今天,歷經七十年左右的時間,為何沙茶醬成為臺灣人吃火鍋不可或缺的沾醬呢?又為何沙茶炒牛肉與牛肉爐受到許多臺灣人的青睞呢?
另一個有趣的問題是:傳統農業社會臺灣人不吃牛肉,今日牛肉卻成為肉類消費的大宗,在飲食變遷的過程中,「沙茶菜餚」是否扮演關鍵的推手呢?發源於南洋,經由潮汕人帶到臺灣的沙茶菜餚,不僅在臺灣落地生根,並由當地業者發揚光大,揚名海外,只要有華人居住的地區,就有沙茶醬的味道,沙茶醬的在地化也是非常有趣的議題。

如果你想瞭解沙茶飲食變遷的歷程,請繼續往下閱讀,本書將娓娓道來沙茶菜餚的有趣故事。
(轉載自《沙茶:戰後潮汕移民與臺灣飲食變遷》,主標與小標為本刊編輯所加。)
註解:
[1] 參閱巫秋玉,〈明清時期潮汕港口發展與潮人下南洋〉,收於李志賢主編,《海外潮人的移民經驗》(新加坡:八方文化企業,2003年),頁389~398。
[2] 訪談高雄市「可香潮菜館」第二代店主朱瑋生,2015年11月20日。
[3] 參閱潮汕歷史文化研究中心編,余文華著,《潮州菜與潮州筵席》(廣州:花城出版社,1999年),頁42;張新民,《潮汕味道》(廣州:中國廣州暨南大學,2012年),頁18~19;林貞標,《玩味潮汕》(廣州:中山大學出版社,2016年),頁32~55;知中,《關於火鍋的一切特集》(北京:中信出版集團,2019年),頁118~143。
[4] 潮汕人善於經商,例如蔡志祥的研究提到十九世紀潮汕商人建立了一個橫跨香港、新加坡、曼谷和汕頭的米穀貿易網絡,透過「聯號」的公司形式將泰國的米銷售到華南地區。參閱Choi, Chicheung,“Rice, Treaty Ports and the Chaozhou Chinese Lianhao Associate Companies: Construction of a South China-Hong Kong-Southeast Asia Commodity Network, 1850s-1930s” in Lin Yu-ju and Madeleine Zelin eds. Merchants Communities in Asia, 1600-1980 (London: Pickering & Chatto Ltd), pp. 53-77.
[5] 潮汕會館位於臺南市立人街三十號,由旅臺潮人楊允璽(廣東大埔)、林夢熊(廣東海陽)等潮商集資興建。潮汕會館正殿供奉三山國王,右殿為韓文公祠,左殿供奉媽祖、兩廣總督與廣東巡撫之牌位。會館專供潮汕商民留宿、聚會與促進商務之用。參閱周宗賢,〈臺灣會館的研究〉,《淡江學報》24期(1986年4月),頁243。
[6] 呂實強,《丁日昌與自強運動》(臺北市: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72年),頁292;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臺東州采訪冊》(臺北市:大通書局,1984年),頁42;謝紀康,〈丁日昌對臺灣防務的探討:以電報等洋務建設為例〉,《育達科大學報》22期(2010年3月),頁79~80。
[7]「華僑」是指在「臺民去就決定日」(1897年5月8日)以後來臺之中國大陸人。由於閩粵地區謀生困難,自古即有外移之傳統。日治時期臺灣工作機會多、工資高,且語言和風俗習慣與閩粵相似,再加上臺灣勞力不足,需由大陸勞工補充,因此吸引許多華僑來臺工作。日治初期臺灣各地已有華僑團體,例如廣東華僑分為粵東幫和潮州幫,各有私會亦合組公會。1901年大稻埕的廣東幫與潮州幫組織臺北公會,整頓商規。「臺灣中華會館」要到一九二三年才成立。參閱許雪姬,〈臺灣中華總會館成立前的「臺灣華僑」,1895~1927〉,《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20期(1991年6月),頁113~114、11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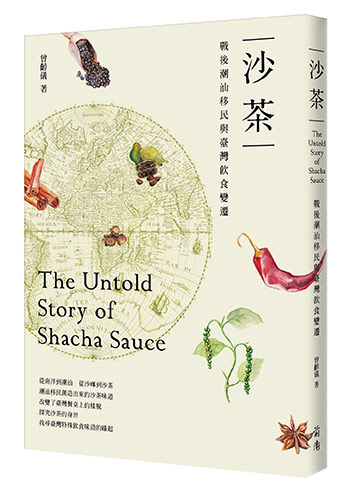
- 作者:曾齡儀
- 出版社:前衛
- 出版日期:2020/12/0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