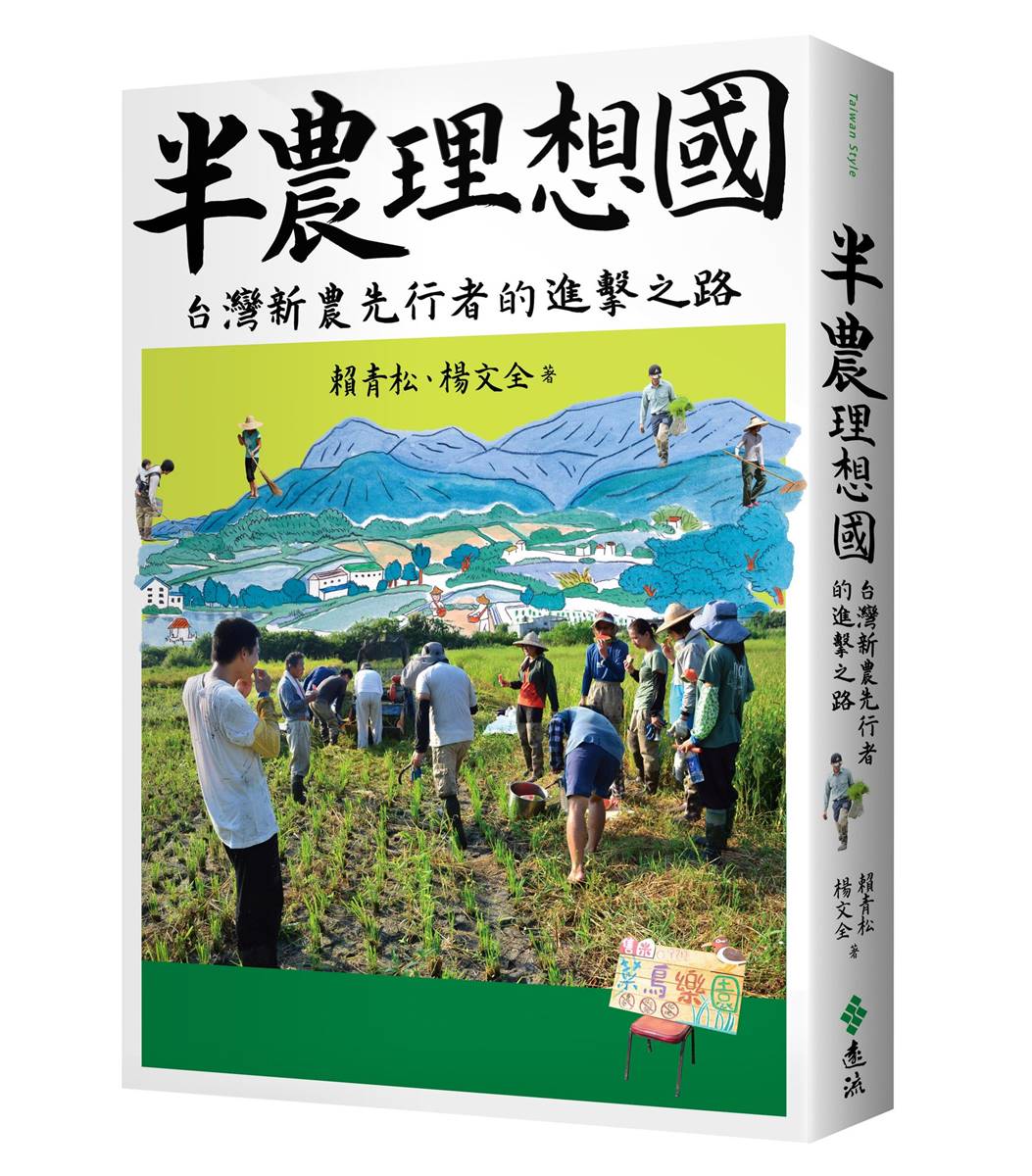來到深溝村的新農們,基本上都是致力於從事不使用化學藥劑的友善耕作。這與賴青松十幾年來在深溝村所堅持的農作方向是一致的,說起來似乎簡單,只需要照著賴青松既有的方法,按部就班,就能夠從深溝村水田裡順利種出稻米,不是嗎?事情顯然沒有那麼簡單。
老農與新農之間的磨合
在深溝村,賴青松之所以長期受到老農地主們的信任,有一個關鍵的原因是,他雖然沒有使用化學農藥與除草劑,但是在水稻耕作的各個階段,他所管理的友善稻田,外觀上都跟使用農藥與除草劑管理的稻田沒有明顯差異。在水稻生長期間,賴青松一定會想方設法地把田裡被福壽螺吃掉的秧苗補齊,將雜草清除乾淨。簡單地說,賴青松耕種的水稻田長得整整齊齊、飽滿漂亮。當然,只要能夠做到這種程度,水稻的單位面積產量往往也能達到一定的水準。
但是,新農們大部分都無法達到像賴青松一樣的水準。如果這只是因為缺乏經驗,以致於在田區管理上有所疏漏,那倒不是太大的問題。只要假以時日,累積更多經驗之後,就有機會達到老農的標準,至少不至於被老農地主們嫌棄或批評。比較麻煩的狀況在於,新農在友善耕作的方法上,往往有各式各樣的追求與理想。新農法的實驗與嘗試,經常導致田區的管理無法達到一般標準。甚至,有些新農還會刻意挑戰這樣的標準,覺得自身的做法才正確,老農一昧追求雜草清零的想法是落伍的。
對於雜草失控的田區,老農地主們的顧忌通常有兩種,一是看了不習慣,總覺得自己辛苦照顧了一輩子的田地,本來種得漂漂亮亮的,現在被新農搞得亂七八糟,還會被鄰居親友笑話,怎麼吞得下這口氣;另一個擔憂是田裡長了這麼多雜草,萬一這個新農明年放手不管,那落在田裡的雜草種籽又該叫誰來收拾?
這種新農與老農之間,在價值觀與實際操作面上的根本衝突,幾乎無法妥協或化解。我們不可能讓老農心裡過不去,因為他有可能因此收回土地;但同時,也不可能要新農放棄自己在農耕上的發想,因為他也可能因此離開深溝村。所以,我們的做法,就是在老農與新農之間建立一個田地代管的緩衝帶。

倆百甲串起媒合作用
多年以來,倆佰甲作為新農育成平台,最主要的功能即是為新農夫媒合田地。媒合的方式頗為獨特,深溝村的老農或地主將田地交給賴青松代管,他將這些田地轉介給我(倆佰甲的負責人,面對新農的窗口。二○一七年春耕之後,這個位置轉由曾文昌接任),我再媒合給新農夫。簡單地說,賴青松就是倆佰甲的土地部門,我與繼任的曾文昌則是人事部門。有了這個媒合平台的機制,地方老農們不需要對新農夫有一定程度的熟悉與信任感,也能夠將田地轉租出去;同時,新農夫也不必到處碰運氣,尋找願意出租的田地。
更理想的是,在這個機制下,我不必直接面對老農與地主們,費心打點關係,那對我這種移居深溝村不久的新人而言,確實有些沉重。至於面對新農夫,因為很好奇他們為何而來,於我是一件充滿樂趣的事。相對地,這樣的機制,也讓已耕種十多年的賴青松,無須將一定的農事標準直接套用在新農夫身上,畢竟這些標準對新手農夫而言確實十分為難。而維繫與老農及地主之間的信任關係,則是賴青松長期立足深溝村的根本,也是他日常需要費心的所在。
在如此平台機制下,老農與地主們如果對於耕作的新農夫有任何意見,會直接向賴青松反應,他將這些意見轉達給我,我再告知新農夫,提出改善的要求。在這樣層層轉達的過程中,即使老農與地主們有再多的抱怨或不滿,對剛進場的新農夫來說,壓力已減輕許多,雙方不會立即產生過於激烈的對立或衝突,進而減少新農夫折損或退場的機率。
但維持這樣的機制,倆佰甲也有需要面對的壓力與風險。例如新農夫與可耕田地的供需天秤兩端,難免出現落差。老農與地主們大多在每年的十月休耕期結束之後,便會決定下年度釋出田地的數量,此時,倆佰甲必須當下決定是否承接新田。然而,往往要等到來年春暖花開之際,大型曳引機的引擎聲此起彼落地隆隆響起,才會催促新一批的夢想家們痛下決定!想要投入水稻耕作的新手們,似乎必須看到有些田裡開始插秧了,才會意識到做決定的時刻到了。只是,此時如何才能有多餘的稻田來支應新手們的需要呢?
從另外一個角度來說,原本由賴青松二○一二年一肩扛下的艱難決策,如今每年入冬後,改由倆佰甲的平台集體承擔。如果該年度倆佰甲所承接的農地面積,大過於新手農夫所需要的數量,我便需要出面協調,拜託有能力的夥伴們暫時代管多餘的田地。這樣的操作模式,也再度體現倆佰甲作為育成平台的公共性,最重要的目的就是保留深溝村珍貴的農地,為往後可能進入深溝的友善新農留下一條路。
友善新農的水稻產業鏈
為了支持新農們順利耕種水稻,倆佰甲也需要擁有一套能有效運作的機械化稻作代耕系統,特別是在新農們剛剛進場的階段。
在一般的台灣農村,水稻的機械化代耕系統已非常完備,是發展成熟的產業鏈。服務內容從大型曳引機的耪田與整平,到育苗、插秧、施肥、收割、運送、烘穀、儲藏及冷藏,乃至於最後階段的碾米、色選與真空包裝等環節。然而既有的產業鏈無法為新農們提供適合的服務,主因是業界早已形成一套符合規模化、標準化的作業程序。這套高效率的代耕系統,奠基於越來越大的生產規模,大面積的單一田區,以及農地重劃過後源源不絕的灌溉溝渠。同時,農夫也需要熟練地配合機械化操作的節奏,在每一個生產環節跟上腳步,例如,在春耕整地之前,隨時確保田區能維持適當的水位。
然而,新農卻往往面臨種種不利的處境。首先,由於友善新農是最後進場的參賽者,因此入手的常是慣行農法業者因不利大型機器操作而放棄耕作的田地。例如,不方正或位置不佳的田地,抑或是土層較淺充滿礫石的薄田。其次,倆佰甲幾乎都是新手農夫,對田區的操控上往往不如人意,很難配合大型代耕業者所要求的精準度。第三、新農的耕種面積相對較為零碎,這對田間機械的操作,或是稻米收割後的後期作業,都不可能有很好的效率。種種原因讓我們很難找到願意長期配合的代耕業者。也因此,如何建置一套專門服務新農夫的水稻產業鏈,是一開始就出現在眼前的難題與選擇。
倆佰甲第一年接下的兩甲半水稻田,是透過李婉甄的引介,才找到願意協助的代耕業者。但是到了第二年,倆佰甲的水稻耕作規模瞬間擴大,增加到三十位小農、二十甲的田地,這對只有兩年耕作經驗的我們來說,是極大的挑戰,需要專業代耕的協助。沒有人可以告訴我們該怎麼辦,只有靠自己摸索,想辦法摸著石頭過河解決問題。同時,許多新增加的田地,因為長年處於休耕狀態,連專業代耕業者都避之唯恐不及。例如土層中石頭很多的田、有湧泉難以排乾的田、奇形怪狀不方正的田等等。
結果,這一年在尋找代耕業者上硬是吃足了苦頭,但也因此促使我們認清現實,自己發展代耕系統,是遲早都要面對的課題。

提供代耕服務,體諒新農處境
當時,倆佰甲內部分成四組,分頭尋找願意協助的代耕業者。但是,由於休耕農地活化政策的推行,許多代耕業者本身也被迫承接過多的田地,操作能量已趨近飽和。因此,我們只能非常彈性地運用各個不同業者剩餘的零碎時間,一點一點完成田間的工作。而最初分成四組委託代耕業者的目的,也是考慮到若遭遇臨時狀況,還有其他三組可以支援。當四組業者都無法進場時,我們就自行購買小型的二手設備,把最後剩餘的作業完成。正是在如此艱難的處境下,倆佰甲的水稻代耕操作系統,一開始就具備開放、彈性的特徵。同時,也因此開啟了自備農業機械,甚至促成新農夥伴成為專業代耕業者的道路。
隨著倆佰甲的規模日益成長,透過各種管道來到深溝村及周邊村落的新農越來越多,友善耕作的面積也一年一年增加,開始出現有心投入代耕事業的新農,購買各種大小農機。我自己就買了一輛二手的大型曳引機為大家翻耕田地,後來有人陸續添購插秧機、割稻機、烘穀機、碾米機等等,為這個不斷成長的新農社群提供專業服務。同時,也有新農們以集資的方式,共同購買農機以滿足自身水稻生產的需要,這種做法一方面可以減輕個人添購農機的成本,一方面也可以讓更多人取回田間管理的自主權,例如農機進場的時間,以及翻整犁田的方式,而不必受制於傳統代耕業者的操作慣性。
由於提供代耕服務的就是新農社群自身的成員,更能了解與體諒新農的處境,因而慢慢發展出滿足友善稻作需求的專業服務。例如:在不用藥的情況下,為了減少福壽螺對於水稻秧苗的危害,有人建議在春季田區翻耕時,在四周的田埂旁邊開闢出較深的側溝,引誘福壽螺集中於此。而因為擁有自己的曳引機,我們可以從嘗試錯誤之中,找出以曳引機開溝的方法與程序。又例如在稻穀的儲存上,建立一套共享倉庫的彈性管理方法,以因應新農小量出貨的需求,而這些都是既有業者不願意或無法提供的服務。
發展至今,目前在宜蘭員山地區,已經出現不少代耕業者,願意為新農夫們提供各種開放及彈性的服務。其中有傳統的在地代耕業者,也有轉型投入的新農夥伴。如今每位進場的新農夫,都有機會在此找到相契的業者,彈性地建構出專屬自己的作業流程,實現理想中的農耕事業,掌握務農的自主性。(本文摘自《半農理想國:台灣新農先行者的進擊之路》,主照與部分小標為本刊所加。)
作者簡介:
賴青松,日本岡山大學環境法碩士。「青松米穀東俱樂部」發起人,「慢島生活公司」共同創辦人,「穗穗念」共同創辦人。
長期關注經濟發展與環境永續間的平衡,2000年選擇到宜蘭展開半農半X的實驗生活。2004年發起穀東俱樂部,開啟志願農民進鄉的新時代。2013年,協助倆佰甲新農育成平台成立。2019年,出任慢島生活公司負責人,開始以商業模式打開城鄉反向移民的通道。
楊文全,臺灣大學建築與城鄉所博士。「倆佰甲新農育成平台」發起人。法鼓文理學院兼任助理教授。務農期間曾任宜蘭縣政府農業處處長。
長期從事農村規劃工作,2013年為突破規劃上的瓶頸,開始在宜蘭縣員山鄉深溝村務農,從事友善耕作的水稻栽種,企圖以農夫的視角在實作的場域中探索台灣農村在網路時代可能的發展契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