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秤颱風過境後,天空恢復成一片晴朗。10天前,陽台水龍頭下面的破水桶被吹到隔壁阿伯家的門口,阿伯家門前的籐椅被上下吹翻倒了過來,附近的社區老人活動中心失去了一棵相伴多年的老榕樹,老榕樹被吹得連根拔起,硬生生地橫臥在通往田間的馬路上。而這些都已經是10天前的事。陽台上的水桶又滴答滴答確實地接著那個會漏水的水龍頭,藤椅上的阿伯正在陰涼之下獨享夏末的涼風。老榕樹被攔腰鋸成兩截又種了回去,少了濃密的樹蔭,看起來是有些殘缺,幾乎變成颱風曾來過的唯一的證據。一切又回到了日常,原本被颱風吹得一律倒向南的稻子,如今又站得直挺挺,將台東覆蓋成一片片濃密的綠。
我嘗試忠實地記錄著日常的一天。
早上五點半天空透出微微亮光,我睜開雙眼然後又賴床了。因為早晨冰涼的空氣和床單緩緩透出來的溫暖叫人舒服地難以抵擋。六點半,應該是六點半吧,我不確定。床頭櫃上已經沒有鬧鐘,再也不願意被時間催趕甚麼。早上是一天工作最寶貴的時間,天色尚未明亮,遠方的都蘭山在清晨總會覆蓋著一層特別濃的霧氣,被雲朵包圍只露出山頭化作雲端上的蓬萊仙島。
我想像自己是一個早起的農夫(其實很晚),就像一隻驕傲、有權力的公雞在萬物俱寂的時刻準備破曉,我彷彿擁有浩瀚無垠的宇宙,那權力之大就像是開啟自然運轉的發動者。寧靜的清晨,空空如也的馬路,樹枝上頭的鳥兒靜悄悄,遠方的山頭煙霧繚繞。這一切就要在下一秒開始改變。冰冷的空氣會再次被太陽曬得暖呼呼,成群的鳥兒又會開始吱吱喳喳,山上的霧氣也終將煙消雲散。在這短暫的清晨片刻,我擁有著它(其實是它擁有我)。我吸一口冰涼的晨間空氣後呼喚棕狗的名字,GABEE迫不及待地跑來坐上機車踏板,然後我發動機車,一如公雞鳴啼。
我喜歡把機車熄火一路從山上溜到山下像騎單車那樣享受山裡的安靜。騎車過橋經過武陵溪下游,溪水因為山上下過大雨仍然是黑濁滾滾。到了田邊例行性地向稻子道聲早,很假掰地低下頭靠近她們吸氣自以為這樣可以吸到什麼菁華。
什麼也沒吸到。
但是看到稻葉上都還掛著一顆顆清晨的露水。田中有幾塊光禿禿的地方,那是被金寶螺吃剩的不毛之地,也代表著田裡幾個低窪的地區。傳統防治金寶螺(福壽螺)的方法無非灑藥或是使用 “有機”的苦茶粕,我曾經在幫農的時候灑過一次苦茶粕,隔幾天就可以看到成堆的空殼殘敗地散落在田間角落。但不只是金寶螺,所有身體有黏液的動物如蝸牛、青蛙、蚯蚓、水蛭也一併歸西。自然農法還指望著蚯蚓來替大地翻耘,所以連苦茶粕也不能使用。甚麼都不能用,只好眼睜睜地看著積水中的秧苗漸漸稀疏消失,補秧變成一種示意性的宣告或軟弱消極的抗議一再重覆。補秧到補無可補,乾脆把家裡的剩的芹菜渣和地瓜葉連同青草茶煮剩的茶葉茶枝通通丟進水窪裡,自我催眠以為這樣可以餵飽他們,毫無威脅地告誡著他們井水不犯河水。
事實證明有效,有效的不是那些菜渣,而是如同“南澳自然田”的阿江與“四季耕讀農園”的慶豪在網路影片裡所開示的,金寶螺確實不往沒有水的地方去。有水沒水,變成了一道無形的邊境讓人緊張兮兮,要不要放水進田裡,在初期的這30天變成一件讓人掙扎的決定。手心手背都是肉,不放水稻子會枯黃,放了水金寶螺又像開了鬼門,在中元節放出去的水燈一樣。所幸,有“一根稻草的革命”的信心加持,作者在書裡說他初期照顧水稻的方式如同旱作一般,加上老天爺眷顧,不時在午後來陣及時雨紓解大地的渴,截至今日(9/2)為止,我只跑過一次水。而晴天和雨天的比例據筆記剛好是12天(全天晴朗) versus 12天(陣雨、大雨、颱風)。
日本來的秀明農夫畑匡昭先生說,秧插下去的那一刻就如同稻子和野草賽跑的槍聲響起。這20幾天來田裡都沒有淹過水,野草們毫無阻撓飛快地追趕著秧苗。10天前,我參考網路上流傳的防草密技,也嘗試著用刷地板的刷子刷著秧間小路。那時候野草才剛發芽,點點碎綠像碎花布一樣美麗,引來隔壁可愛的阿公阿嬤用台語關心發出如下述語句: “唉呦威,那~麼多草…”,“少年ㄟ,哩這工作做沒完啦!”和 “疑,哩手裡那一支係瞎密?”等。網路的妙招連活到70的阿嬤都沒見過,雖然遠不比灑除草劑輕鬆,但效果真的很不錯(如果泥土再漿一點會更棒)。

如今又過了10天,稻子已經來到約30公分高,正拼命地分蘗著。野草還是緊追在後,除掉他們就是我今天的任務。我在田裡仔細地分辨著敵我,心中默念莖節間有毛的是稻子,沒毛的是稗子。田裡大多都是碎米莎草和疑似火炭母草偶而會看見一些稗子,我先是彎著腰拔,很快變成蹲著拔,最後索性跪下來拔。莎草的根很淺,很容易拔,我重覆地拔著,很認真地把每根草都拔得乾乾淨淨,這樣的狀態很快地掉入一種執念,不思考,見草就拔,什麼都不多想,一心就想把雜草拔乾淨。可是雜草卻好像怎麼拔也拔不完,他們在阡陌之間,躲在稻稈周圍,有時隻身隱沒時而叢聚。好像一心要走到終點,卻慢步在一條永無止盡、沒有盡頭的路。剛開始一切新鮮刺激,哼著歌盡情地享受周圍的景致,然後漸漸地開始感到乏味,於是想加速而奔跑起來,隨著因為焦急而凌亂的步伐漸漸讓身體感覺疲弱,再也無心欣賞路旁的風景,隨之而來的是一陣焦躁和厭惡。
這時我的心底出現一個聲音,
“為什麼要除草? 為什麼要討厭草?”
“因為他會阻礙稻子的生長”
“真的嗎?”
“…”
“我想還有因為我怕隔壁的阿公阿嬤、幫我插秧的師傅、還有育苗場的老闆他們會過來看,會過來指指點點吧,他們會說我懶惰,說自然農法不行,說這說那…”
“!”
是阿,除非是把稻子給包住的雜草,讓稻子行不了光合作用,否則我還沒看過有甚麼理由說雜草和稻子無法共生的。那究竟我在除什麼? 又是為了什麼而除? 我停頓下來,看著滿手的黑土和雜草,陽光不知何時已經灑落在大地之上,在某個精準的角度,會把葉子上尚未蒸發的露水照得像鑽石那樣閃閃發亮。我突然覺得他們在田裡出現也許有其他的意義,我曾經很專注地把草看得很清楚,但從來沒有一次真正地看到他的存在!
我突然一下子覺得好輕鬆,身體也不再疲倦。我又跪下來除草,但不再費心去想著田中行距間是否乾淨,因為我不再在意阿嬤的眼光;我仔細地將稻子周圍的草剔除,迎接其他雜草的存在,我欣賞起他們的獨特的葉形和姿態,就像那個重新愛上路旁風景的跑者。我甚至最後開始想像自己是一隻牛(不是羊,因為他們吃草的方式不一樣),而這裡是免費的沙拉吧,我用手掌大把大把地捲起叢聚的雜草,聽著雜草發出清脆的撕裂聲,就像牛用舌頭在吃草那樣。我只要勤勞地修剪自己心愛的草坪那樣對待他們就好,我跪著,化身成一條牛。
那天回家吃早餐的路上,我經過每天必經的山坡,我注意到今天的天空很藍,一種很單純很單純的湛藍,那藍變成了一個背景襯托著青綠但已開始轉黃的大地。
”要進入秋天了嗎?”
我騎進綠色隧道,抬著頭欣賞頭頂上樹葉舖成的細網透出閃閃藍光,一片一片地在我眼前飛梭,而我的臉頰享受著這最後幾分鐘的涼爽。這風景突然喚起了我當初到日本或是歐洲旅行隻身冒險的記憶。這樣子的驚奇感動從來沒有在任何一個已經熟悉的地方發生過,但今天在一個再熟悉不過的必經之路上,卻前所未見地感到陌生,但一切又顯得那麼新鮮刺激、自由與美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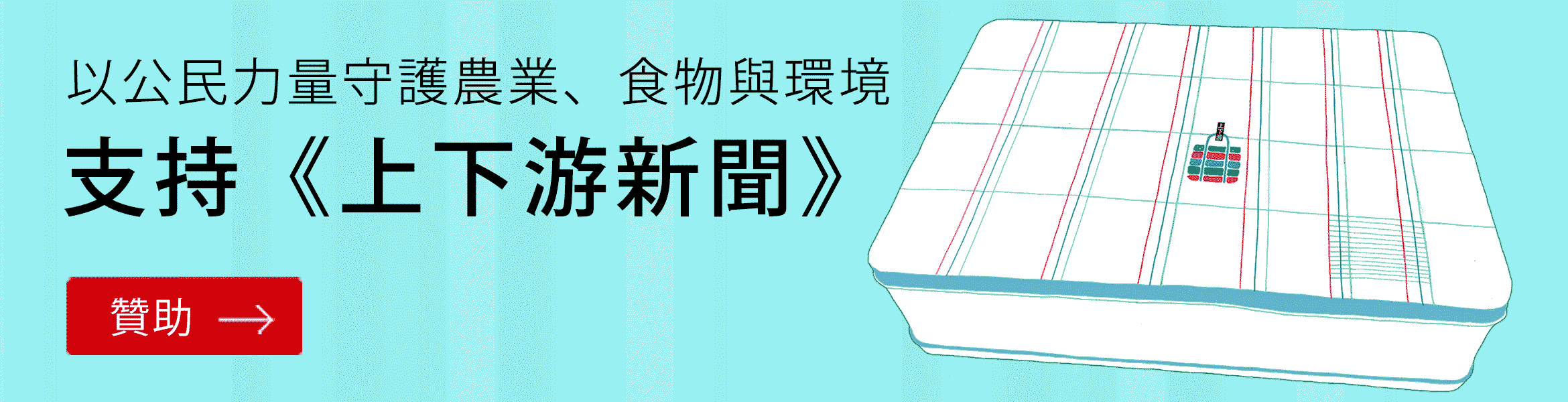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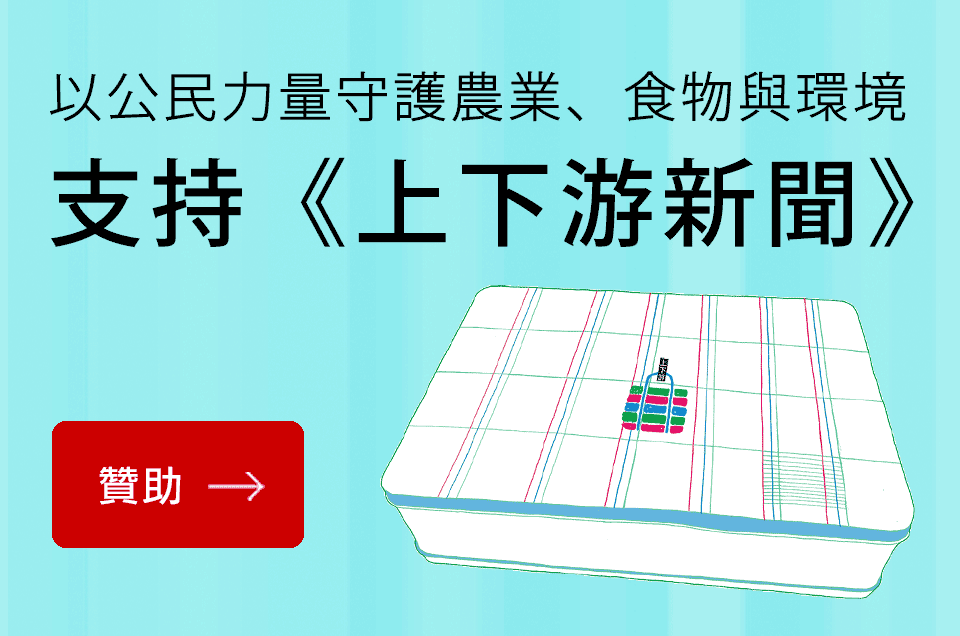











真的是很棒的觀察與領悟,請繼續加油
不過這也讓我想起在之前有人分享除草的妙招時,我提出”為什麼需要除草呢?”時,所引來一些討論
之前農改廠送我們有機的苦茶粕,我們也是用一次就嚇到,怎麼蚯蚓死了一堆.
殺傷力比慣行農法用的殺蝸牛藥還強.
現在我們也是不敢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