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壽螺,怎麼辦?有機的用苦茶粕,慣行的用耐克螺或者偷用三苯醋錫。
以往農改場針對苦茶粕的建議用量是「每公頃50公斤」,但農人的感受是「一甲地300公斤都不夠」,因為苦茶粕會危害田間其他生物,所以農試所改以無患子抽出液研製「益無螺」粒劑,但田間使用者仍少見。
三苯醋錫很毒,所以農政單位禁用,改以耐克螺取代,但是農人的感受是「耐克螺毒性比較輕,但是用量要好幾倍才有效,加起來毒性還不是一樣。」雖然是禁藥,但熟客仍然可以在農藥行買得到三苯醋錫,這是公開的秘密,去掉包裝,無色無味,很難抓,罰款沒有改變講求效用的農人,甚至在有機產銷班也發現這個東西,這也就不足為奇了。
農政單位的宣導、建議,始終不敵「農友前輩」的經驗主張,這樣的拉扯時時在田間發生。
福壽螺,農人一般稱呼「金寶螺」,很諷刺,不管是福壽還是金寶,農人避之惟恐不及,但是對某些人來說,福壽螺卻讓他們賺到一筆外快。休耕期間,蓄滿水的田裡會出現捕螺人,沿著田邊放下誘餌,有用俗稱的「鹿仔飼料」,有用發酵的麥子,福壽螺聞香而至聚成一堆,捕螺人用特製的撈網一網打盡。捕螺人說,這些福壽螺都是運到竹南以南的釣場,釣烏鰡、黑格(?)很受歡迎,一公斤十幾塊,賺個幾萬塊不成問題。
福壽螺用大米袋裝著,送上貨車從宜蘭運到西部,不吃不喝又悶熱,折損率很高吧?捕螺人說,一袋上萬隻,死掉的不超過兩隻手掌,福壽螺夠耐吧!

(福壽螺的食性雜,葷素不忌,連福壽螺卵也不放過。)
福壽螺的食性更是堅強!我看過廢報紙上爬滿了福壽螺,也看過死在田裡的水鳥引來一身的福壽螺,甚至福壽螺卵也不放過。常常聽人說,用福壽螺來吃雜草,這在田裡沒有秧苗的時候的確可行,但是我的實地耕作觀察,福壽螺有品味,絕不是飢不擇食,牠也是美食家,牠會挑秧苗而棄稗草,即便秧苗比較粗壯,一旁的稗草比較幼嫩,牠還是想盡辦法爬上秧苗,用體重壓彎稻葉,落入田裡啃食。
回到我耕作的田裡,撿除福壽螺,在插秧之前就必須密集進行。我用過高麗菜葉,用過米糠糰,今年我發現更好用的誘餌—地瓜葉,福壽螺先吃葉,葉子吃完了就吃藤,吃到什麼都不剩。
插秧之後,什麼誘餌都無效了,接下來就是拿著寶特瓶改裝的桶子,巡田展開巷道游擊戰。雖然田水盡量放低、放空,但是「世界不是平的」,行間、株間只要有積水就可能淪陷,秧苗全軍覆沒,一陣心痛。這樣的戰事大約持續一個月,直到補秧補到無秧可補。
撿除福壽螺是運動兼行禪,但是怎麼處理這些福壽螺,卻讓我傷過腦筋。我曾經載去餵魚,送給捕螺人,拿去堆肥,可是既麻煩又不減碳又不「自然」,尤其太矯情。就地正法吧,可是腳踩的當下,聽到破裂螺殼的聲音,不免心虛遲疑。

有個常常作拔草志工的朋友提供了建議:「總會先念三稱觀世音菩薩聖號,然後念一個除草偈:
我今除草除惡業
一切眾生皆迴護
若於鋤下喪其形
願汝即時生淨土
想到拔草的時候,拔的不只是草,還有心裡的煩惱,就越拔越起勁,過程中難免傷害了眾生,道了歉送了祝福,心裡就踏實安穩了不少。」
但在這之前,我是從《薄伽梵歌》得到力量,在俱盧之野,在戰場上,阿周那與黑天的對話:
阿周那看到父輩、祖輩、老師、舅父、兒子、孫子,還有兄弟們和同伴。阿周那還看到岳父和朋友們,他的所有親戚都站在兩軍之中。他滿懷憐憫,憂心忡忡說道:
「看到自己人,聚在這裡渴望戰鬥,我四肢發沉,嘴巴發乾,我渾身顫抖,汗毛直豎。」
「我不渴望勝利,黑天啊!不渴望王國和幸福。」
即使我被殺,黑天啊!即使能獲得三界王權,我也不願意殺死他們,何況為了地上的王國。」
「我寧可手無寸鐵,在戰鬥中不抵抗,讓持國的兒子們,手持武器殺死我。」
阿周那說完這些話,心中充滿憂傷,他放下手中弓和箭,坐在車座上。
阿周那精神沮喪,站在兩軍之間,黑天彷彿笑著說道:
「無論死去或活著,智者都不為之憂傷。」
「智者對痛苦和快樂,一視同仁,通向永恆。」
「沒有不存在的存在,也沒有存在的不存在。」
「你的職責就是行動,永遠不必考慮結果。不要為結果而行動,也不固執地不行動。摒棄執著,阿周那啊!對於成敗,一視同仁。」
「你永遠無所執著,做應該做的事吧!」
不就是福壽螺嘛,不就是病蟲害嘛,何苦牽拖這些有的沒的?何苦掉書袋?
因為………我的八字輕,沒有一點《哲學的慰藉》加持,生命中就會有太多不可承受的輕。
因為………把一個人抓牢在地球上的,不是地心引力,而是一點這個或那個的信念與堅持,否則人就會輕飄飄,或者無所適從,或者隨波逐流,活不出一個人的力道與重量。
這就是福壽螺教我的事。
(本文同步刊載於作者部落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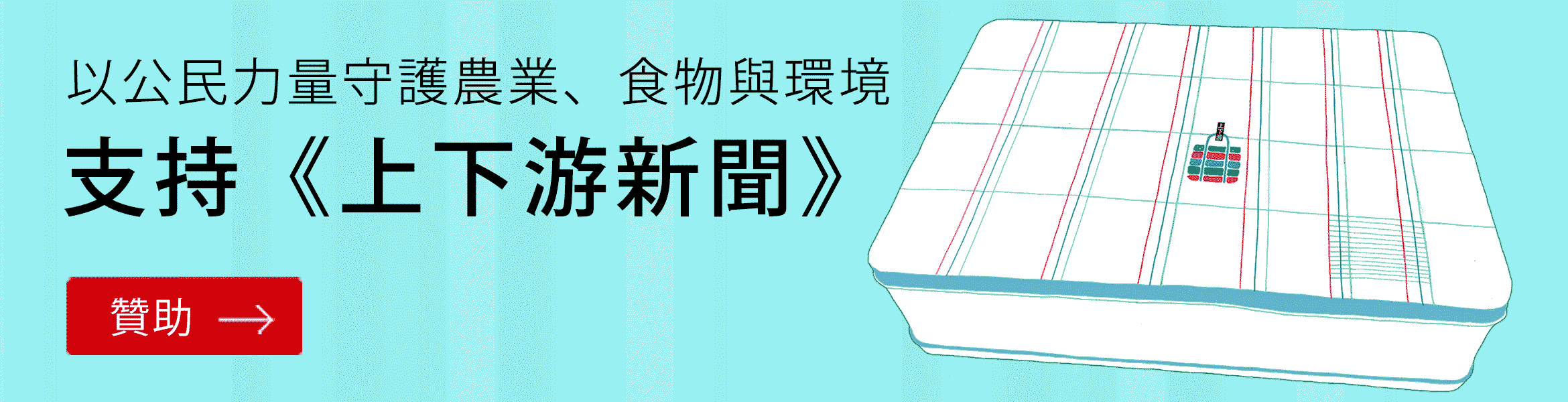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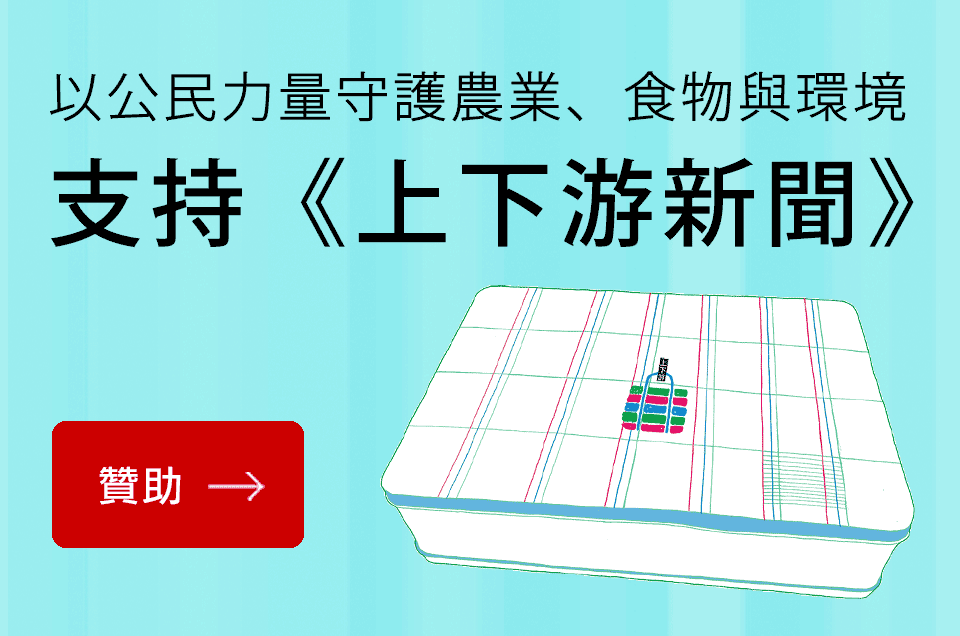











原來用苦茶粕也沒辦法防治福壽螺啊…
小弟受教了
只是不知到使用三苯醋錫這玩意
會不會也會被秧苗吸收
然後被我們吃下肚呢?
沒想到竟然有〈除草偈〉,感謝,我也需要這份智慧來加持我的行動。
噴藥前心裡很掙扎,撈了好幾桶先行放生,沒能撈出來的,噴藥時為牠們獻上祝福,得以出離畜生道,往生極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