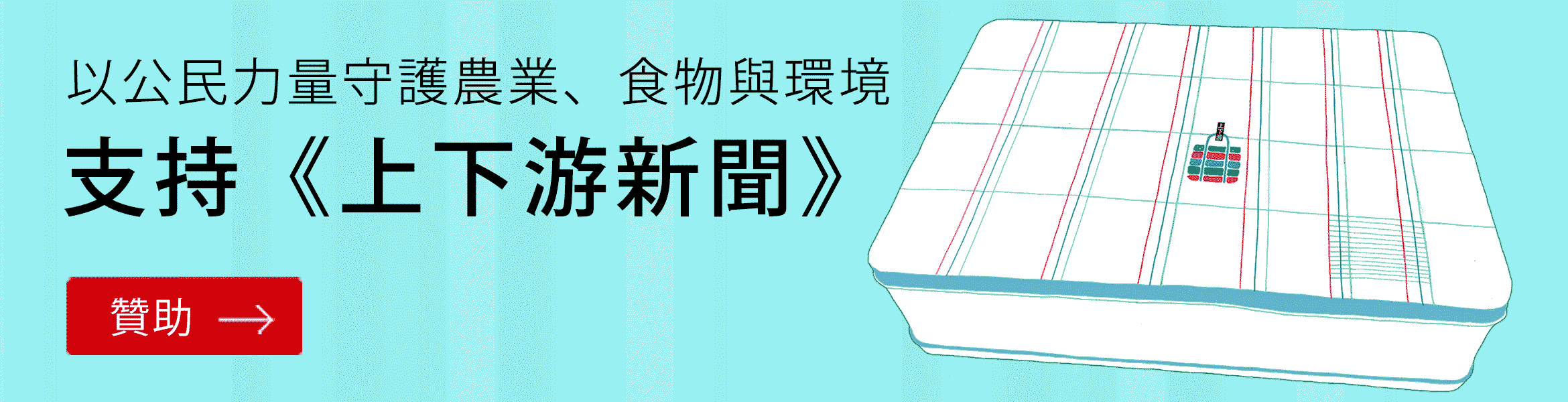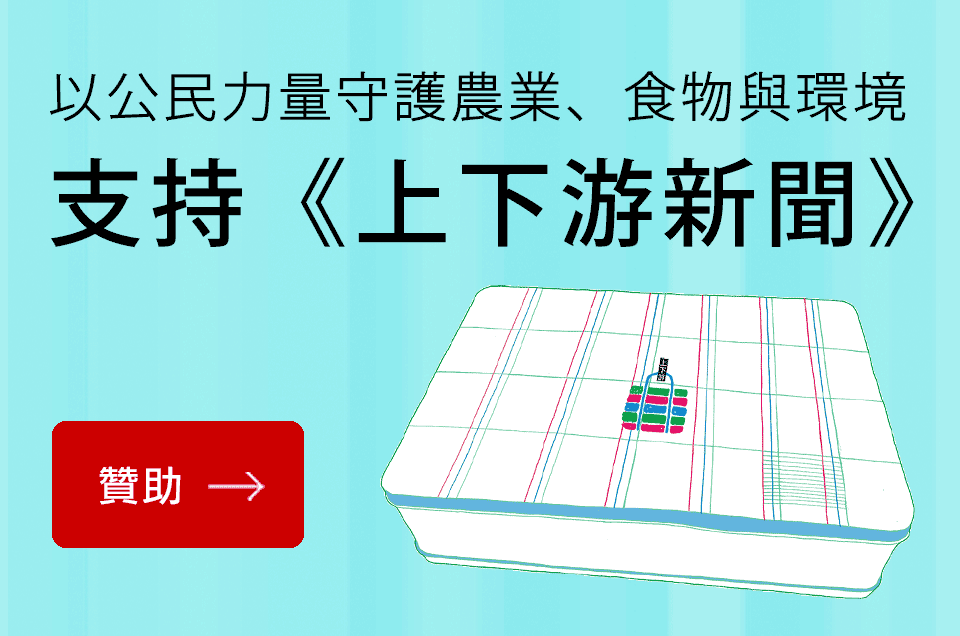◎文 / 劉崇鳳、圖 / 林東良
晚餐時刻,我呱啦呱啦地講著清水斷崖出遊的心得,「站在很高的地方,還是可以聽見海潮聲喔!」、「走進山裡,我覺得心安,感覺好像是〝我回來了〞……」然後我高舉雙手:「又回到山間海邊,啊,真是太開心了啊!」
「那出海有看到海豚嗎?」他問。
「海好大、原來海有這麼大啊!」我情緒飽滿,聲音高亢,一邊比手劃腳,像從來沒見過海的小孩。在看到他疑惑的眼時驚覺自己似乎有點過頭,才搔搔頭:「有啦,有三隻花紋海豚……」然後哈哈哈亂笑。
當鄉村生活日復一日,你還是需要外在世界的躍動,才能重新聽見心跳。
「我跟著船搖晃,感覺船在海上跳舞。」在海上航行幾次,我現在才發現船會跳舞,「是海教船跳舞的,船不能忘記海,就像人不能忘記土地。」我煞有其事地說。他點點頭。
「下次,我們也邀朋友,去清水斷崖附近走走吧!」他點點頭。
一定是夏天快要到的關係,我才會那麼興奮。一定是感覺到山變綠了,而海更藍,我才會如此滿足。
一切都是為了清水斷崖,一切都是為了他們說要去海上看紅色的崖壁開始。
多羅滿船公司的林大哥幾年前提出航行至清水斷崖的提議時,許多人不解也不看好,無情地說別鬧了、別傻了……那一定是因為,我們都沒看過清水斷崖,不明白航行這麼遠、走這段山路所能見的風景,原來如此遼闊無邊。
所以當東良寄發通告信給志工,信件裡用紅色放大字強調〝我們要在日出之時去看紅色的大牆壁,誰要去看紅色的大牆壁?〞我不自覺就笑出聲來,不管是從陸地或是海上,看清水斷崖,不知覺就變成了黑潮夥伴間的默契,一個暗語,一個只屬於我們,公開的祕境。
儘管每年都帶著來自島嶼各處的朋友們前往,還是每年都不一樣。
那是一處經過整治的碎石坡,石頭都還很新,一條康莊大道從碎石坡的腰際橫劈了過去。
土匪不走修好的路,他背著相機在碎石坡上走著,面朝大海,居高臨下。我們看著他的背影,視野反而更單純了,只有海、天與石頭。
賴威威站在中間說明:這是為遊人安全而闢設的步道,看似貼心,卻干擾了環境本身,有沒有更合適的辦法……
海平面像是被風吹皺的藍色絲綢,平平靜靜,天寬地闊。
海岸線隨灣口沿繞,白色的浪花散落在沙灘上,我們已經站在可清楚眺望大海的高度,卻依舊能聽見海潮聲。
就像,船航行至清水斷崖的岩壁前,船隻的引擎聲因待速而減弱,土匪(解說員)貼心地沒有說話,於是我又再次聽見了,海浪在岩壁上,往覆拍打的聲音。
那是大海的心跳。
有那麼一刻,船隻靜靜地搖晃,山骨嶙峋,我站在船首,感覺近乎垂直的崖壁迎面而來,愈來愈大、愈來愈大,大到你必須逼視自己心中的渴望,必須承認心中的緊窒感其實是一種舒暢。料峭的岩壁上有不同顏色的岩質,石層的縫隙裡,竟還生有樹木,翁翁鬱鬱、生機勃勃,大自然真是太神奇。
貼得那麼近,而我們是那麼渺小。仰望崖壁,像是朝聖,一條細細如同腰帶的皺褶橫越了清水斷崖──那是日據時代的臨海道,台11線的前身,人類的斧鑿之痕。我終於明白,為什麼船公司的林大哥會突發奇想,耗時費力航行這麼遠來到這裡,只是靜靜觀看。清水斷崖揭示了一些什麼,一些我們自己也說不明白的事物。
日出以後,海面波光粼粼,山的稜脈都清晰了起來,東側的雲光倒映在這面的山體上,八點的陽光在海面上拖曳,拉出一條長長的光束。我抬頭,土匪也背對我們解說,船上的人都忍不住迴望遠去的清水斷崖,天更藍了,中央山脈很綠。我坐下來,把腳懸掛在船舷外,日光在海上斑斕,一隻花紋海豚舉尾下潛,閃閃發光的海面上,牠的尾巴舉得好高好高,優雅如同一位舞者。我瞇起眼,以為這是一張電影海報。土匪又在讀詩了。
我看見了前日那條我們走過的山徑,山頭小得像一顆饅頭;也看見了前日那條我們走過的沙灘,浪花迤邐,拉出一個漂亮的崇德灣。我們何其有幸,生在這座島嶼之上。回航途中,許多已死的河豚漂浮在海上,七星潭岸上的建築物愈來愈多,奇萊鼻還是一座埋盡垃圾的環保公園,我想起蘇花公路的命運,海風只是吹著。

這島,還有多少不為人知,壯麗又脆弱的角落呢?
大海的心跳聲永遠都在,豎起耳朵,我希望一輩子都不要忘記聽見。
所以餐桌上,我才會如此興高采烈地述說這兩天。大概也是天氣愈來愈暖和的關係,因為夏天就快到了。我想起土匪的解說引領、想起默默坐在船尾凝視著日出的東良、想起時不時為活動操心的賴威威、想起總在下山或回航後如同媽媽一般出現的姿樂。我想起這些人,明白自己喜歡與這些人共遊。興高采烈地述說裡,其實有他們的身影同海融在一起。
對我而言,生活在島嶼之上,有陽光、大海、高山,還有夥伴,光是意識到這件事,就是這兩天最迷人的收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