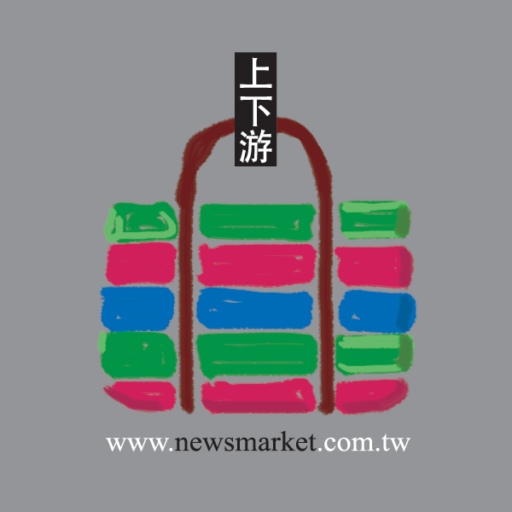在農村,許多農民很愛找農藥行詢問用藥、施肥的問題,信賴程度有如老師,但因農藥行的利潤和農藥綁在一起,農民接觸農藥行未必能獲得正確的使用方式,甚至造成過量施肥、多項農藥混合施用的「雞尾酒農藥療法」現象。
近年來雲林虎尾開了一家只賣有機質肥料和有機防治資材的農藥行,老闆陳鳳義本來在台北從事建築業,15年前返鄉協助父親的中藥行工作,中途兼職種過幾次田,逐步打開對農業的興趣,他開的義直農藥行不賣化肥,堅持只賣有機質肥和有機防治資材,非常獨樹一格,在雲林縣一帶更是異類。
-780x520.jpg)
農藥整組拿去噴 越噴越害
原本想當農民的陳鳳義,在兼職種花生和水稻時,曾經跌了好大一跤,「每次去農藥行買藥,藥行都給一整組,少說有10罐,結果越噴越多,蟲卻死不了,根本像亂槍打鳥。」
後來陳鳳義跑去農委會藥毒所上課,了解如何正確用藥,才發現傳統農藥行配藥沒有「輪用機制」,導致害蟲的抗藥性越來越高,舉例來說,水稻出穗若發生稻熱病,農藥行可能會同時拿三賽唑、嘉賜黴素和大成粉等給農民,結果他發現這三款都是殺菌劑,混和使用有如雞尾酒。
「正常來說,其實只要噴一款就好,但台灣農田長期噴藥,噴一款不見得有效,因此得採輪用機制,這次先噴A、下次再噴B,才能減少抗藥性的產生,甚至改用生物性農藥,像微生物製劑,針對性高、對環境又無害。」
雲林青農長知識 減少無謂農藥用量
陳鳳義開了「另類農藥行」後,在雲林結識一群理念相近的青農,雲林縣青年農民聯誼會的成員,有的種花生、有的搭溫網室種洋香瓜、有的種蔬果,他笑說,他對藥品的知識大多是透過和青農交流而來,雖然只賣有機質肥料和有機防治資材,無法獲得老一輩農民的市場,但透過交流,他再帶著青農問題去找農業改良場老師,從而學習正確用藥知識,這樣的販售模式是他自己認為比較理想的模式。
陳鳳義表示,雲林這群青農思維很不同,他們不片面接受農藥行給的「一組農藥」,而是到店裡指定要哪幾款藥,對資材累積專業看法,這群青農多是農二代,父執輩都有豐富的農耕經驗,也都慣用化肥和傳統用藥,他們返鄉接手大多希望能改用有機質肥料、減少無謂的農藥用量。
-780x505.jpg)
科學辦案 找出最適合下肥方式
一如農藥的使用習慣,青農發現老一輩用化肥堅信「給越多、產量就越大」,但過量使用的結果,不但導致台灣土壤偏酸的比例增加,甚至引發土壤鹽化。
在雲林種花生的青農陳炳洲說,老一輩不願改善肥料使用習慣、進行合理化施肥,大多是因為擔心產量會下降,像他的父親種花生會下3次肥,第一次的基肥一分地約用一包半,之後開花和結果再分別給一次肥,但其實花生本來就有固氮能力,並不用追肥。
陳炳洲接手花生田後,為了養地讓貧瘠的土壤逐漸恢復,決定改用有機質肥,他說,目前一包20公斤有機質肥要價350元,一包40公斤化肥則要300到450元不等,化肥和有機質肥的用量大概是1:3,因此他一分地用3包有機質肥,雖然初期成本比較高,但因為不追肥,也不用增加後續請人代施肥的工錢(一包約100元),算下來還比使用化肥省1000多元。
陳炳洲說,嘗試改用有機質肥後,他的花生田一分地產量有600台斤,和原本相當,父親最後才決定放手,「其實老一輩有老一輩的做法,他們有豐富經驗,過去被教導這樣使用化肥,並沒有對錯,這都是為了顧及產量,為了能夠養家,而我只是有機會在產能和土壤健康間尋找平衡而已。」
農青:當政府不再補貼化肥價差 才可能施肥合理化
現行化肥因為有價差補貼,間接助長農民多使用卻毫無節制的習慣,陳鳳義說,反觀有機質肥料,政府並不是每包直接給予價差補貼,而是農民需通過有機認證或處於有機轉型期,才能拿著證明向農會提出申請,而且計算方式是以耕地面積為單位,而非用量。
有青農私下透露,要翻轉傳統化肥用量過高的現象,最直接的方法就是取消化肥的價差補貼,同時搭配政府剛開始試辦的直接給付政策,「當化肥價格回到原形,農民才比較有可能因為成本考量,思考合理化施肥。」
此外也有青農提到,現行有機質肥料的品質不穩定,老一輩農民無法放心,擔心改用後產量卻一落千丈,因此相關業者如何生產較穩定的有機質肥,也必須納入配套管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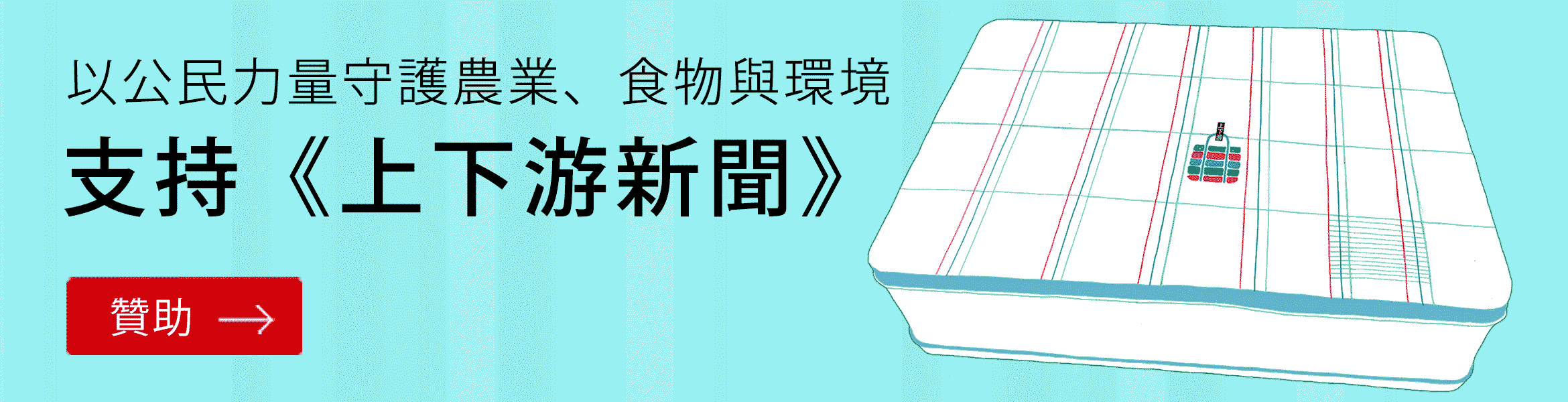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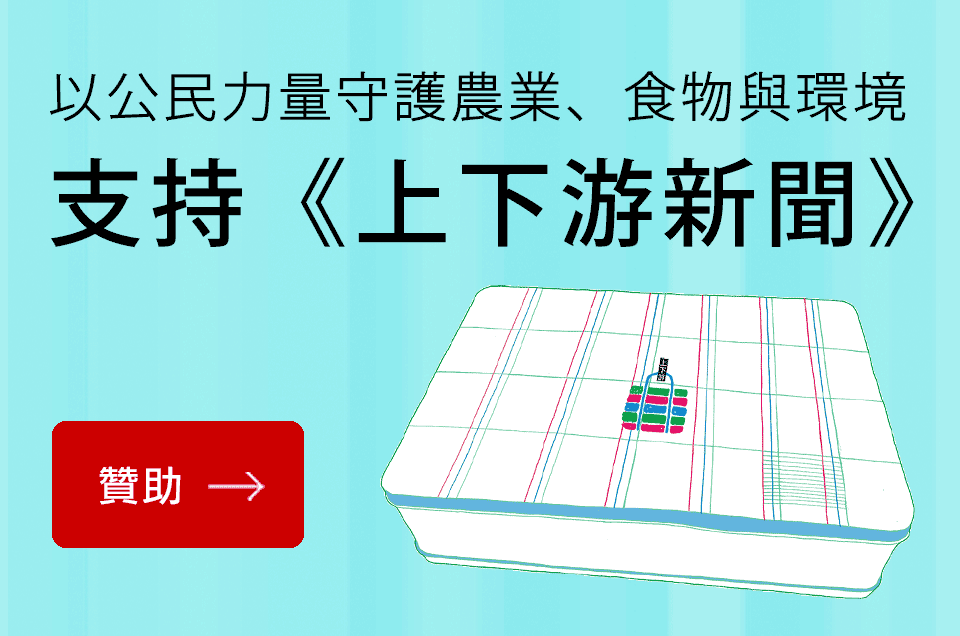




-293x293.jpg)